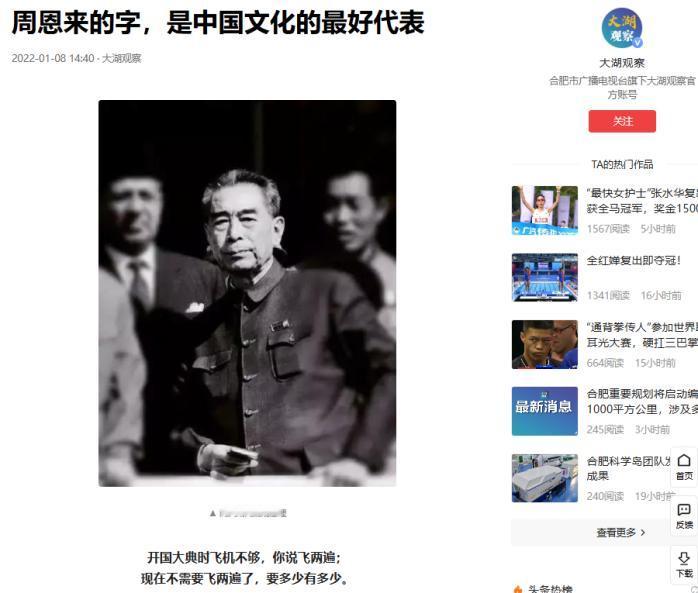1955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以后,林徽因认为碑文应该用楷体来写,但具体由谁来写犯了难,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说:“周总理的字苍劲雄伟,刚劲有力,有如颜碑,风格端庄凝重,可以问问周总理”。 1955年春天,纪念碑工程会议室里,林徽因拿着碑心石背面的尺寸图纸翻来覆去比对。一开始她估摸着能写150个字,后来精确算出来只有114字。 这114字分成三段,一段29字、一段30字、最后一段55字,一段比一段长,那股层层往上涌的气势,得靠合适的字体才能撑起来。 她坚持用楷体,可不是随便拍板的。碑刻跟在纸上写字不一样,得经得住风吹日晒,还得让不管文化水平高低的人都能看懂。 楷体规规矩矩、清清楚楚,刚好符合“刻在石头上长久保存”的需求。要是选了行书或者草书,过个几十年说不定就有人认不全了,那碑刻记录功绩、传递历史的作用不就打折扣了? 林徽因研究中国古建筑大半辈子,太懂传统碑碣的门道了——从汉朝的隶书到唐朝的楷书,只要是刻着重要历史内容的石头,几乎都用规整的字体。就连她之前设计的八宝山公墓碑刻纹样,也没脱离这种庄重的传统。 当时参与讨论方案的专家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用隶书显得古朴,也有人觉得篆书更有民族味儿,但都被林徽因一一考虑后否决了。 隶书的笔画弯弯曲曲太多,114个字挤在一起容易显得乱,特别是最后那段55字的长文,笔画多的字堆在一块儿,整体看着就失衡了;篆书就更麻烦了,认识的人太少,纪念碑是给所有老百姓看的,用太生僻的字体反而拉远了距离。 楷体就没这些问题,笔画清晰、结构匀称,就算是“内外敌人”“民族独立”这种笔画多的词,在有限的空间里也能显得端庄,跟碑心石方方正正的造型看着也协调。 彭真提这个建议,也不是一时兴起。他见过周恩来早年的书法,知道这位出身书香世家的领导人,书法底子特别厚。 周恩来少年时写的赠言里,就有明显的魏碑风格;1917年去日本之前,他给同学题字,那个“愿”字写得宽宽大大,笔力沉得像砸了重锤,那时候就能看出他对碑刻书法的理解了。 到了中年,他的字更显浑厚稳重,给保健护士郑淑芸的题词里,颜体的骨架和行书的流畅结合得特别好,48个字写得又秀气又有劲儿,完全能撑得起碑文的庄重劲儿。 更关键的是,周恩来从纪念碑奠基到建设,全程都参与了,1949年奠基典礼上,他还代表主席团讲话,对“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建碑目的理解最透彻。让他写碑文,相当于让文字和背后的历史背景连在了一起,特别贴合。 为了写好这114个字,周恩来下的功夫比谁都多。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一睁眼,先不急着处理别的事,就坐在桌前练写碑文;晚上忙完政务,还得再琢磨琢磨,单个字反复比对,整篇连起来练习,前前后后整整一周,写了40多遍。 他还特意调整了书写的节奏:前两段29字、30字的短文,字体写得稍微紧凑些,透着历史的厚重感;最后那段55字的长文,就把字间距稍微放宽一点,让“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那股跨越时间的开阔感更明显。 这种细节上的琢磨,正好对上了林徽因之前琢磨的碑文要一层比一层有气势的想法。写完之后,他还亲自把手稿送到工地,挺谦虚地说“要是不行我再重写”。 这份认真劲儿,跟纪念碑建设者们的态度一模一样——光开采运输那块碑心石,就用了7116个工人;林徽因连浮雕上的花,都要从敦煌壁画里反复挑,最后选定了牡丹、荷花、菊花这三种有象征意义的花。 其实早有例子能说明这么选没毛病。南京中山陵的碑文就24个字,最后选了“民国第一楷书”谭延闿来写。他的颜体字结构宽绰,笔力跟铸铁似的结实,把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分量稳稳托住了。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分量更重,涵盖了一百年的革命历史,周恩来的书法既有颜碑的端庄稳重,又有魏碑的刚劲骨气,还加了他革命生涯里练出来的内敛锋芒,比单纯书法家写的字多了一层精神内涵。 林徽因看到手稿的时候,当场就认可了。她知道,好的碑文字体不光要好看,更要“看到字就能想到背后的人”,得让后人看到这些字,就能联想到书写者和那段历史的紧密联系。 周恩来的字正好做到了这一点——既有传统书法的底子,又有时代精神的印记,跟碑上172个无名英雄的浮雕配在一起,刚好构成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完整故事。 从1949年奠基到1958年建成,纪念碑花了3亿多元,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林徽因甚至把自己生命最后几年的时间,都投到了纪念碑上,而周恩来用40遍手稿换来的114字碑文,最后跟着汉白玉碑石一起立在天安门广场,成了跨时代的精神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