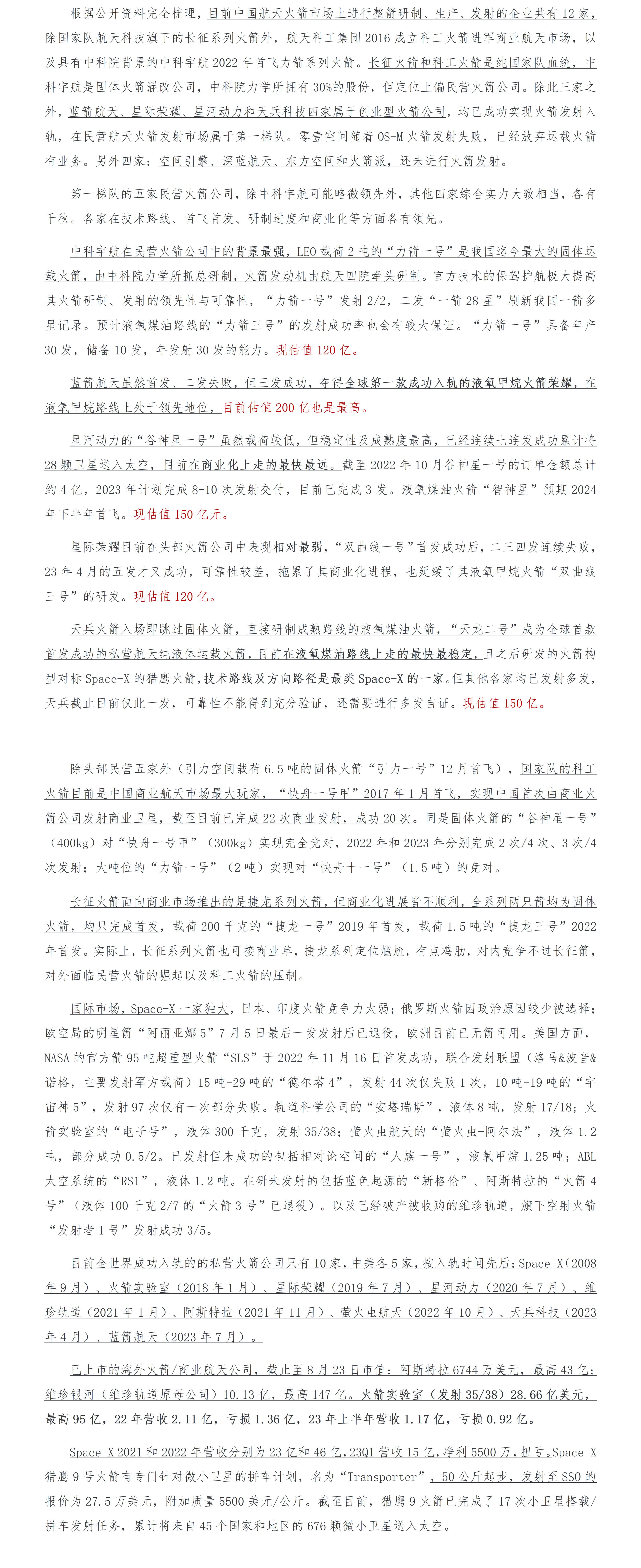【关于商业航天】
两年前做过商业航天的一级行业投研,与二级炒股重点关注产业链不同,一级是从整体的行业市场与技术进展来做研究。今天来看,整个行业进度略超预期,但总体还是在个人两年前的判断之内。两年前写的,现在来看,依然不过时,以下↓
商业航天的一级投资判断分两个项目:火箭与卫星;核心判断点:技术与市场。
国内商业航天市场与国外尤其是美国的商业航天市场完全是两种生态,虽说不至于完全不可比较,但差异性远远大于共性。
1.火箭:
航天行业对资源和技术要求极高,资金、设备、人才均大量集中在体制内,即使是其中最容易获得的人才资源,从脱离体制的那一天,在缺乏体制内配套服务的支持下,能力也很难完全施展。
尤其是火箭行业,国内所有的民营火箭公司,所有的技术渊源、人才支持、甚至是设备采购全部来自于体制航天,民营火箭公司的技术路径与模式虽然在一直追随Space-X的路子,但技术支持离不开体制。
但体制内的核心技术不可能流出给民营,会卡核心人才的流出甚至成熟产品的外供(蓝箭航天朱雀一号的火箭发动机是直接采购的航天六院货架产品,后被航天科技集团发文直接叫停禁售)。
Space-X除了接获NASA大量服务订单与经费补贴外,还获得了非常多的直接技术支持,比如前NASA载人航天主管退休后加盟Space-X。在中国,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目前及未来,体制航天能给到的支持:
体制内航天院所众多,或放手开闸部分非核心技术与非关键岗位人才(关键核心人才很难出走);
成熟的货架产品、设备配件后续可能会开放给民营企业;
不愿意做也无意竞争的微小卫星市场;
政策性让利扶持,比如“星网”分羹40%的发射机会;
类似中科宇航性质的民企与国企融合发展的商业航天模式。
但以上支持完全不足以使中国商业航天培育出可比腰Space-X的企业。航天产业具有极强的军工与体制属性,此二属性在中国是被尤其“关照”的,决定了中国商业航天的后天环境较差。除此之外,先天土壤也不支持,我们不具有Space-X在硅谷的创新基因。
Space-X是对美国商业航天的创新甚至颠覆,目前在全球一骑绝尘,其竞争力对其他所有竞争对手,包括各民营航天与各国家队,都是降维打击。
国内商业航天发展初期是计划航天的继承和拓展,是继承而不是颠覆,是拓展而不是发展,甚至可能都不是竞争,至少目前计划航天不care。人才、技术、设备大量依赖体制决定了国内的商业航天初始定位不可能太高,只能承接一些边缘市场。商业火箭去打一些低价值的微小卫星(高价值卫星更倾向于高可靠性的长征系列),商业卫星企业寻找低级目标和低端技术转移的市场去经营。
相较于体制航天,民营火箭公司的优势在于效率优势、整合优势与市场化。民营航天的最终目的与市场还是稳定的商业化,而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以及创新效率提升都是为了商业化的成功服务。
尤其是后者,民营航天的创新试错率要比体制航天高得多,新箭首发,体制航天没有99.9%的成功率保证是不会发射的,但民营航天极端情况下只需要50%的成功率就会发射,无论成功与否,发射即是“证明”。
也因此,蓝箭航天夺下了全球第一款液氧甲烷火箭入轨的荣誉。但其实国家队和Space-X都有首发液氧甲烷火箭的技术与实力,只是国家队更考核成功率,以及创新效率更求稳;而Space-X则是跳过了1,直接上100,首发全回收载荷150吨的“星舰”。
2.卫星:
对民营航天的商业化而言,火箭受制于体制与技术,而卫星更多的是偏向于市场因素。
美国的在轨卫星以通信卫星为主,占比约八成(全球通信卫星占比约七成),而且随着“星链”的不断发射,占比会继续提高。而中国的在轨卫星中遥感卫星占比约八成,中美两国的卫星生态完全不同。
原因在于:我国的地面基站基础设施建设异常强大,22年底4G基站603万个,23年4月5G基站273万个,全球4G基站和5G基站的七成均在中国。除了深山森林、戈壁荒漠等探险科考以及海上航行等需要用到卫星电话的特殊场景外,中国对天基通信几乎没有需求。地面基站通信网络超高密度覆盖、速率更高且时延更低,对卫星互联网是碾压竞争。
相较于中国高密度的信号基站(中国4G信号密度是美国15倍),美国的乡镇农村及城市穷人区、80%洲际公路都没有4G信号。美国弱地面基站的现实国情,天然催生了卫星互联网的市场需求,对于地广人稀的非城市人群,卫星互联网是刚需。
实际上对于仅有三成基站的全球除中国之外的所有其他非城市人口,卫星互联网都是刚需(全球80%的地区没有网络覆盖)。“星链”和“铱星”等国外通信卫星星座是真实需求推动的市场产物。仅就通信卫星及卫星互联网行业而言,中美市场生态完全不同,不具有可比性,“星链”的市场规模对中国不具有参考意义。
所以,事实上,除了小规模组网(中国交通星座、行云工程)以应对海上航行及探险科考等特殊需求外,市场因素下中国没有组建超大规模通信星座的必要。
即便不考虑国内地面基站已经能完全满足通信需求,强行组网也大概率会沦为摆设,因为没有市场,对内竞争不过地面基站,对外竞争不过“星链”。
国内市场,卫星基站资费要比地面基站资费贵,而且网络不稳定;国外市场,要么用不起(亚非),要么用“星链”(欧美),且“星链”组网更早、技术更成熟、更稳定、更政治。
也即,12992颗的“星网工程”不是以需求为导向组建,而纯粹是战略考量,占频保轨,先到先得。也因此,虽然一万多颗星看起来市场机会足够大,但实际上很可能发射组网进度会大幅落后于预期。一是战略意义大于实际需求,会故意压制发射频率与组网时间;二是未攻克火箭回收技术,发射成本太大。
通信卫星之外的第二大商业卫星是遥感卫星,但市场相对更小。
一是遥感卫星一般是区域组网或特殊任务组网,卫星所需数量少;
二是通信卫星的市场偏向于ToC,而遥感更偏向于ToB,遥感的市场空间会更小;
三是中国遥感区域主要聚焦于中国国土及周边,没有全球扩张(军事)的需求。
全球在轨的遥感卫星占比只有18%(1192颗),而通信卫星是72%(4823颗)。中国在轨更多的是遥感卫星,占比约六成(332/541),“高分”、“风云”、“海洋”、“资源”四系列是国家四大骨干卫星遥感网络。
头部民营商业卫星公司:长光卫星的“吉林一号”、天仪研究院的“海丝一号”和“巢湖一号”、微纳星空的“泰景系列”、航宇微的“珠海一号”等都是遥感卫星。
以上↑
产业判断 个人判断,近两年的可回收火箭进度是略超预期的,可回收试验箭5年内可以成功,比肩猎鹰9的商业化规模发射要在10年外。卫星方面,中国不可能组类“星链”的通信星座,国星和垣信的万星星座进度一定会大幅低于预期,即便未来可回收运力实现了,也只会更多的发射占频保轨战略小卫星,而不是纯商业卫星。在可见的时间线内,商业卫星没有大未来。
至于二级市场,人形机器人好歹可以炒未来,低空经济好歹可以炒政策,商业卫星炒什么?绝对的龙一“长光卫星”上A都被否了,还在那死命的吹虫二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