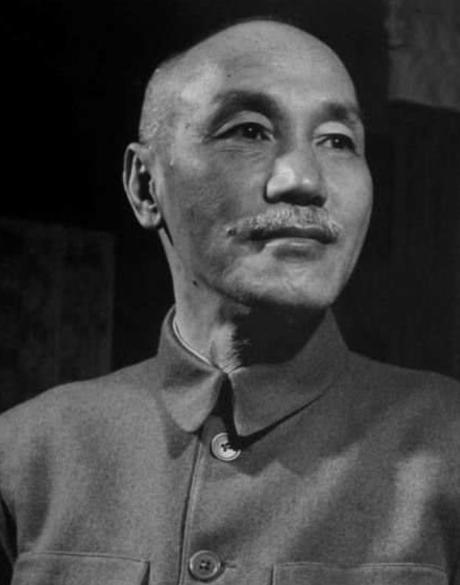蒋介石自1915年开始写日记,至1972年因手肌萎缩停笔,持续57年,现存53年共63册 。这一记录远超同时代政治人物,形成了一部独特的“个人政治史”,它既是研究蒋本人思想与行为的“钥匙”,也是理解国民党政权兴衰的“镜子”。 1972年,台北士林官邸的书房里,85岁的蒋介石颤抖着放下手中的笔。 这本写了57年的日记,停在“手肌萎缩,难以执笔”的最后一行。 63册、53年、20000余页,这部比《曾国藩日记》还厚重半倍的“私人史”,不仅是他个人的“修身账本”,更是打开国民党政权兴衰的“密码箱”。 杨天石说:“不看蒋日记,历史研究缺块拼图;但信它,容易掉进他的‘心机陷阱’。” 蒋介石的日记,始于1915年的上海。 28岁的他,那时还是个“混不吝”的纨绔子弟,逛窑子、赌钱、跟青帮混,日记里满是“见美色起邪念”“终日嬉游”的忏悔。 转机发生在1916年。 导师陈其美被袁世凯暗杀,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你该做个像曾文正公那样的人。” 曾国藩的“日课十二条”,成了蒋介石的新信仰。 他开始效仿这位晚清名臣,用笔每日记录克制欲望、反省言行、研读经典。 1919年在香港,他见了位叫“介眉”的妓 女,当晚日记里就记:“心生邪念,记过一次。” 后来他总想起这个女人,便在日记里反复写“须戒之”“不可忘本”。 这种自我敲打,他坚持了一辈子。 哪怕1949年后退守台湾,手抖得握不住笔,他仍在纸上写:“今日又动肝火,需自省。” 写日记,成了他与内心“恶念”较劲的武器。 翻开蒋日记,像在看一场持续半世纪的“吐槽大会”。 他对国民党军政大员的点评,犀利得近乎刻薄。 对陈诚这个被他视为“接班人”的干将,却总让他头疼。 1943年陈诚反对二次入缅作战,蒋骂他“跋扈恣睢,纪律荡然”。 1947年东北“剿共”失利,蒋写“辞修对政策猜疑诽谤,失却信心”。 退守台湾后,更疑他“与胡适、梅贻琦勾结,意图夺经国之权”。 对孙科孙中山之子,在他眼里“庸暗如阿斗”。 1948年孙科竞选副总统,蒋痛斥其“是非不明,狂妄糊涂”,甚至断言“总理一生为其所卖”。 对桂系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功,他连写六个“恨”。 白崇禧逼宫“亥敬电”,他骂“叛迹更显,恶毒阴险”。 白崇禧猝死家中,他暗喜“能善终是幸运”,又补一句“罪有应得”。 对孔宋,孔祥熙被夸“财政功臣”,宋子文却被骂“奸诈卑劣,养虎为患”。 1945年宋子文任行政院长搞崩经济,蒋在日记里写“误国误党,党国罪人”。 连空军司令周至柔作战不力,他都骂“枪毙十次不够”。 戴笠坠机后,他哀叹“雨农不死,大陆不失”。 这些骂声,不是简单的情绪宣泄,这是他与政敌的心理战,是权力场上的“软刀子”。 但日记不全是真话。 杨天石说它“可信度85分”,剩下的15分,藏在蒋的“小心思”里。 刺杀汪精卫的“美颜”。 1938年戴笠刺杀汪精卫失败,蒋在日记里写“不幸中之万幸”。 这“幸运”藏着什么? 汪精卫是党内元老,蒋本想留他去欧洲避风头,结果戴笠搞砸了。 写“万幸”,是在掩盖自己“不想彻底撕破脸”的妥协。 对宋美龄的隐喻。 晚年他总引用孔子“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1972年病重时,他写“与女人、小人相处费劲”。 “女人”是宋美龄,“小人”是她的外甥孔令侃。 母子俩总给他添堵,他只能在日记里发发牢骚,不敢明说。 还有对戴笠的“怀念”。 戴笠死后,他夸“雨农不死,大陆不失”。 可戴笠生前权倾朝野,蒋对他又爱又怕。 这句“夸”,更像对“工具人”的惋惜。 戴笠帮他铲除异己,没了这把刀,他更孤独。 这些日记,最终成了历史的双面镜。 一面照见他的自我修养,一面照见他的权谋算计。 他写“克己”,却纵容特务系统制造白色恐怖。 他骂“叛徒”,自己也对盟友下狠手。 他标榜“为民”,却在大陆溃败时带走了黄金、文物和知识分子。 但这些矛盾,恰恰构成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他不是神,是个会挣扎、会虚伪、会后悔的凡人。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 他的日记被封存在“国史馆”,成了学者研究的“富矿”。 有人从里面读出了他的“圣人梦”,有人读出了他的“权力焦虑”,更多人读出了一个时代的动荡与悲欢。 正如杨天石所说:“看蒋日记,要带着‘显微镜’和‘望远镜’,显微镜看他的小心思,望远镜看他的大历史。” 主要信源:(台海网——《蒋中正日记(1937-1947)》将在台湾出版 蒋介石日记(蒋介石自1915年至... - 百度百科 澎湃新闻——从日记看蒋介石晚年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