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担心中国能打败日本,担心的是打败日本之后,我们又开始发善心了。 中华民族有天然的善根,对被打败的民族从来没有赶尽杀绝的习惯,除非他们一再背信弃义,比如准噶尔汗国。日本人自己常说最懂中国人,看看他们的文字就明白——既用汉字,又掺着平假名和片假名。这种组合,正好体现他们想学中国,又偏要搞出不同的那股劲。 这是个性格别扭的民族,外面一脸和气,刀子却藏在笑容后面,刚刚还在鞠躬,下一刻可能就抄家伙动手,这种表里不一贯穿历史。 他们的文字故事得从汉字传入说起,公元一世纪左右,佛经把汉字带到了日本,早期,日本人照搬汉字发音写自家话。 等到平安时代,他们开始另起炉灶,一部分从汉字草书简化出平假名,另一部分从汉字的偏旁部首造出片假名,一个用来写本土词,一个用来标外来语,结果就是三套符号同堂使用——既想学,又想区别,这种矛盾不只在文字上,骨子里也一样。 晚清的左宗棠曾总结过这个民族的毛病,说他们只懂小礼节,不讲大义,注重细枝末节,却不顾廉耻;敬畏强者,却不知感恩;强时劫掠,弱时低头。 翻成白话,就是表面功夫做得漂亮,心里不服,机会一到马上翻脸,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弱的时候,积极派出遣唐使来求学,吸收中国制度文化;一旦国家强了,就立刻出兵扩张。 从明代倭寇扰海,到近代全面侵华,都是这套模式:弱时依附,强时侵略。战败后,他们会摆出认错的姿态,却从不真正服气,等待下一次翻盘。 问题在于,我们的民族习惯在击败对手之后收刀留人。明朝对蒙古各部、清朝对不少归附少数民族,都是在胜利后允许他们继续生存,甚至保留部分自治,这背后是文化上的自信,也是天性里的善良,但这种善良,不是没有底线。 准噶尔汗国就是例外。这个源自卫拉特蒙古的政权,在噶尔丹领导下,不断南侵骚扰清边,康熙三次亲征才逼得噶尔丹败走自尽。 雍正时期他们又起兵,直到乾隆年间更是反复叛乱,尤其是阿睦尔撒纳,前脚请求清军帮他坐上汗位,后脚就反叛,这样的反复,让乾隆彻底断了宽恕的念头,下令全力剿灭,结果就是,准噶尔这个名字彻底消失在历史中。 把这段历史和日本的行事风格对比,就会发现背后的相似性,他们看准了我们不会赶尽杀绝,在弱的时候用低姿态换取喘息机会,但内心的野心和敌意一直存在。 一旦再度强大,便恢复侵略本性,历史上他们屡次侵略,败后也只是暂时偃旗息鼓,并未真正放下敌意。 所以,真正值得担心的,不是打一场胜仗,而是在胜利之后该如何应对这个“畏威而不怀德”的邻居。 对这样的对手,如果只是再次宽容,历史很可能会重演,准噶尔的结局提醒我们,善良可以有,但必须有边界,在面对这样反复无常的民族时,松懈也许就是为下一次冲突埋下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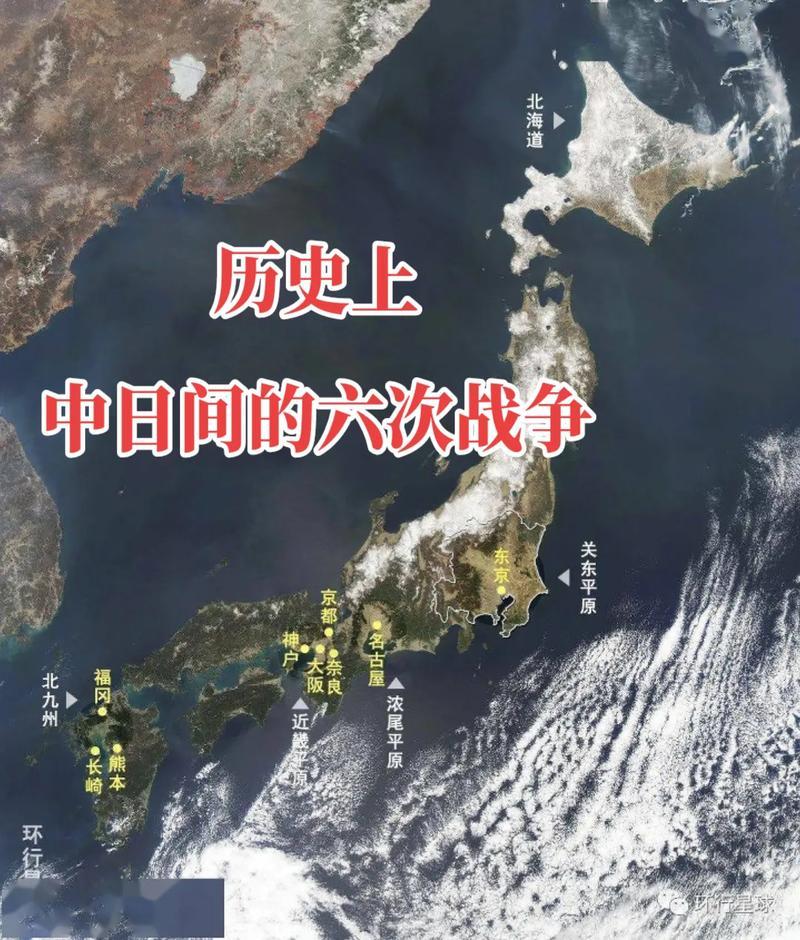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