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李叔同千里迢迢将母亲的棺椁从上海带回天津老家。不料,族人口口声声“小妾不能从正门入,直接到坟地埋了”,将棺木挡在了门外…… 一只喜鹊衔着松枝飞进了产房,在天津著名的“桐达”李家,这被视作佛赐的祥瑞,那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男婴叫李叔同,日后他将那根干枯的松枝终生带在身边,仿佛是在纪念那个给他生命的女人,母亲王凤玲。 这是1880年,李家权势熏天,经营盐务与钱庄的父亲李世珍已是68岁的垂暮老人,而王凤玲不过是个16岁的女孩,在这个拥有豪门虚名的深宅大院里,她因为出身微寒,进门那天花轿甚至只能走侧门,这份卑微像一根刺,不仅扎在她心头,更深深刺痛了年幼的李叔同。 尽管只有五岁时父亲便撒手人寰,李叔同依然在锦衣玉食中长大,早已看遍了泼天富贵,但这并没有让他快乐,母亲在大家族夹缝中求生存的眼泪,成了他童年最深刻的底色,十四岁那年,他才华横溢成了天津卫的才子,想在戏曲的生旦净末丑里寻找寄托。 甚至与名伶杨翠喜互引为知己,可惜这段情缘终究敌不过世俗权势,心上人被重金买走送作权贵玩物,母亲又为了所谓的门风逼他娶了不爱的富商之女,那年他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为了生计还在沪学会翻译外文,家里却传来了噩耗。 最疼他的母亲在郁郁寡欢中病逝,年仅42岁,悲痛欲绝的李叔同护送棺椁千里北上,只为圆母亲一个落叶归根的梦,可当他伫立在李家大宅前,那扇曾经侮辱过母亲的“正门”再次紧闭。那些族中长辈冷冰冰地甩下一句:“外丧不进门,把棺材直接拉去坟地。” 那一刻,过往母亲所受的冷眼与屈辱统统涌上心头,一向沉默温吞的李叔同爆发了,他不仅要进门,还要把几千年的旧俗砸个粉碎,“必须走正门,谁敢拦,我就跟谁拼了”这声嘶吼震住了全族人。 棺椁最终堂堂正正抬进了李家大厅,但这还不够,在那个满城尽是披麻戴孝的年代,他为母亲举办了一场惊世骇俗的葬礼:没有哭丧,不收银钱,不论官商,四百多人身着黑衣,他在墓前抚琴,让孩童们唱着他亲自谱写的哀歌。 这场被视为“中国新式葬礼开端”的仪式,轰动了整个天津卫,可在喧嚣过后,李叔同心里那盏灯却灭了,母亲走后,世间再无牵挂,那些曾经视若珍宝的功名利禄,忽然变得索然无味。 有人说他心太狠,当他在西湖断桥边与日本妻子做最后的告别时,两舟相向,那个曾经深爱他的女子泪眼婆娑地问:“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他没有回头,只留下一句振聋发聩的:“爱,就是慈悲”。 这句“慈悲”里,藏着太多的痛,若未见过众生皆苦,未尝过锥心之痛,又怎会懂得何为真正的慈悲,出家后的二十四年里,他持戒之严近乎苛刻,甚至被人称为“苦行僧”曾经挥金如土的阔少爷,如今衣服破了补了又补,身体病弱也拒绝服药。 只是日夜念佛,在这份极度的自律中,他仿佛找到了真正的自由,现代人总把“焦虑”挂在嘴边,在这快节奏的内卷中,或许我们都该读读弘一法师那本《人生没什么不可放下》无论是商业巨擘曹德旺,还是文坛斗士鲁迅,亦或是唱着《送别》痛哭流涕的朴树。 都在他的文字里找到了灵魂的出口,正如张爱玲所言,在这个红尘之外的高僧面前,哪怕高傲如她,也只剩谦卑,1942年,这位曾经的富家公子预感到大限将至,他断绝了一切尘缘,不再进食,在那张留给世人最后的墨宝上,他没有写什么豪言壮语。 只留下了“悲欣交集”四个字,人这一辈子,手就那么大,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从“桐达”李家的钟鸣鼎食,到古寺青灯的一碗白粥,他用半生繁华换了半生彻悟。 既然谁都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那些曾以为过不去的坎,如今看来,也不过是过眼云烟,与其执着于过去和未来,不如活好当下的每一个瞬间,因为除了这一刻的呼吸,没有任何东西真正属于你。 信息来源:海峡新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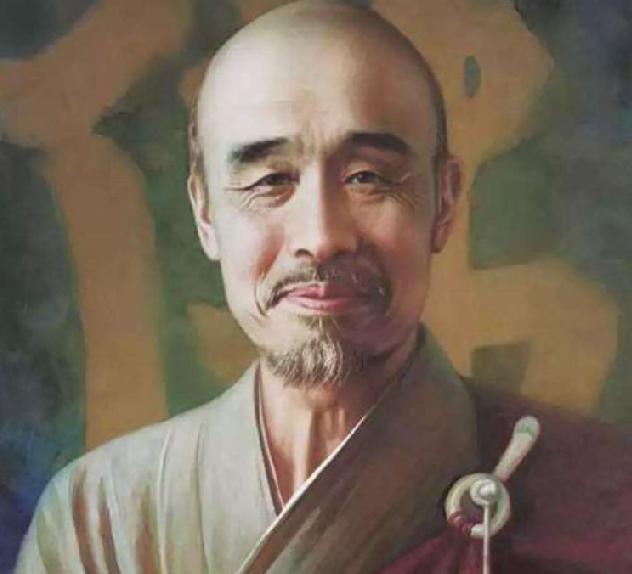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