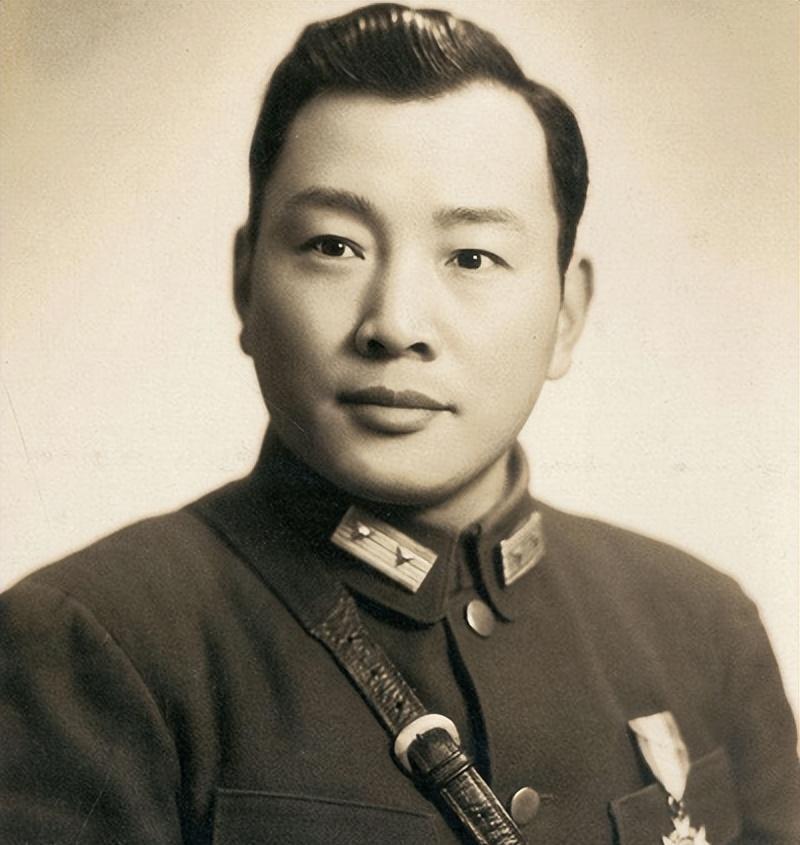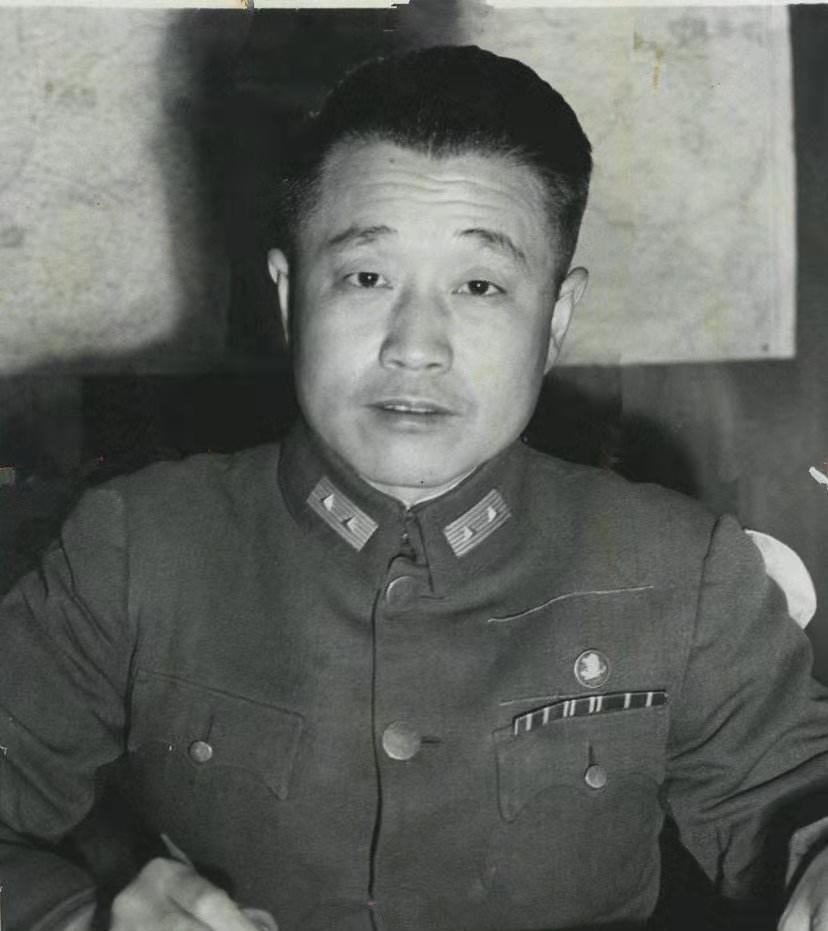1959年10月4日,作为第一批被批准特赦的战犯,杜聿明走出了功德林监狱,一代名将的人生从此开始转变。 他怀里揣着特赦通知书,纸张边角被汗水浸得发皱,就像他此刻的心情,说不清是轻松还是沉重。 在功德林的日子里,医生每天都会来查房。 杜聿明记得第一次拿到链霉素的那天,护士说这药要从苏联进口,专门给他治肺结核的。 当时他正趴在桌上写《淮海战役回忆》,钢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墨水晕开一个小小的黑点。 同屋的宋希濂凑过来看,脊椎上的护腰支架硌得椅子吱呀响,两人对着摊开的地图,忽然都没了话。 那年冬天,西花厅的暖气让玻璃窗蒙上了层薄雾。 周总理握着杜聿明的手,说起他弟弟杜聿德1928年牺牲的事,声音轻得像落雪。 你看,一家人早就在为同一个目标奋斗了。 总理的手指划过桌上的照片,那是杜聿明失散多年的女儿杜致礼,正站在哈佛大学的草坪上笑。 后来杜聿明才知道,为了找这张照片,工作人员跑了三个档案馆。 1963年春节,曹秀清从美国回来那天,杜聿明在机场转了三圈。 妻子穿着他熟悉的蓝色旗袍,头发比记忆里白了些,手里拎着的皮箱边角磨掉了漆。 两人走到出口时,曹秀清忽然说了句北京的冬天比徐州冷,杜聿明赶紧把大衣脱下来裹在她身上,就像1937年送她去后方时那样。 韶山冲的稻田在1973年夏天绿得发亮。 宋希濂站在解放战展馆门口不肯进去,败军之将哪有脸看这些。 杜聿明拍了拍他肩膀,说起陈毅当年自请处分的事,打仗输了不丢人,不敢承认才丢人。 展馆里的油灯还亮着,玻璃柜里的作战地图上,红铅笔标出的箭头密密麻麻,像极了功德林学习室里那些被圈点的《论持久战》。 晚年整理文史资料时,杜聿明常对着台灯一坐就是半夜。 宋希濂送来的护腰垫放在椅背上,磨得发亮的皮革上,还留着当年监狱医务室的编号。 书架第三层摆着十二封泛黄的信,都是写给台湾旧部的,最后一封结尾写着两岸终会统一,届时共饮茅台。 如今这些信成了历史档案馆的展品,玻璃展柜里的灯光,总让他想起功德林那个治肺结核的链霉素小瓶,在暗夜里透着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