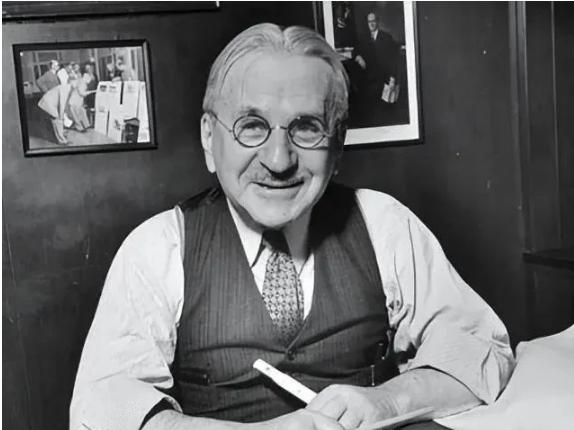1913年,蒙古乌兰巴托,一名女子因犯通奸罪,被实施“箱刑”。 木箱的缝隙里露出半只冻得发紫的脚,戈壁滩的风卷着沙砾打在箱壁上,像无数根细针在刺。 这个被剥去外衣的女人蜷缩在不足一立方米的空间里,罪名是“玷污家族荣誉”,而所谓的证据,不过是男主人酒后的一句戏言。 阿尔伯特·卡恩的镜头悄悄对准了这一幕。 这位法国银行家正在进行他的“地球档案”计划,原本想记录草原的游牧风情,却撞见了文明外衣下的野蛮。 他后来在日记里写“木箱上的锁锈得厉害,像极了这里女人的命运”,最终没敢按下快门。 类似的箱子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 中国南方水乡的“浸猪笼”会把人绑在竹笼里沉入河底,印度乡村的石刑让受害者被亲友用石头砸死。 这些刑罚都有个共同点专为女性设计,仿佛女人的身体天生就该是道德的试验场。 那个蒙古女人其实是个寡妇,为了养活孩子才去给权贵打工。 男主人强迫她发生关系时,她拼命反抗过,指甲缝里还留着对方的皮肉。 可当女主人发现后,挨打的是她,被定罪的还是她。 这种双重标准,在19世纪的全球都在上演。 1921年蒙古革命后,新政府第一件事就是修订刑法。 当法学家翻开旧法典,发现光是针对女性的“道德罪名”就有27条,其中13条可以判处死刑。 1926年,箱刑被正式废除,但戈壁滩上的老人们还记得,最后一个被装进木箱的女人,在里面唱了三天三夜的草原长调。 现在乌兰巴托的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个复制的木箱。 玻璃展柜旁放着两张照片:左边是1913年卡恩拍摄的沙漠,右边是2023年女性议员们举着反家暴法案的合影。 箱子上的裂痕被灯光照亮,像一道愈合中的伤疤。 前几天我去参观时,遇到个蒙古族女孩正在写生。 她画的不是箱刑的残酷,而是箱子缝隙里长出的一株骆驼刺。 “老师说这叫生命的韧性,”她指着画纸告诉我,“就像我们女人,再小的缝隙也能钻出来。”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文明的进步从来不是忘记过去,而是把曾经的枷锁,变成后来者的踏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