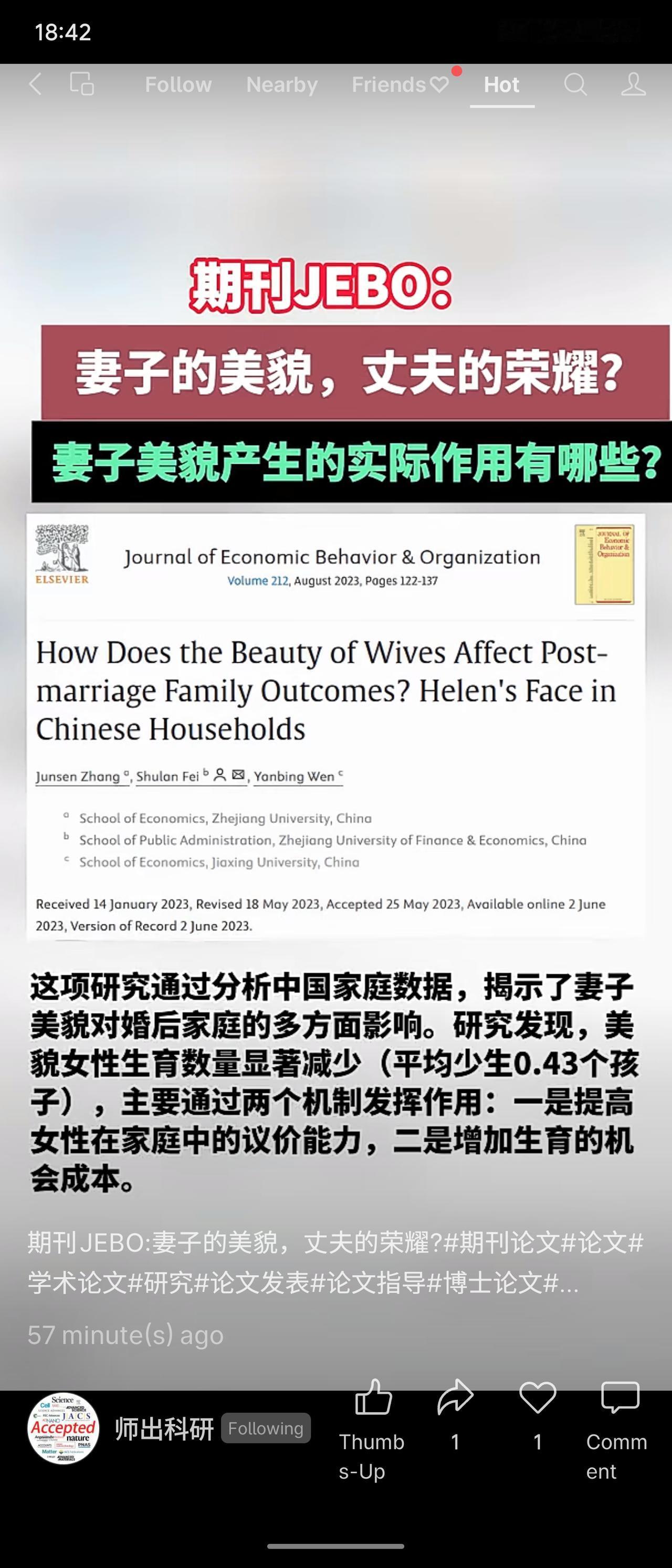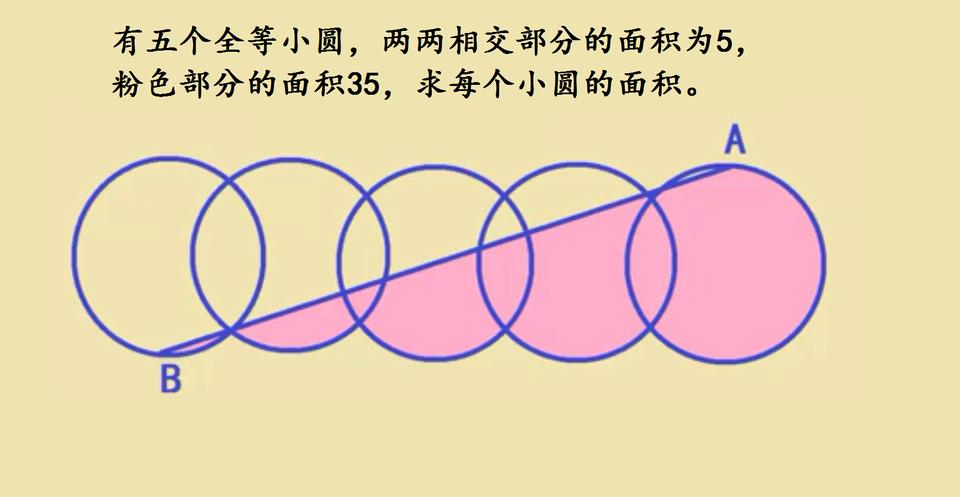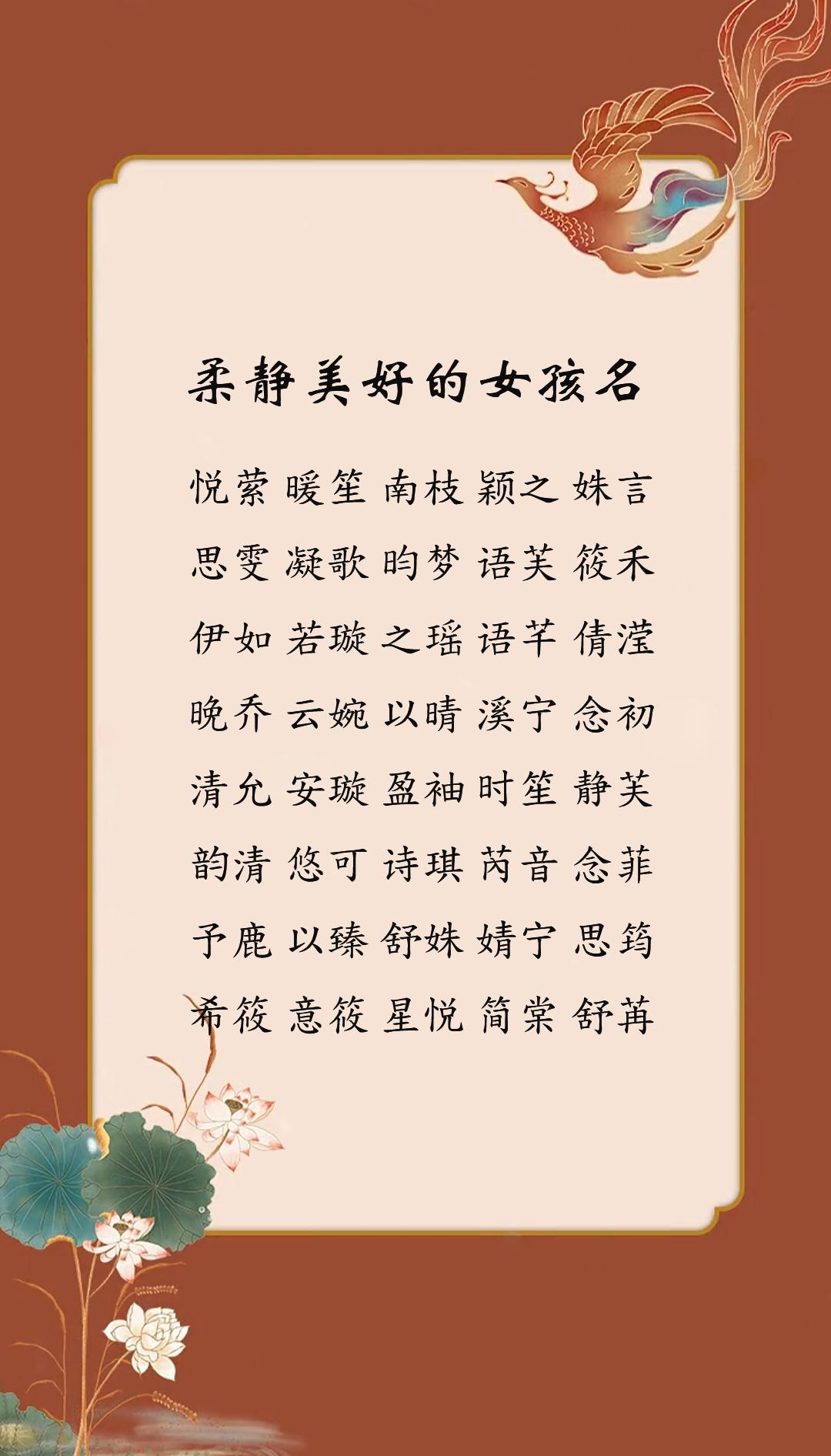坐月子时,婆婆天天煮糙米稀饭,我吃得实在咽不下,跟婆婆说要不明天煮点鸡汤吧,天天吃这个孩子没奶水吃。婆婆听完立刻怼回我:"我们当年都这么吃。" 我看着她转身进厨房的背影,蓝布围裙边角磨得起了毛,左手袖口沾着片枯黄的菜叶,像是早上择菜时没擦干净。这已经是第十二天了,每天掀开锅盖都是褐色的糙米粥,上面飘着几粒蔫巴巴的咸菜,偶尔卧个荷包蛋,蛋白边缘都煎糊了。 夜里孩子饿得直哭,小拳头攥得紧紧的,我抱着他在屋里来回走,乳房胀得像石头,奶水却细得像线。月嫂悄悄说:"姐,你婆婆是不是不太会做饭啊?"这话让我心里一动——上周我看见她在超市对着菜谱发呆,手指在"产妇营养汤谱"那页摩挲了半天,最后还是拎了袋糙米出来。 第二天我起大早想偷偷炖点鲫鱼汤,刚把鱼放进锅,就听见婆婆在客厅打电话:"...手术费还差两千...我这儿有,别跟孩子说..."我端着锅僵在厨房门口,想起上个月老公骑车摔了腿,他只说擦破点皮,原来偷偷做了手术。婆婆挂了电话看见我,慌忙把手机揣进兜里:"你起这么早干啥?快回屋躺着。" 那天下午我假装散步,去社区医院问老公的病历,护士说:"你是他家属吧?他妈妈昨天来交了五千,说不够再找她,老太太自己膝盖疼得站不住,还硬撑着没说。"我站在医院走廊,看着窗外婆婆拎着菜篮蹒跚走远的背影,忽然想起她总说"当年我生你老公,一顿能喝三碗糙米汤",却从没提过那时她刚做完阑尾炎手术,喝米汤是因为没钱买止痛药。 晚上我把攒的工资卡塞进她枕头下,附了张纸条:"妈,明天我想吃您包的菜团子,就用糙米面做。"第二天一早厨房飘来香味,她正坐在小板凳上揉面,膝盖上搭着厚毛毯,面团揉得不太匀,可菜馅里卧着两个打碎的土鸡蛋——那是她每天去早市捡的碎蛋,说"便宜,给娃攒着补营养"。 "其实我知道该喝鸡汤,"她忽然红了眼眶,"可你老公手术费还差三千,我怕买了鸡你们又要掏钱,你坐月子本来就该吃好的..."我蹲下来帮她揉面,手指碰到她手背的老茧,那上面还有个新伤口,是昨天给我煮姜汤时烫的。 现在孩子满月了,奶水早就够吃。婆婆每天早上五点去早市,回来时菜篮里总有只活蹦乱跳的鸡,说"张婶教我挑的,黄毛的最下奶"。她还是会煮糙米粥,但里面总卧着个流心蛋,说"你妈当年教我的,糙米粥养肠胃,鸡蛋补气血"。有天我翻她床头柜,看见那本磨卷边的"月子禁忌"里夹着张缴费单,是老公的手术费,下面用铅笔写着:"还差一千,明天去捡塑料瓶"。 原来那些让我们皱眉的糙米饭,藏着的不是固执,是"我吃过的苦,不想让你们知道"的疼惜;那些红着脸的解释,说到底都是"怕你们担心"的温柔。生活啊,就是把硬邦邦的难处,熬成一锅暖烘烘的粥,让不同年代的爱,在咕嘟咕嘟的声响里,慢慢炖出最贴心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