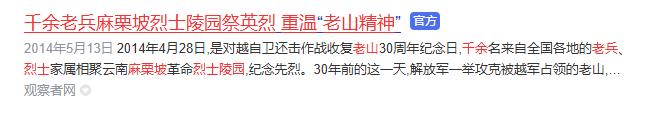这是1985年1月20日,从老山某阵地争夺战中运回来的部分烈士遗体。由于战争太惨烈,从战场上抢运回来的烈士又太多,火化间一下子安置不了全部遗体,只能把部分遗体临时安放在火葬场前的空地上。那种场面,让战友们泪如雨下,让路过的村民久久不肯离去。 那天是个阴冷的冬日,风刮得人脸生疼,火化场前的空地上躺着一排排烈士,他们还穿着带着泥土和烟尘的军装,有的指尖还紧紧握着枪,冻得发紫也没有松开。 没人大声说话,只有风声和压抑的抽泣声。 战友们一个个蹲在地上,用冻得通红的手,一点点擦着烈士的脸。 擦着擦着,眉眼也红了。 这些遗体是从那拉口方向送下来的。几天前前线爆发激战,敌人朝阵地投下炮火,部队拼死守住阵地,战士们死伤惨重。 一辆接一辆的红十字军车拉来遗体,火化场一下子容纳不了太多,只好先放在外面。 那天到了29具,几乎每一具都是肢体残缺,血肉模糊。 有的战士被炸得看不出模样,有的只剩破碎的残躯。 火化组是南京军区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下设的,组建的时候就是为了处理烈士遗体。 带队的是韩亚清,一个平时负责组织工作的干事。他带着二十多个人,提前去一线学了怎么处理遗体,也自己设计了表格,记录每一个烈士的姓名、单位、伤情、遗物情况。 每一具遗体都要经过接收、清洗整容、火化、登记、装盒入库五道工序,不允许出一点差错。 韩亚清本来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死亡,但当这29具年轻的身体堆在他眼前时,那种锥心的痛还是一下子压住了他。 他们很多人才十九岁,刚写完入党申请书,有的人连给家里报个平安都没来得及。 这些人不是新闻里的数字,是亲手擦拭过脸庞的兄弟。 那天晚上,火化场断电了,墙上挂着煤油灯,灯光忽明忽暗。 柴油炉轰鸣着,空气里全是油烟和血腥味。韩亚清和军医们连夜处理遗体,有的战士半个头颅被削去,他就用棉花和石膏一点点修补;有的四肢僵硬,为了换上干净的军装,他只能用热毛巾反复敷着,用手捂着,甚至要把脚抱在怀里,直到能把裤腿套进去。 那一刻,烈士们不是冰冷的尸体,而是沉睡的弟弟,是远在他乡的亲人。 韩亚清说,他们是在替这些战士的母亲,给他们洗最后一次脸,穿最后一套衣服。 有一位烈士的口袋里,还塞着一封没寄出的信,纸上只隐约能辨认出“妈妈,我很好”四个字。韩亚清一看见就蹲在墙角哭了。 更让人难受的是,有一次夜里一辆车开进火化场,只带来一个麻袋。 打开一看,是18位猫耳洞战士的残骸,被炮火直接炸碎,只抢回了一袋血肉模糊的碎片。 韩亚清和战友们一边流泪一边用竹筛仔细分拣,生怕漏掉哪怕一小块骨头。 最后火化后,只找出了五块能辨认的骨头。 村子里的人也来了。一位老大娘拎着壶水,蹲下来给烈士擦手,一碰到衣袖就哭倒在地。 几个年轻姑娘找来塑料布,小心地把遗体盖住,像是怕他们着凉。 几个壮劳力铲了些土,在空地边搭了个挡风的土坡,没人说话,动作都轻得像怕惊扰谁的梦。 这些烈士大多数连像样的照片都没留下,很多人也没有留下什么遗物。 可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人等着回家的。 他们不是雕塑,也不是课本上的名字,是村里二娃,是邻家弟弟,是家里盼着过年的儿子。 他们在最冷的日子,守着最危险的阵地,挡住了敌人的炮火,换来了边境的平安。 从1984年老山战事开始,南京军区第一师是在1984年底轮上阵地的,一直到1985年5月才退防。 半年时间打退了敌人好几轮进攻,毙伤敌军数千人,自己也牺牲了三百多人。 轮战结束后,部队安排骨灰移交,接待烈士家属,韩亚清又亲自去阵地调查了36位无遗体战士的情况,找目击者确认他们的牺牲方式,确保上报信息准确,不让家属多想。 麻栗坡烈士陵园里,现在还安放着他们的骨灰。 每年清明和节日,总有人来祭奠。只是时间过去久了,很多名字不再被提起,很多故事没人再说起。有人会觉得这些牺牲值不值,也有人会拿战争当笑话,但真正走过那片空地,看过那些冻僵的手和血染的信的人,是不会说出这些话的。 我们今天的每一口饭、每一个夜晚的安稳,都是他们用命换来的。 他们走了,但不是为了让人忘了他们,而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安心过日子。这份安稳越久,就越该记得是谁换来的。 信息来源: 千余老兵麻栗坡烈士陵园祭英烈 重温“老山精神”.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