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俗文学领域,一部作品要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经典,其自身无疑须具备两个层面的魅力:一是故事的魅力,一是叙事的魅力。

《西游记》,胡胜校注,中华书局2025年9月版。
所谓故事的魅力,就是故事本身(无论由谁来讲述,不管通过何种媒介来呈现)足够吸引人,能够迎合大众趣味、满足大众期待。所谓叙事的魅力,就是讲述故事的艺术性,讲述者如何在遵循特定媒介的艺术传统与表现成规的同时,实现风格化叙述;在充分照顾大众文化教养、知识结构、审美旨趣的基础上,将个体意识(特别是文人精神)注入文本,使其具有深刻的思想、丰富的意涵,同时彰显文笔与技巧,为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史家们提供无穷的阐释空间。
在这两方面,百回本《西游记》都满足了要求,且达到极高品位。
今人阅读《西游记》,理解《西游记》,甚至重新发现《西游记》的价值,也应当主要从这两个层面的魅力去考虑。
故事本身的魅力,是世代累积而成的。
它以玄奘西行求法的历史事迹为本事,在后来演化、传播过程中,逐渐脱离历史本相,羼入大量虚构、幻想,最终蜕变为一个庞大的神魔故事群落。
玄奘,俗名陈祎,河南陈留(今洛阳)人。他于公元628—645年,用时十七年,历尽险阻,到五天竺(今印度)求法。归国时,带回佛经657部,1330卷。又用了十九年的时间,与门徒、同行埋头译经。他为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万古风猷,一人而已”。

邮票《玄奘》
玄奘回国后应唐太宗之请,口述西行闻见,由门徒辨机执笔,写成《大唐西域记》。其后,门徒慧立、彦悰又撰写《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尽管两书在描述中已夹杂不少神异色彩,有“神化”倾向,但依然属于纪实文学范畴。
真正进入文艺的想象天地,虚构一个“西游”世界,始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部说唱作品刊刻于两宋,成书或许早在晚唐五代。
《取经诗话》中第一次出现了猴行者、深沙神等形象,尽管情节、形象都较为粗糙,叙事上也略显稚拙,却为后来的故事发展提供了不少原型(典型者如“经过女人国处”“入王母池之处”)。
其后又有元明时期的“西游”杂剧,存留下来的有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残帙)与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全本)。
后者现存本为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刊本,但创作应在元末明初或者更早。全剧计六本二十四出。这部早于百回本小说的剧作,集结了前代“西游”故事的精华。把原本独立发育的讲述玄奘出身的“江流故事”和孙悟空大闹天宫连接在了一起,增加了火龙化马、收水怪沙和尚、降黑猪精猪八戒、过女儿国、火焰山诸多情节。从一些文本证据(如剧中孙行者居住“花果山紫云罗洞”,与《取经诗话》所谓“花果山紫云洞”,仅一字之差)看,它应该属于《取经诗话》的故事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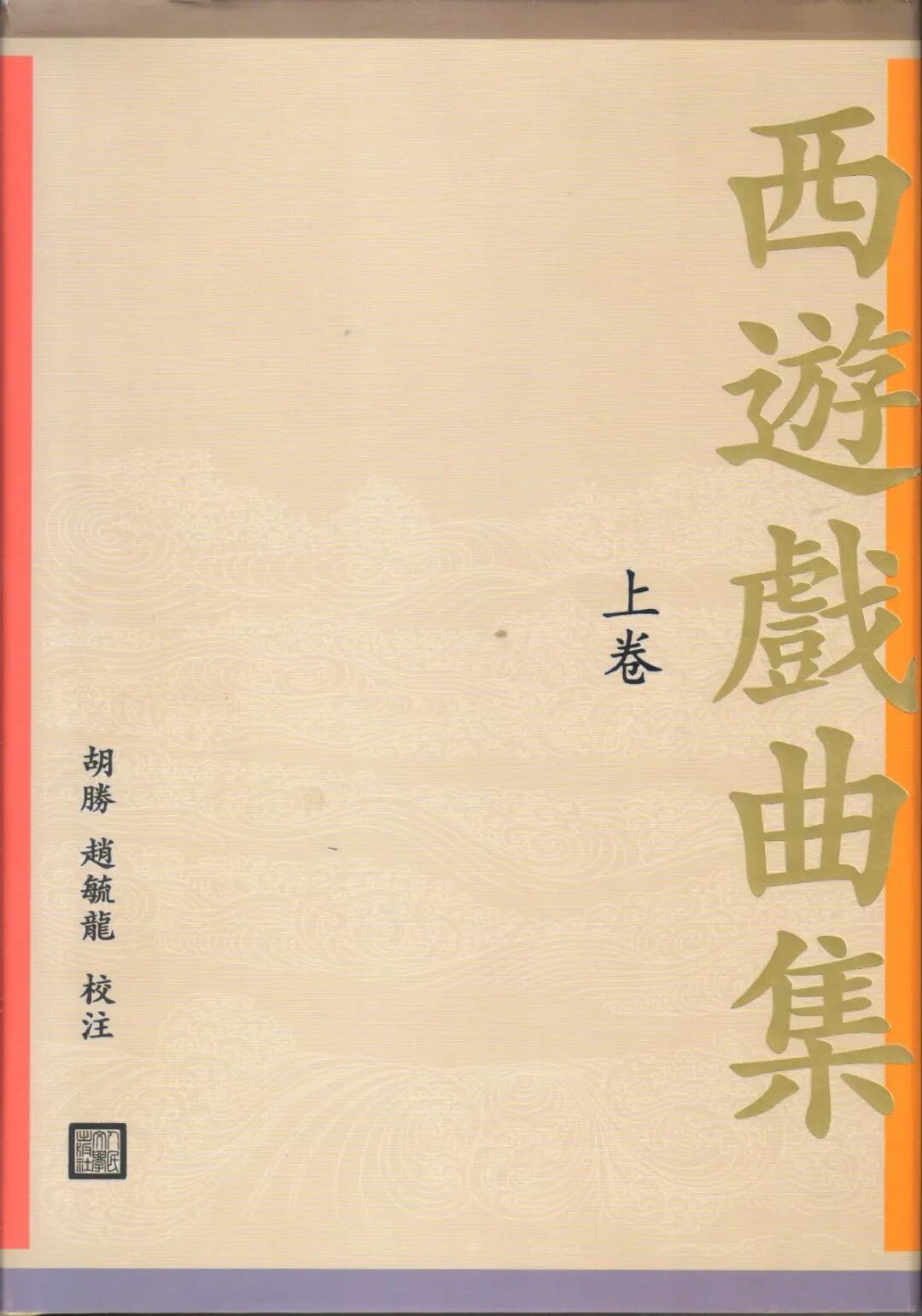
胡胜、赵毓龙校注《西游戏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部《西游记平话》。这部平话在国内久已失传,庆幸的是在古代朝鲜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尚存相关故事叙述和七条小注。
尽管属于转述性话语,但信息量够大,能够说明《平话》较杂剧又有所发展。西天路上的妖魔数量猛增,不仅有黑熊精、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还多了师陀国、棘钩洞、薄屎洞等处魔障。孙悟空的名号也由杂剧中的“通天大圣”蜕变为“齐天大圣”,他与沙和尚、朱八戒同往西天,最后法师证果旃檀佛如来,行者证果大力王菩萨,朱八戒证果香华会上净坛使者。
细化到具体情节,“车迟斗圣”一回占据了很大篇幅(可能就是《平话》的“大节目”之一),百回本的相关情节要素“云梯赌圣”“隔物猜枚”“油锅洗澡”等应有尽有,孙悟空顽皮、促狭的性格特征也已初见端倪。
此外,现存明代《永乐大典》残本卷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卷送字韵梦字类中的《梦斩泾河龙》,明确标注引自《西游记》,这段文字极有可能和《朴通事谚解》所引《西游记平话》属于同一部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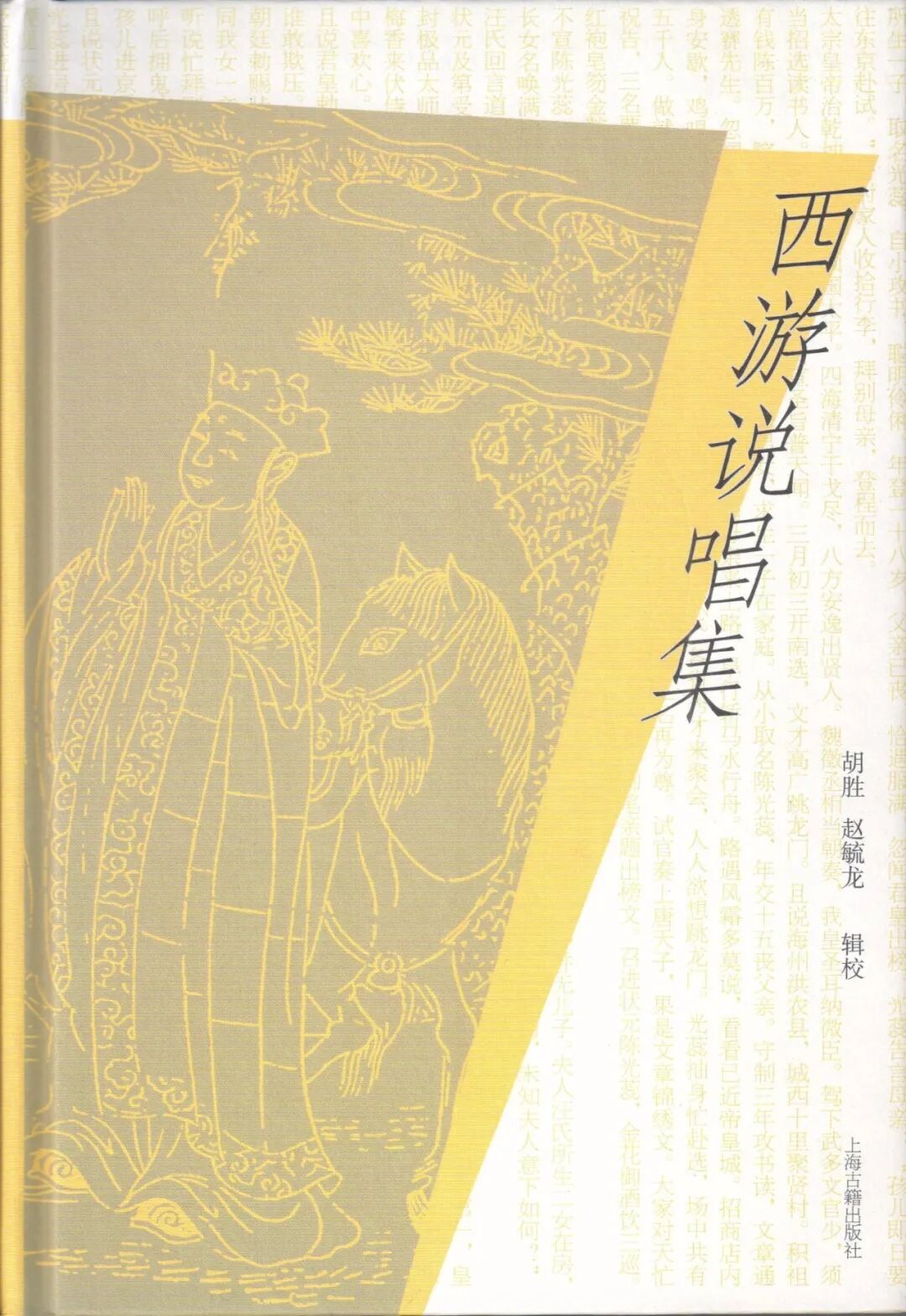
《西游说唱集》,胡胜、赵毓龙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将上述资料汇集在一起,大致可以勾勒出“西游”故事蜕变并逐渐形成一部集大成小说的发展、演进脉络。也有人认为:在世德堂百回本小说和平话之间似乎还应有一个过渡本(或称其为“前世本”),但因资料所限,无法清晰呈现,暂不论及。
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是目前所见该书的最早刊本。它是此前“西游”故事的集大成者。
当然,前此参与叙述“西游”故事的各部文本,不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还是《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也是其所处时代、所涉媒介的集大成者,都具有足够的叙事的魅力(否则,它们也不可能流传下来),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文本尚处于民间话语体系内,是集体叙述经验的多媒介、跨文本传递,即便由文人写定(如吴本杂剧、杨本杂剧),也是“媚俗”的成分居多,多多少少可以看到文人的知识与趣味,却很难发掘出文人精神。
至百回本《西游记》才完成了文人话语体系对传统故事的“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实现了具有极高品位的叙事。
这一质的蜕变,得益于百回本的作者(准确说应是“写定者”)。关于他的身份确认,直到今天仍有疑议。

《〈西游记〉与西游故事的传播、演化》
有清一代,从康熙间的《西游证道书》署名元代虞集的序言开始,将著作权给了全真教的丘处机(此前已有类似说法,但多是只言片语,在大众层面的影响很小)。
丘著说得以广泛流传,一方面是证道派评点本的极力鼓吹,《证道书》之后,无论《西游真诠》《西游原旨》等“权威”评点本,还是各种历史上不具名的道教徒阐释,虽然侧重不同,但在该书著作权方面高度一致;另一方面是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写过一本《长春真人西游记》,此书记述丘处机率领弟子西行觐见成吉思汗的事迹,涉及沿途的山川地理、土物风俗,是真正的“游记”,但此书收在“道藏”中,当时世俗民众见到的不多,以致“郢书燕说”。
清代其实已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但影响不大。直到现代学者鲁迅、胡适等人,根据天启《淮安府志》等相关文献,判定其为淮安人吴承恩,又经出版、传媒、教育等文化机构推波助澜,吴著说才流行起来,以至成为一个文学常识。至今小说的封皮、版权页,无一例外,都标注为“吴承恩”。
但这一看法的最大漏洞在于缺乏文献的“铁证”,无法成为定谳,所以反对的声浪一直也没有停息过。正所谓“破易立难”,颠覆常识固然需要勇气,但更需要证据,同时也要提供一个更具参考性的选项。

《西游记资料汇编》
目前看来,否定吴著说之后,学界还无法提供另一位令人信服(遑论达成共识)的作者。有人另提出唐新庵、阎蓬头、李春芳等不下十数位的“候选人”,不能说这些说法一点启发性没有,但它们目前的价值似乎也只在于启发性。
当然,学界仍要努力寻出作者,这是我们“知人论世”文学传统的自然体现,但在没有足够的“硬证”之前,我们不必急于一时,更不能在预设结论的情况下,选择性地使用材料来为以上候选人“背书”。
既然目前还无法提供一个能让正反双方都服膺的合适人选,我们权且将著作权挂在吴承恩名下。只要大家有足够耐心——说不定哪一天地下出土文物会给我们一个意外惊喜呢!
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写定者”是一位长期沉郁下僚的底层文人,他对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朽有太多的感触,他只能“以戏言寓诸幻笔”,把自己的人生感喟寄托于“无何有之乡”,借神魔以刺世,同时他也是一位叙述高手,具有超凡的文笔与技巧,于是便有了这本吞吐八荒、雄视古今的奇书问世。
百回本《西游记》之所以耐看,艺术上脱胎换骨是最直接的原因。原本散在的、独立发展的“西游”故事被巧妙黏结,作品的主次人物做了微调。

《破顽空:西游知识学》,赵毓龙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8月版。
原本的第一主人公三藏法师,让位于行者悟空,这样大闹天宫的故事模块和西天取经完成了无缝对接。连接这两大板块的粘合剂是“唐王入冥”。
正如清代一位评点者汪象旭所说:这一回是过接叙事之文,就像元人杂剧中的楔子,因为引出唐僧,必先用唐王建水陆道场,要说水陆大会,必先说地府还魂,而魂游地府是由于泾河老龙告阴状,老龙之死是由于犯天条,犯天条是由于迁怒卜人袁守诚,迁怒卜人则是由于渔樵问答。
这样环环相扣,把原本独立发育的“西游”故事顺畅而又自然的衔接起来。彰显文心之妙。除了结构上的调整,内容也极大丰富,对“九九八十一难”的组织,也是步步为营,煞费苦心。
尤其对前期“西游”故事的取舍增删,处处见出幻设叙事的功力。比如女儿国故事,在《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中,皆以之为重要“节目”,到了百回本写定者手中,又想象生发,精心布置,首先利用《诗话》中“若识女王姓名字,便是文殊与普贤”一句,将此事另行分化出活色生香的“四圣试禅心”一难。
同时考虑到杂剧中的女王见猎心喜,色欲难耐,有损一国之君的风度、体面,于是将人物一分为二,另造出蝎子精这一角色,承担“情色”笔墨,女王则回归人间国主的精神气质。如此处理,可谓恰到好处,各得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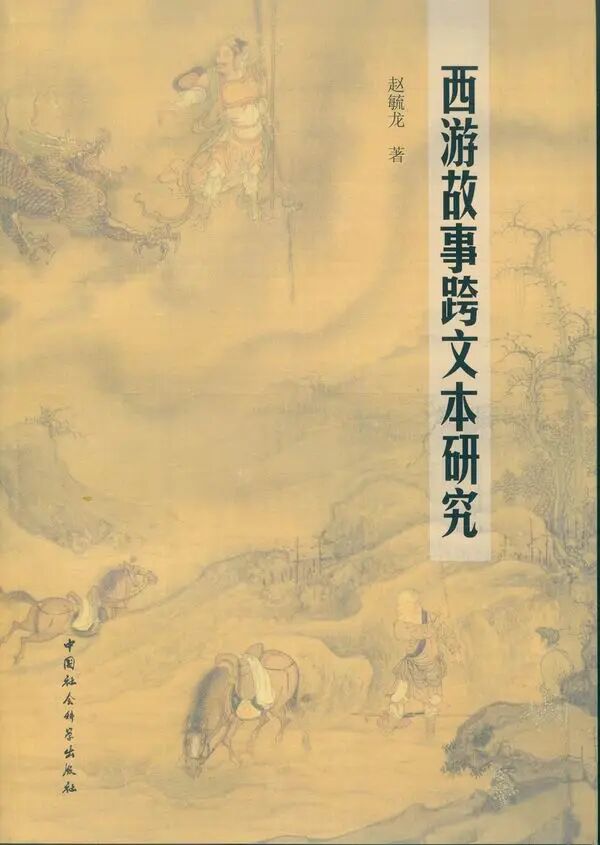
《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赵毓龙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再如百回本中的铁扇公主为红孩儿之母,向原型追溯,二者其实毫无瓜葛(如杨本杂剧中两个角色均登场,彼此并不相识),红孩儿的原型之一是嫔伽罗,其生母是大名鼎鼎的鬼子母。
“鬼母揭钵”故事在宋元时期就已经进入“西游”故事系统了,但百回本没有吸纳该故事,鬼子母形象被芟荑,红孩儿则留下来,“寄养”到铁扇公主的膝下(第四十二回收伏红孩儿,大圣去南海拜观音,出来迎接的诸神中出现了“鬼子母诸天”。
该形象于书中仅此一见,恰出现在红孩儿段落,算是写定者对故事进行“外科手术”时留下的刀口),母子之情也转嫁给了铁扇公主(尽管已移居翠云山芭蕉洞,拥有平息山火的芭蕉扇,但还残留了铁扇公主的名号),于是铁扇公主从传统“西游”故事中的“光杆儿司令”演变成了一位母子情深、夫妻反目的慈母、弃妇、怨妇,人物形象空前丰满。
类似人物形象的设置不止一处,如三藏的前身是“金蝉子”,金蝉子实为“金蝉”,在中国人传统文化心理中,“蝉”是长生的象征物(这一点可从考古报告所载,秦汉古墓中大量出土的蝉形玉琀等得到印证),于是令诸魔垂涎的唐僧肉就都有了原始的动力——用好药,有疗效;吃唐僧,得长生。
此外,法师的秀气外表与佛典中的释迦弟子阿傩有诸多重合之处,于是阿傩的“女色磨难”成了法师挥之不去的梦魇,遂有女妖渴望与其交欢,盗取元阳真气的情节。

《西游宝卷集》,胡胜、赵毓龙、赵鹏程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5月版。
可以说,“我佛如来的二弟子金蝉子转世”,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其实已为这一人物增添了多重内涵,也为妖魔劫掳唐僧的行动,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动力。
作者行文中,更是随手生春,文字之诙谐幽默,常人难以企及。孙悟空被玉帝招安,做了天宫的弼马温,实则是民间俗传:马厩中放猴可有效阻止瘟疫。
于是作者为猿猴之属的大圣“量身定作”了一个亘古无双的官职——弼马温(避马瘟)。作者之游戏笔墨,于此可见一斑。
最为关键的是,作者在花团锦簇的文字中渗透了自己浓烈的主体意识。在一个原本的宗教故事框架中楔入了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考,在滑稽、谑浪的文字背后隐藏了自己的一颗“傲世之心”。
虚幻的神魔世界成了真实人世的投影。作者对现实是失望的,所以他笔下的天、地、人三界皆非净土!他的希望、他的失望都在一部稗官之中!
百回本《西游记》问世之后,对其主旨的解读、阐释就没有停止过,“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鲁迅语)明代人认为作品的主题是收束放纵之心(“收放心”);清代人认为是阐扬金丹大道;今人认为是“安天医国”“诛奸尚贤”……
不同时代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准,“六经注我”式地去解读,这恰可说明:作为一部传世经典,《西游记》的蕴含永远不会被穷尽!

李卓吾评本《西游记》第一回
《西游记》问世以后,版本众多,世德堂百回本是现存最早刊本,此外的明刊本中《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版本相对精良,二本文字稍异,难分伯仲,可以相互参证。
1、本次校勘以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为底本,以日本广岛市立中央图书馆浅野文库藏本、河南省图书馆藏本、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本以及世德堂百回本等为参校本。
2、原书《题辞》、凡例、批语从略。
3、凡底本漫漶、阙文依参校本择善而从;明显错讹径改,个别差异较大者出注。
4、全书采用简体横排,凡古今字、异体字、通假字以及少量不合今日规范的字词等统一以通行规范写法;有些字词前后写法不一,尽量统一。如,埜—野;拏—拿;筭—算;女圣(恠)—怪;疋—匹;悮—误;觔斗(抖)—筋斗;惊呀—惊讶;抖搜—抖擞;耳躲—耳朵;吻喇—唿喇;丁(钉)—叮;吾党—吾当等。
5、注释主要是针对佛道术语,典章名物,方言俚语,诗词掌故等加以简明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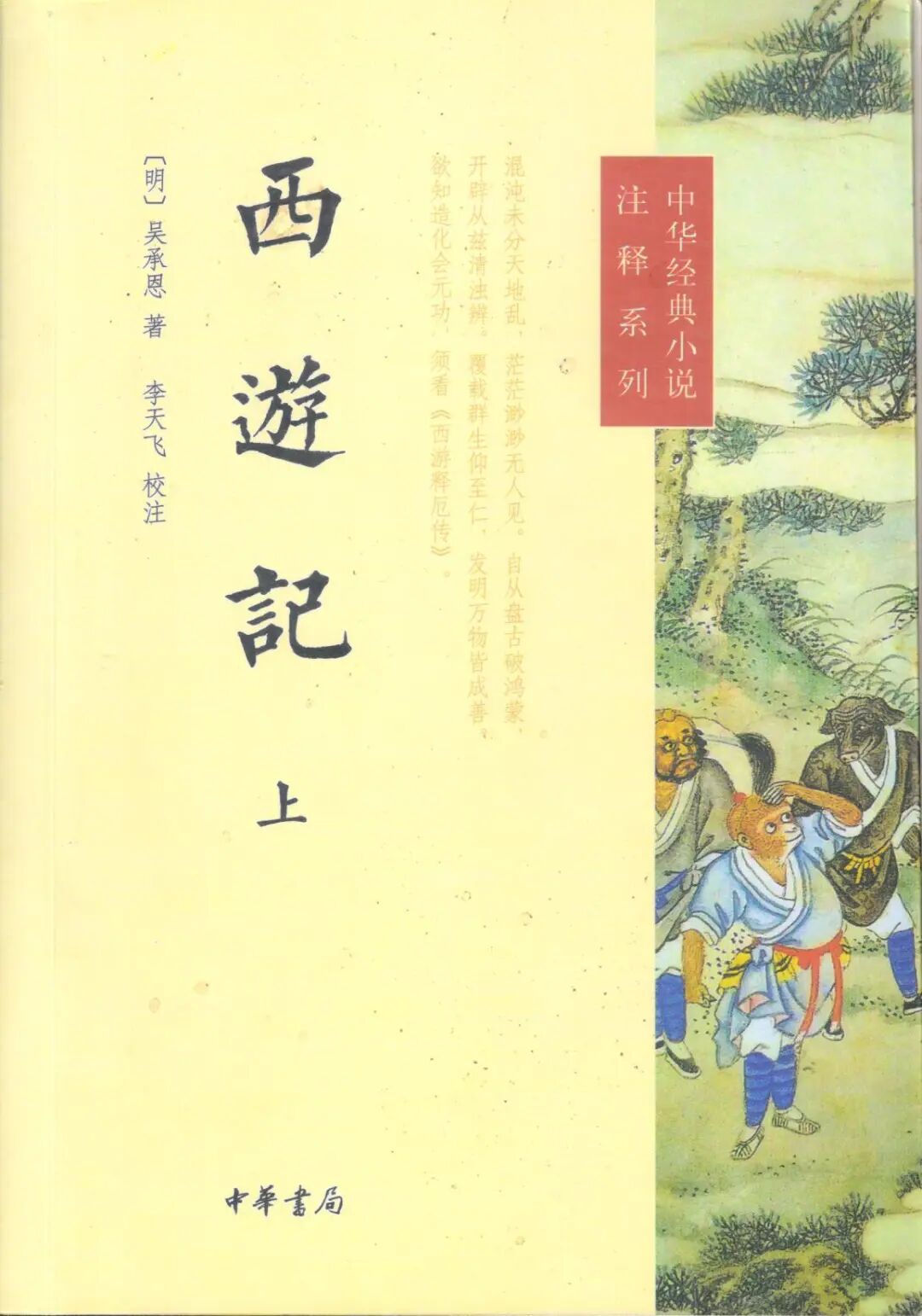
李天飞校注本《西游记》
本书在校注过程中对前辈、时贤观点、成果多有借鉴,李天飞校注本启发尤多,在此一并致谢!限于识见,错舛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