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障人士排队来领分红,举着房本争先恐后地签约,生怕晚了就享受不到房屋抵押的优惠,背景音乐播放着“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听障人士吴大姐不仅自己抵押了唯一的房子,还介绍很多亲友参与理财,公司暴雷的消息传来,她在愧疚和绝望之下点燃煤气自杀身亡……
这个在短视频平台引发关注的片段来自电影《震耳欲聋》,于今年国庆节上映,凭借对听障群体被诈骗的的写实刻画,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影片讲的不是什么虚构的故事,而是我们身边可能正在发生的、针对听障等弱势群体精心策划的骗局。
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相关信息显示,由于沟通障碍和社会支持不足,听障、心智障碍等弱势群体在金融理财领域很容易成为被诈骗的对象。
电影之外,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当我们的邻居、朋友因为先天障碍而活在信息的孤岛里,我们构建的社会支持体系,能否成为他们信赖的桥梁?
作家张雁,同时也是心智障碍孩子的母亲,在看完电影后,给我们发来了她的思考。
文 | 张雁
作家 自闭症孩子母亲
编辑 | Zoey_hmm
图 | 电影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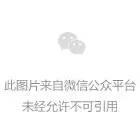
他们听不见 他们被骗了
在城市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对面,有一片低矮破旧的居民楼。这里生活着一群聋哑人,人们管这一片叫哑巴楼。
他们是城市中的底层,所谓的“低端人口”,收入微薄,生活拮据。更因天生的听障,被无形隔绝在主流社会之外。
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他们常常无所适从,只能相信“和自己一样的人”。
于是,当理财公司老板老金出现时,他们几乎毫不犹豫成群结队地抵押了自家的房子,购买一种承诺高额回报的理财产品。
只因为老金“和他们一样”,也出自这个大院——他父母都是聋哑人,他在这里长大。
即使后来当了老板,他仍经常回来,和大家聊天、晨练,发红利时满面红光,诚恳可亲。
你很难指责他们贪婪。比如,那位孤身一人的小卖部老板,不顾劝阻执意卖铺子买理财。他说:我想给自己找个好点的养老院,我不想一个人孤独死去。
这难道不是一个人最正常的人生愿望吗?
法庭上,金老板的律师否认听障人士的特殊性。他说:听障不影响智力,听障人士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们签的合同合法有效。
他的话在法律上不无道理。但他刻意忽略了一个事实:听障人士因沟通障碍,在知识获取、技能学习和日常沟通中困难重重,很多人严重依赖手语,依赖懂手语的人做翻译才能与普通人正常交流。
而诈骗分子就是利用这一点,表面提供帮助,实际上则误导和断绝他们和外界的正常联系。
电影中有这样的一幕,一位受骗的聋哑大姐到派送出所报警,却因为语言障碍无法沟通。
这时,尾随而至的犯罪分子黄毛假装成热心邻居,主动担任手语翻译,当着警察的面向大姐施压,转而对警察谎称,大姐报警是因为“狗丢了”。
与听障人群相比,心智障碍者面临的困难就更为显著。他们能听能看,却常常难以理解日常语言、表达困难。遇到困难或需要帮助时,甚至说不清自己是谁、家在哪里。
就在前几年,还发生过身在救助站的自闭症青年意外死亡的案例。
当你深入了解残障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世界,你会发现,个人很难抵御有预谋的欺诈和剥夺。那么,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CODA:在照顾与逃离之间找寻自我
这部影片引入了一个对多数人而言陌生的词CODA(Child of Deaf Adults)——聋人父母的健听子女,片中,年轻律师李淇和诈骗公司老板老金都是CODA。
中国有多少CODA?尚无确切数据。但根据全国约3000万听障人士来推算,这一群体可能有几十到上百万。
他们天生健听,能听会说,却成长于一个寂静的家庭环境中。童年语言环境的缺失可能导致他们的语言和社交能力落后,但也正因如此,他们在与父母的交流中熟练掌握了手语。
他们中很多人曾为父母充当手语翻译,甚至成为父母和外界沟通的依靠。有人这样形容他们“一直在照顾别人,从来没当过孩子”。
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突破了环境限制,成为人群中的佼佼者,他们会如何看待自己的出身?是逃离过去迎接新生,还是会像照顾父母那样,去守护更广大的群体?
年轻律师李淇曾拼命努力,想跻身精英律师行列,彻底摆脱残障家庭的阴影。
直到一次偶然,他接下了一桩法律援助案件。帮一对听障兄妹打官司。他赢了,并因此一举成名。
既然无法抹去CODA身份,不妨把它转化为独特的优势,他选择成为一名精通手语、专供听障相关领域法律纠纷的专业律师,成为聋人与法律之间的桥梁。
李淇的矛盾和转变,让我联想到我的孩子。我的长子乐渔是成年的心智障碍者,他的弟弟则是刚刚考上大学的普通孩子。我希望小儿子前程似锦,不被哥哥和家事拖累。
但也明白,未来他多少会承担起照料父母和哥哥的责任。这既是法律义务,也是人伦常情。每个人生来便对他人负有责任,这正是人类社会得以维系和传承的根基。
相信人还是相信制度?
多年以来,我在工作和生活中认识不少成年心智障碍人士,健鹏就是其中一个。
我问他“你觉得看了这个电影有什么经验教训值得记取的?”
健鹏回答得很干脆:“遇到不决之事,保持冷静,想办法求助自己信任的人。”
“还有呢?”我接着问。
“不要贪小便宜。”他说。
我相信健鹏不会陷入金融骗局。原因有几条:
首先他能支配的钱很少,有钱也都交给了父母。
其次他的荣誉感强,喜欢朗诵、做手工、参加集体活动,对赚大钱没有兴趣。
更重要的是,他参加残联和其他公益组织的各种公益活动,和残障人士家属或其他爱心人士学习唱歌、画画、运动,学做手工,他的生活很充实。
在这些活动当中,他遇到的都是来帮助他的“好人”。他喜欢自己工作的职康站和温馨家园,也喜欢那里的老师和管理员。
当然,他有时也会因过分依恋某个人而碰壁,这也是他学习和磨练的机会。
好的制度,就是让好人保护弱者,就像律师的法律援助制度,让没钱没人脉的听障人士,能得到像李淇这样精通手语的律师的帮助,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值得一提的是,CODA本身也是一个公益组织的名字。由CODA人士创立,旨在帮助健听子女在听障和健听两个世界之间找到平衡。
心智障碍者由于自身的缺陷,更需要来自组织和制度的支持。家庭和亲人已经承担了太多、太久,不堪重负。
在我接触的许多心智障碍家庭中,那些得到社会组织,特别是家长组织支持的家庭,大人和孩子的生活质量都改善了很多。
有的孩子从情绪失控到成为社区家庭的老师助理,有的孩子通过同伴和社会接触改善了问题行为,有的孩子从胆小退缩变得合群,家长们从悲观绝望到重新振作……
我越来越坚信:制度的改善终将造就一个对残障者更加友善的社会,而这也会惠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李淇曾因出身遭受歧视,认为帮助听障人“吃力不讨好”,也曾因急功近利,认为“眼前利益最重要”,放弃原则收取了不义之财。
但他最终还是回归本心,选择帮助那些从小看着他长大的邻居、为他收集卡片的杂货铺老板,哪怕为此赔上来之不易的事业。
这个转变,除了良知唤醒,也来自司法局和其他律师的支持。
同时,被帮助的听障姑娘张小蕊坚强不屈,不为钱财打动,不向黑恶势力低头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鞭策。
弱者不仅有权利,也有责任。想要得到别人的帮助,自己也要付出努力,比如诚实守信,比如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发声。
我们的孩子会长大,也会变老。作为心智障碍者,他们需要一张牢固的安全网来托底。这张网,首先要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好的制度也需要好人去执行,去推动。
所以,我们既要相信制度,也要依靠值得信任的人——而那个被保护的人,也应当包括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