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士虎
微信版第1808期
笔者近年来从事皖江池州先贤古籍整理与注译工作,参与整理了《郑三俊全集》《桂超万全集》《敬事草》,注译了周馥《负暄闲语》《玉山诗集》等,对《贵池二妙集》中吴应箕、刘城等人作品亦有关注,发表了考证论文。在译注整理这些古贤作品的过程中,翻阅了相关资料,如宛陵名贤沈寿民的《姑山遗集》,看到了让我神往的宣城与池州两地先贤交往的图景:他们往来频繁,相亲相知,志同道合, 彼此激励,情谊深挚,生死不渝。兹以宣城先贤沈寿民为例,漫谈明末宣、池两地先贤密切的人文交往,以及这种交往所产生的影响。
一、沈寿民拜师郑三俊,师生情深
沈寿民(1607—1675),字眉生,号耕岩,宁国府宣城人。明末诸生,加入复社,崇祯九年(1636)举贤良方正,荐征赴阙,疏劾大司马杨嗣昌夺情误国及总督熊文灿主抚之罪,由是名动天下。未几,引疾归。筑别业于姑山之麓,耕读其中,学者称耕岩先生。博通经史,以朱子理学为宗。69 岁卒,学生私谥贞文先生。沈寿民与芜湖沈士柱合称“江上二沈”, 与吴应箕、刘伯宗、沈士柱、杨维斗合称为“复社五秀才”,明亡后与吴县徐枋、嘉兴巢鸣盛并称“海内三遗民”。著有《姑山遗集》三十卷、《闲道录》十六卷等。

沈寿民像
郑三俊(1574—1656),字用章,号玄岳、巢云老人,筑一室曰“影庵”,池州府建德(今安徽东至)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 授元氏知县,累任南京礼部郎中,归德知府, 福建提学副使。天启初,被召为光禄少卿,改太常。崇祯初,官拜南京户部尚书,后升任北京刑部尚书、吏部尚书。著有《巢云》《影庵》二集。《崇祯元氏县志》赞其“举朝推重,天下第一清品”,《明史》本传赞其“为人端严清亮,正色立朝”。
崇祯二年 (1629),郑三俊任南京户部尚书,23 岁的沈寿民于十二月游学至金陵,为次年在金陵参加乡试做准备。期间沈氏作《上南户部尚书郑公书》,书信中称郑公“殷然以抡群才、奖后进为己任”“蒞官以来,拒却私谒,非德不交”,请求入其门下:“寿民, 宛之鄙人也,遑遑乎四海无所归,何至亦蒙一字之拔,矧推引之意,早举于未识面之前。而请托之人,又概乎无平生之素,吾何修而获此苏、朱数君子之遇也哉……即此犹可以当门下乎?不然,自顾盖无足以辱知己也。岁行尽矣,寒素无所将,敢为是言以献,聊志铭德云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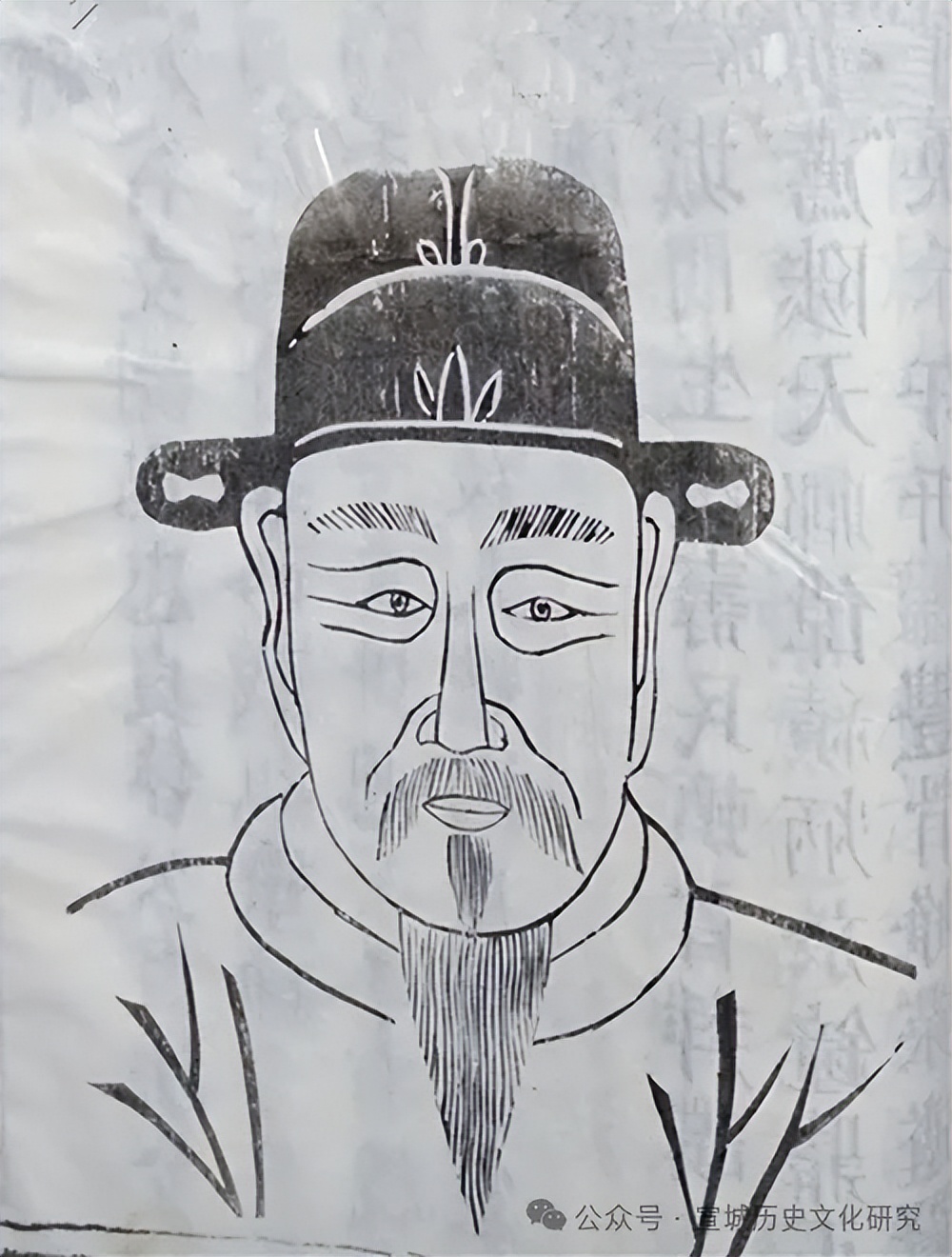
郑三俊遗像
此后,二人往来密切,成为相知相亲的一对师生。从“蒙一字之拔”“推引”“请托之人,又概乎无平生之素”等词句看来,沈氏并不熟悉、从未交往的某个人,向郑公推荐了年轻的沈氏,郑公礼贤下士,遂有一字之拔的善意回应,这让沈氏非常感动。据笔者推测, 其内情可能是郑公批单子,给沈氏提供了(按其资历也能享受得到的)入南京国子监学习与暂住机会。
沈氏作品中,保留了多篇与郑公有关的诗文,如《奉郑玄岳先生书(丙子 1636)》《奉郑玄岳先生书(戊寅 1638)》《救郑公疏(戊寅1638)》《奉建德郑太宰书(崇祯癸未十二月, 1643)》《奉郑玄岳师》《奉郑影庵师》《祭影庵郑师文》《与郑稚默(三俊长子)》《口号别郑日如(三俊三子)》《与郑继之(三俊侄)》《与孔仲石(三俊侄)》《东山篇奉玄岳师(壬午)》《午日郑玄岳师席上得舒城报二首》《中秋影庵师座上漫占二首》《寄李卓生(三俊女婿)》《与李卓生》《郑太宰公像赞》等 [1]。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三俊在任刑部
尚书时,执法平允,不阿帝意,崇祯帝怒责其欺罔,褫其官下狱。沈寿民为救恩师,作《救郑公疏》,因为已有廷臣具疏申救,“郑公就诏狱三日,余持是章且上,会黄东崖、徐虞求诸公,各具疏申救甚力,或曰‘盍俟诸?如必不得请也而继之,讵无济?’又三日,上御门特释,异数也。是草可以焚矣。”(《姑山遗集》卷一《救郑公疏》文末附注)郑三俊无辜获罪一事,对沈寿民影响颇深,是沈氏决定隐居不仕的一个原因。郑公清正刚直的品格,为弟子树立了榜样。
三俊出狱,返回故乡,沈氏作《奉建德郑太宰书(崇祯癸未十二月,1643)》,提醒老师要避嫌远祸,“温公既归,绝口论事;蜀公虽退,不敢居名,老师应善处此。”又要求老师承担责任,设法保一乡平安。郑公性情孤冷, 阅历丰富,绝处逢生,居乡自会谨言慎行。沈氏岂不明此理?但他还是忠言聒耳,只不过是为了表示对老师的一片关爱之心罢了。
明亡后,沈氏在《奉郑影庵师》信中称“门生寿民奉训门墙最久,其为衔戢亦最深”,他劝老师编撰国史,以嘉惠后学,保存信史,敦促老师把自撰年谱(自卸任归德知府后续起) 编写完,并求录副本相赠,认为“为教更大。此固《昭代言行录》所亟引为冠冕者也”。信末,追记了师生分别时的情景,老师执手殷勤, 欷歔眷顾,沈氏掩泪不忍去。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这对师生之间情谊深挚,还有沈氏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力求保存优秀文化薪火的淑世情怀。
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十日,郑三俊薨于南原之里第。沈寿民闻讯,从黄山奔赴南原吊唁,与三俊遗孤相向痛哭,“尔也失父我失师”(《口号别郑日如》),表现出对恩师去世的深切哀痛之情。沈氏在奔丧吊唁如礼,返回宣城后,“以讣同邑秦华彦、汤缵禹、吴錂、吴坰、徐日康、弟沈寿国, 诸咸北面先生者,于居于游,各为位哭。越明年夏迄期,乃相率裂帛纪哀,衔诚走奠”, 而寿民稽首作《祭影庵郑师文》,赞美老师“公忠勋炳两曜,名德德重元龟。贻嗣贤以清白,擢众正于布韦。凡百有口,人歌人碑。” 哀悼老师十多年来的不幸遭遇:“艰贞震厉, 无宁终日,不啻齿嚼冰雪,而手捍熊羆。”
沈寿民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也不断表现出对先师的思念悲悼之情,诸如“束身姑山之椒, 驰神玉峰之下,泪濡腹痛,不可以步”(《与孔仲石》),他赞美老师的忠诚勋节,“本朝唯王三原、马钧州、刘华容三公(即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堪望肩背,余悉非敌。” 他感激老师的器重,“教爱不稍衰,兹德可忘, 犹忘穹昊尔!临丧号恸,决裂肝胸。”(《与郑穉默》)“南园痛哭以来,神思惨惨,全无欢绪”(《与李卓生》)等语甚多。沈氏还经常回忆到自己在老师府中学习的场景,“谒南园而别,弹指告期,心如游云,往来左右, 诚不可道里格、刻晷停也。私惟老师德厚气完,八十年犹日初旭。”(《与郑继之》)在《郑太宰公像赞》中,概括了郑公的勋绩、品性与风范:“范、韩也勋名,文、谢也忠贞,鲁公书法兮临池,靖节诗篇兮暮吟。戴纵垂绅兮千秋典型,硕望清修兮奕世荣恩,手有槐而心有地兮翼我后人,耀国史而辉家乘兮从祀庙廷。”
郑公对弟子沈氏颇为信任器重。江桓《太宰郑公传》[2] 载,郑公“殆甲申(1644)三月之变闻,哭临几绝,遂被缁入山,屏世务,不使关白,晚益简亢,绝交游,惟门人宣城沈寿民、贵池刘城、同邑江杏时或过从,相持悲愤而已,坐卧小庵,日手录性理、史鉴诸书,寒暑不辍。”以二人交往之密切,可推知郑公肯定有不少与弟子酬唱往来的诗文、书信,可惜郑公在世时,诗文稿没有刊行,清代顺治至康、乾时期,文字狱频发,其书稿更没有刊行机会, 迨至清末,郑公故居遭兵燹,文稿被焚。笔者近年来参与裒集整理焚余的郑公诗文,没发现他与弟子交往的片言只字,这是历史留给读者的遗憾。
二、沈寿民与吴应箕气谊相投
吴应箕(1593—1645),字次尾,号楼山,贵池人,与刘城并称“贵池二妙”。明亡后, 举兵抗清,顺治二年(1645)十月,兵败被俘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明末称复社五秀才,应箕为首。其克全晚节,尤不愧完人。” 从吴氏《楼山堂集》诗文看,他与宁国府(今宣城市)友人沈寿民、沈寿国兄弟、梅朗中、万应隆(泾县)、梅之晔、梅斐伯(斐伯是其子) 父子、刘振、昝质等人都有交往,而与沈寿民交往最多。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万应隆、吴应箕、沈士柱、沈寿民、梅朗中组织文社——南社 [3]。时吴应箕 27 岁,沈寿民才 14 岁,此次应是二人初次相见。
天启四年(1624) 春,吴氏游宣城,初夏返池州。沈寿民于此年加入应社,可能与吴氏此行有关。先是,吴氏与吴郡徐和鸣合七郡十三子为匡社,刊发十三子之文。后来推金沙周镳主盟,周氏将文社大大扩展,上江徽、宁、池、太、淮阳、庐、凤与越之宁、绍、金、衢诸名士,咸以文邮至,遂改社名为“应社” [4]。
天启七年(1627)夏,沈寿民应试南陵, 吴应箕偕同池州、安庆府友人刘城、蒋臣、吴钟、王公俨拜会。沈寿民《谒吴楼山坟哭之, 追数往事,拟杜七歌(甲午八月,1654)》[5] ( 其一 ):“回首丁卯月维夏,出门有交君颉颃。” 附注云:“丁卯试南陵,楼山偕存宗、一个、空之、公俨诸子交予兄弟。”
崇祯二年,南社、应社加入了张溥、张采组织的复社,沈寿民与吴应箕同为南社、应社领袖人物而入社。二人与刘城、沈士柱、杨廷枢合称“复社五秀才”,又与顾杲、徐汧、陈贞慧、侯方域、方文并称“复社七魁首”。崇祯三年暮,吴氏至宣城,作诗《宣城留别沈眉生、治先兄弟》,诗云“积雨动高林, 留人意自深。二难谁可并?八咏到于今。燕市存轲渐,关中识布心。踏歌何处断,欲别未成音。”表达了依依难舍之情。(《楼山堂集》卷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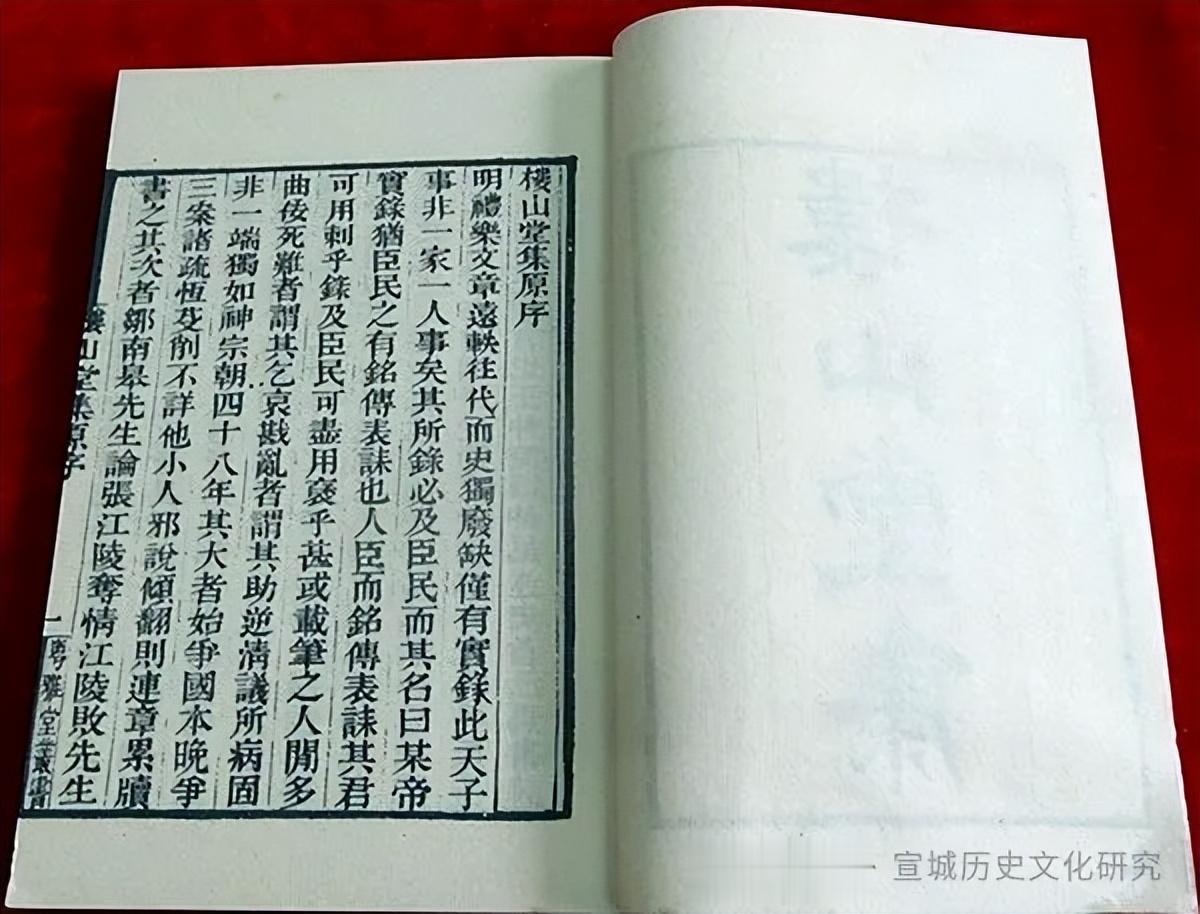
《楼山堂集》卷首书影
崇祯六年(1633)春,吴应箕于杭州西湖孤山读书社沈寿民寓所,“读陈百史(陈名夏)所为《程墨选》,心奇之,即语眉生:‘此当有名于世。’已而百史举于乡,名果噪于天下。”(参见《楼山堂集》卷十六《陈百史古文序》)此季,复社在苏州虎丘召开大会, 吴应箕、沈寿民、沈士柱为上江社友召集人, 人称“三茂才”。
吴、沈二人的交往,始于以文会友,终于名节砥砺和精神契合。正如吴应箕所说:“宜之友有沈眉生者,与予交二十年如一日,始交也以文而不徒以文。”(《楼山堂遗文》卷五《梅斐伯文序》)吴应箕传世不多的诗文作品中, 仍保留了不算少的与沈氏来往的书信与诗文, 这是二人相知相契的写照,篇目除《宣城留别沈眉生、治先兄弟》外,还有《与沈眉生论诗文书》《答沈眉生书》《乌龙潭山亭同沈眉生》《寄周仲驭兼致眉生》《虎丘同仲驭、眉生》《得眉生、孟璿、朗三书却寄,时眉生以抗疏归, 不复就试》《定生以眉生疏草相示》等,另有《折槛行》诗序中言及沈氏与一干友人(周镳、陈贞慧、顾杲、梅朗中、麻三衡),请吴在京口饯送被逮赴京的南京御史成勇。成勇进士出身,为官刚正清廉,崇祯十一年任南京御史时, 因上书参杨嗣昌夺情入阁,被革职下狱。
而沈氏亦有赠吴先生的诗,卓尔堪《遗民诗》中收有沈氏的《赠吴次尾》[6],诗云: “巍峨望陪京,恻恻涕泪新。握手风萧条, 边马声酸辛。据鞍三山头,感慨大江津。寓目览旧迹,萧条愁杀人。荒郊千里别,归为山谷民。夏日苦难夕,冬夜苦难晨。水流长泯泯,花落空纷纷。远怀积秋浦,相思在河漘。雁飞不可接,郁结何由陈?”诗歌意绪低沉, 少了飞扬锐气,当是明社倾覆,南都阮大铖一伙对复社成员下毒手,吴氏被迫逃离南京时,沈氏所写的赠别诗。
吴氏《楼山堂集》刻有参订姓名录,其中就有沈氏。时人亦时常看到二人一起参与社交活动的身影,如方以智诗《次尾、眉生、武子饮圣敏舟中》[7],就记录了这个场景。
沈、吴二人志趣相投,均以授徒为业,热心文社活动,又积极介入时政,主持清议。黄 宗羲《南雷文定》卷七《陈定生先生墓志铭》云: “时周仲驭、沈眉生读书勾曲,先生(陈贞慧) 与吴次尾读书亳村,皆好佐王之学,独持清议, 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镆铘出匣。”
二人刚直敢言,易召人忌。崇祯八年春, 郑公主持京察考核时,揭阳令张明弼被降级, 张氏认为是郑公听信了沈氏和吴应箕的“诬告”,特作《肚单记》[8] 一文,为自己喊冤, 抱怨郑公并嘲讽沈、吴二人。而据沈氏诗文以及其他相关史料可知,张氏被削级,一点都不冤。《姑山遗集·谒吴楼山坟哭之,追数往事, 拟杜七歌之四》即是对此事的追述:“有虫沙中类短狐,谁是螫者沈与吴。昔年化虎揭阳市, 市人十无一完肤。填肠喷秽骄莫比,厥神罚之声通衢。是时癸未天网疏,翻身影射狂哮呼。前指大楼后麻姑,两人销骨何人殊?呜呼四歌兮歌四诉,生日相怜死异路!(金坛张明弼令揭阳,贪污,为计典所黜,无端侵予与吴。大楼、麻姑俱山名,一吴居,一予居也。)”
沈寿民、吴应箕与张县令三人身份、地位不同,活动空间不交集,个人之间很难产生利害冲突。从诗句来看,沈、吴确实指责过复社社友、进士出身的张县令,其目的当是为了维护复社团体的声誉,不存在个人恩怨。郑公为官清正,主持考评官员,自然会细心核察属官的奉职情况。沈诗末尾附注中的“无端”二字, 说明了向郑公进言的并不是沈、吴二人。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四《周镳传》:“太宰郑三俊主察,其贤否多出于镳。故事,先察之日, 太宰发单于科道,科道书其贤否,上之太宰。镳之母党张明弼居官无善状,镳不为隐。三俊察之,明弼当堂诘三俊,据单不应下考。三俊曰:‘吾知子之不善,何必单也?’”据此可知,揭发张令贪腐的另有其人,——即张令外甥周镳,他是沈、吴二人好友。
沈、吴之间, 精神契合。崇祯十一年(1638),吴应箕在无锡顾杲家中,看到沈寿民《劾杨武陵疏》指控阉党阮大铖的一段话,很受触动,遂起草驱阮檄文《留都防乱公揭》, 复社文士 143 人签名支持,签名人中有宁国府文士沈寿民、梅朗中、麻三衡、颜绍庭、赵初浣等人。
黄宗羲《陈定生先生墓志铭》载《公揭》起草缘起云:“会眉生保举入京,劾杨武陵(嗣昌),并及大铖妄画条陈,鼓煽丰芑。大铖始阻(沮)丧,先生与次尾因草《留都防乱揭》。”
沈氏《劾杨武陵疏》文末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鄙劣充朝,奸邪营进。霍维华赍恨以殁,而冯铨招蓄亡命,尚横据于襟喉。吕纯如失望堪怜,而阮大铖妄画条陈,犹鼓煽于丰芑。岂筹兵必需此辈?实逆类巧为借端。” 其谋虑之深远,被不久以后南明覆灭的历史所完全证实。
南明亡后,吴氏起兵抗清,兵败被俘杀, 吴氏卒后,沈寿民与文江子(南京人)拜谒吴应箕墓,作《同文江子别楼山墓归》,诗云: “痛哭高田路,千山响共闻。朱旗残壁在,白马故人回。心许何年剑?魂招到处台。君看坟草劲,秋老不曾摧。楼山家高田。”时隔九年, 沈寿民再谒楼山墓,作《谒楼山坟哭之,追数往事,拟杜七歌(甲午八月)》。可见沈氏对友人的情谊,并未因生死异路而改变。此组诗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比如在沈疏劾杨武陵处境孤危时,吴附书武选司郎中孙嘉绩,致慰问、鼓励与馈赠。《二歌》有诗句云“楼山楼山慰我书,涨天气势睨若无。解衣传饩万里道, 岂无他人谁子如”。《三歌》尾注,提到吴氏于崇祯十二年率江上应试诸子呈督学金公(金兰,字楚畹,绍兴人)促沈氏赴闱参加乡试等事迹,这都是二人交谊的体现。
三、沈寿民兄弟与刘城父子交往密切
刘城(1598—1650),明末清初安徽贵池人,字伯宗,明季诸生。入清屡荐不起,隐居以终。有《春秋左传地名录》《峄桐集》《古今事异同》《南宋文范》等。
刘廷銮(1614—1666),字在公,一字得舆, 号舆父。刘城之子,承家学,又师事吴应箕,诗文皆有名于时。康熙元年以贡考授州同知, 未仕,卒。曾撰《建文逊国之际月表》,另有《梅根集》《贵池掌故》《杜诗话》《李杜行纪》等,与父亲刘城均为复社成员。廷銮弟廷鏊(1618—?),字幼济,亦为诸生,为沈寿民门生。
刘城的宣城友人除了寿民兄弟外,还有梅朗中、麻三衡、麻乾龄父子、赵初浣、陈龙媒、蔡蓁春等人。
沈氏与刘城父子结识,时间很早。《姑山遗集》卷九《刘在公稿序》:“天启七年, 予以学使者之檄,趣试南陵。吾友刘伯宗由池阳来,携在公以至。”
沈、刘二人惇挚至性,留心世务,勤奋博学,笃于友谊,所以共同语言比较多,交往也比较亲切。
刘城有诗《赠沈眉生寿民》(《峄桐诗集》卷二》),编年不详,应是二人初交时的题赠。诗云:“眉生冲默人,渊镜一以静。四座韵飊驰,畏此神清整。当其冥理游,傍若无为影。后顾惠连随,前旌伯也秉。大雅禀先民,体约风遒冷。美稗翦既多,绝艳亦从省。三叹有遗音, 微文于兹炳。”诗中以“冲默”来形容友人,应该是寿民初始参与文会时的表现,面对一众年长得多的文友,作为后起之秀,其谦冲缄默的举止,是得体的。诗歌赞美沈氏在文学上的成就,则是刘城对盟弟的勉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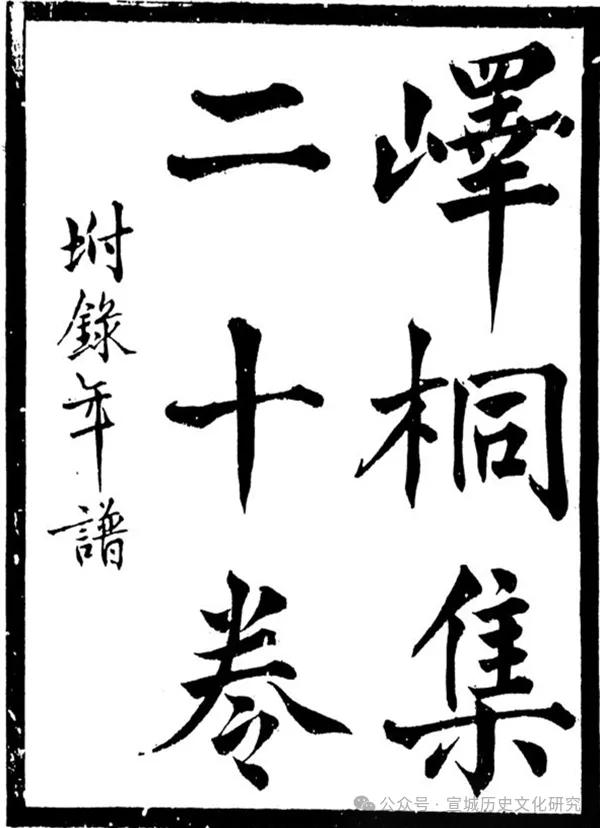
《峄桐集》书影
崇祯三年正月,沈氏应刘城请托,为刘廷銮文集作文《刘在公稿序》(《姑山遗集》卷九),开篇言及天启七年自己因获交于刘氏父子, “忻然不能无所怀也”。而后指责时下父兄师傅指导无方:“惧之以劳,引之以逸,辅之趣时,闭之稽古”,使聪颖子弟变成寻常无闻之人。再揭示有学与为学的意义,引用大文豪杨慎的名言,向廷銮指出,只有通过后天的不断努力, 才能日新其业,热情鼓励廷銮更进一步:“犹总角,已能晓畅于圣人贤人之书,肆力于文, 援经驱史,无艰难劳苦之态,此虽得之天者生而有异,要其习与智长,固时有以取乎人也。夫以子瞻之雄才,而以明允为之父,故才易成; 以郑玄之多识,而以马融为之师,故识益洽。今在公神爽隐厚,方冲然笃志如不及,更以伯宗(父刘城)迪之于前,子先(老师詹振) 掖之于后,宜沛乎其有获焉,谁能御乎?近代杨公用修(杨慎)警敏该博,为本朝冠,乃以语人亦以‘性不足恃,日新其业当由心力’, 则予为嘉在公之能壹意于学而又加进焉,抑孰得而量哉?在公勉矣!”
崇祯九年,吏部议举贤良方正,巡抚张国维于是年推荐沈氏应诏,崇祯十一年二月, 沈赴京,连上三疏劾杨嗣昌夺情误国,并及总督熊文灿迁延不能制敌之罪。疏上,却被留中, 不予回应。沈见机而作,返归宣城,授徒姑山。
池太道史可法、江西右布政使张秉文亦于崇祯九年举荐刘氏孝廉,刘遂于崇祯十一年秋应召赴京。次年应吏部试,注官湖广郴州,以知州用,城辞归。其间缘故,与沈氏提前发来警报有关。沈氏在《答刘伯宗》书信中,诉说自己在京遭受的种种不愉快经历,“携疏至其(指通政司张绍先)门也,凡七往,始上达。”“乃污蔑任口,斥辱百端,封事未彻于御前,已私献武陵(指杨嗣昌)之第”“科目之人卑视征辟”“且政府(指内阁宰相)眈眈侧目保举,非朝伊昔”,告诫刘城不要像自己那样“昂首论列,批鳞折槛始见平生。”“毋以麟凤之姿, 轻投豺虎之口。”要求盟兄要厚待自我,举动不可轻率,要储才以备国用:“我辈虽伏处草野,要当体上天生才、国家需才之意,储为有用,共障倾危,不当遂意径情,浪于一掷,盟兄安得不厚自爱惜耶?”(《姑山遗集》卷二) 听闻这些披肝沥胆之言,刘城自然心领神会。刘收到此信后,作诗《采石得梅生书因怀仲驭》(《峄桐诗集》卷六)回应,诗作赞美沈氏忧劳国事,疏劾执政的义举,表达了一同归隐山居的心愿:“相持咸塞默,兢看一书生。不识批鳞逆,犹将敝舌争。圣朝优戆直,名士嗜孤清。待女周郎久,山居得耦耕。”
《姑山遗集》卷二十二有《书刘舆父卷后(戊戌七月,顺治十五 1658)》,赞美刘城与舆父父子手稿、手帖宝贵价值,“征君(指刘城)平生文章出入汉两京,前后高蔚栗密, 树成纲纪。舆父之习于兹,胚胎也而食息之矣。今序记具在,创端搜类,绳尺斩斩,厥光肆发, 万目睢 ……舆父尚善閟此卷,毋为他日好事者攫以去也。”《卷二十四》有复刘廷銮书信二篇,信中所谈话题都很具体,体现出作者对刘氏父子的深沉的感情,透露出对故国的缅怀和对坚守传统君臣道义的信念。
刘城与寿民弟寿国亦有往来,他为寿国诗艺作序《沈治先诗艺序》(《峄桐文集》卷三),赞扬沈氏兄弟治《诗》不苟,义类名物,能分析得细致入微。言其称诗作文, 必曰温柔敦厚,是不悖于诗之教。他还作诗
《怀麻孟璿、沈治先》(《峄桐诗集》卷十) 怀念宣城麻三衡和沈寿国,诗云:“江南佳丽满,有尔玉为人。落月深相照,离思又及春。何限风流意,翩然并逸群。别来游处共, 总卧敬亭云。”
沈氏与刘氏父子交往,还涉及到生活琐事,比如,刘廷銮请亦师亦友的沈氏为一把扇子题字,沈氏谦虚,称自己字写得不好看, 遂耽搁了三年,终于题写好了,并寄回。并作 诗《扇归舆父》(《姑山遗集·卷二十九》)致意:“是物珍吾笥,三年怯未书。笔因王粲阁,风想谢安余。秋浦愁猿夜,宣州好月初。思君不可见,题罢付江鱼。”在《与刘舆父》(《姑山遗集》卷二十四)中,亦言及题扇事, 此外,还涉及其他琐细的事,如专候兰水师容(即郑公遗像),称赞廷銮作《月表》(即《建文逊国之际月表》),是不朽的事,道歉没能追和后者写的《八代诗》等。
四、宣池两地先贤风义相期、笃友尚节
宣、池两地名贤声气相通,笃友谊、尚气节,切磋学问,砥砺名节,他们淑世忧世, 至性至情,立身行己的事迹互相映衬,成为替乡土增色、名标青史的人物。《孔子家语·六本》云:“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 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地视其草木。”诚为知言。
沈寿民途穷见节,急朋友之难。凌雪《南天痕·逸士传》载:寿民在明亡后,遁隐金华山中,采藜藿充食。有知而饷之者,谢不受, 曰“士不穷,无以见志;不奇穷,无以见操守。”“(沈)性虽孤峭,然其少时慷慨重然诺、笃友谊,自言才疏意广。甲申以前贷金至六百,皆急朋友之急也。”明亡后,在破巢失路、贫病交加情况下,还在搜集亡友周镳遗集, 裒成三十卷,授刻,工费浩繁,数浮百金之外, 难以独立承担,其时“质约迫于左,信义迫于右”,他还是坚持下来了。(《姑山遗集》卷三《答陈仲献书》)沈氏此番义举,古今罕逢。
刘城脱赀赠友、拯救遗孤。陆延龄修,桂迓衡纂《(光绪)贵池县志》卷二九《人物志·隐逸》:“(刘)善诗古文辞,与吴应箕齐名, 而折节温恭,人比之春风好玉。尝脫赀赠黄詹事道周、成御史勇、陈刺史弘绪于诏狱,欲出死力论救之。”“金陵既下,栖隐峡川,冠服不改,应箕死,冒险葬之,抚其孤。爪掌画几, 俯仰咄嗟不常,至没时握《金陵临安图志》不释手,犹冀东晋、南宋之事可得复见云。”
吴应箕竭力救友。宝应县人汤廷琏(号荐玄)负气敢任,吴夸其“文武全才”“天资忠孝”,汤生与县令发生冲突,被县令罗织罪名, 已陷大辟。为救友人,吴氏四处发信恳求有权势的友人张自烈、袁继咸、周钟、周镳、杨廷枢、冒襄、张玮等人斡旋搭救 [9]。
他们都尚气性、重名节。沈、刘应荐举遽返故乡,沈疏劾执政大臣,吴草逐阉党余孽檄文,均是崇尚气节的表现。
他们都忠君爱国。当代学者评价“吴应箕政治上与复社其他领袖一致,是对东林的绍绪,学术上强调经世致用、古为今用。既是一代文人领袖,更是在野的政治家。没有享受到大明王朝的皇恩,却以生命诠释了忠义气节, 名垂青史。”(丁国祥《张溥评传》246 页, 江苏凤凰出版社 2019 年版)
郑、刘、沈三人在明亡后,隐居山野, 坚守遗民身份,刘、沈二人均拒绝官府征荐, 表现出可贵的气节。沈在寄书信给刘廷銮时, 透漏心声,“弊弟今日自砺自进,虽起诸死友 复生,生者无愧。”(卷二十四《复刘舆父》) “然清夜扪腹,原事事起见君父,堪质苍旻。”(卷五《答同邑友人书》)其弟子亦称其“三十年伏首匿形,青毡皂帽,对影无惭。”(《姑山遗集附录·祭文(吴肃公作)》)其思想言行, 均表现出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坚守。
刘城在《峄桐文集》卷八《印记》一文中,袒露改字“存宗”的心态,“城四世单传, 子姓弱,愧不死于崇祯、弘光,姑以存其宗于一日。然终恐郁郁不能久待,故更之曰‘存宗’”。他还让人刻印表明心志,印文曰“大明遗民”“谢发郑心”。忧实伤人,刘氏不忘故国,“(城)愤恨不自聊,徬徨山泽。未几, 竟死。”(《南天痕》卷二十《刘城传》)
郑三俊居家似僧,不与世事。《乾隆池州府志·卷四十·郑三俊传》载:“(崇祯) 十七年五月,烈皇帝凶问至,三俊号恸几绝, 遂披缁入山,自号巢云老人,筑一室名影庵, 日抄录性理、史鉴诸书,足迹不越户,二三亲旧访之,宛然老僧也。”
他们互为师友,思想交流频繁。吴、沈、刘三位平辈友人中,吴氏年最长,他个性外向,在与沈氏交往过程中,自动充当了兄长角色, 诗文酬答之作,都不忘箴规劝勉,《寄仲驭兼致眉生》诗,赞扬二人耿直敢言,蹈死不顾, 激励二人继续坚守忠义,每饭不忘君:
“……谔谔谁能争,后先有同禅。忠信豈必悟?精能天地变。所愿报圣明,何辞遭诛遣?茆岭云亭亭,敬亭清且衍。一饭敢忘君? 匪以资善卷。”
吴氏在《楼山堂遗文》卷四《与沈眉生论诗文书》中,向友人宣说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观。他指出当世作文的弊病,就是不合体(作序者似作论赞,作策者不能有条理、有根据,作传记不切事情,作章奏言不剀切, 拟制诰词不简正),认为今之文不如古之文, 根源在于“真与不真,而有体与无体异也。” 吴氏还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实践:“弟亦尝肆力经史而出入于八家矣,又不欲袭取一语。核其体制以归于清洁,庶几自成一家。”“助流政化者诗也,苟无关系,虽不作亦可。而近日竟陵之派流毒最深,以能用之乎者也诸字为灵, 以有深幽静远苦寒孤危诸语为厚,以杜撰率尔之作为有性情,于是空疏不学之士攘臂登坛, 而诗道亡矣……平生喜曹子建、陶元亮、杜工部三人之诗,为本忠君爱国之心,而有感发兴起之意,且亦各不相袭,自成气体。三百篇之后,惟此可歌可咏耳。弟虽好,未尝用其一语。亦未尝如今之拟古者动作无情之词。”这封书信,体现出来的文学创作思想,是非常高明的, 它针砭了虚伪无情、空疏蹈袭、不能辨体、无助政教的恶劣文风。其观点,对盟弟沈氏文艺观的发展定型,无疑会起到导引作用。
沈氏文学观,强调取法乎上,反对有词无情,重视辨体(文体规范),重视风格、重视文章的社会作用。他曾说过:“先秦两汉之业, 了不可问,即时誉希踪八家,往往唐宋调杂, 今古体混,宏纤夺位,俗雅竞态,尚论者无其源,应手者迷所择,何能据堂室端模楷也?”(《姑山遗集》卷二十三《与季沧苇》)“不有其时与事,强而取古铙歌诸曲拟之效之,词虽工,非情也。……此江菉罗之言也。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所得,曰某篇是某体,某句似某人,词虽工,非情也。…… 此徐文长之言也。杜甫因事立题,《青坂》《无家》等篇,略不更袭陈迹,前哲高之。”“诗诚有为而为。”(《姑山遗集》卷七《夹上芝序》)“宏而弗纤,华而弗炫,善事实而弗忘家国天下之大。”(《卷八·沤斋诗选引》)
从上述言辞中,不难看出沈、吴二人在文学观上的呼应关系。这些宣、池名贤,身份、地位、年龄、学术方面的成就虽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勇担道义、坚守儒者本心、孜孜以进德修业为务, 骨子里带耿直不阿气质的人,他们砥砺名节, 同声相应,笃于友谊,相互成就,促进了宣池两地文学的繁荣,演绎了一段友谊佳话。4 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完全达到了沈氏在《卷二十一·交对(己卯四月)》所阐发的“君子之交”的水准——“君子之与人也,未交,无弗慎;既交,无弗恭。无临难而罔顾,无见义而苟容。无有言而寡践,无善初而隙终。无疑嫌以起,无谗佞以从。无事亲不揆以义,无事君不绳以忠。无生无死,无穷无通。”给后世人们树立了宝贵的榜样。
注释:
[1]所列举的沈氏十七篇诗文,除《郑太宰公像赞》外,均收入沈氏《姑山遗集》。《郑太宰公像赞》收录于民国郑氏裔孙编《巢云老人焚余集》。
[2]江桓《太宰郑公传》收录于张赞巽等监修、周学铭总修《(宣统)建德县志》卷十九《艺文传》。
[3]“南社”由万应隆发起组建,参见李德淦等主修、洪亮吉主纂《嘉庆泾县志》卷十八《文苑·万应隆传》。
[4]参见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清代抄本四卷本。
[5]此组诗收录于《姑山遗集》卷二十八。
[6]此诗收录于卓尔堪《遗民诗》卷十,清康熙年版。
[7]方以智《方子流寓草》卷之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50 册影印明崇祯刻本。
[8]《肚单记》收录于张明弼《萤芝全集》卷四, 明别集丛刊第五辑第 42 册,据光绪戊戌金沙于氏刻本影印。
[9]吴应箕为救友人汤廷琏,四处拜托的书信收录在《楼山堂集遗文》中。
参考文献:
[1]江菲菲 . 沈寿民研究 [D]. 合肥 : 安徽大学 ,2015.
[2]沈寿民 . 姑山遗集 [M]. 明别集丛刊第五辑084 影印康熙有本堂本 . 合肥 : 黄山书社 ,2016.
[3]吴应箕 , 刘城 . 贵池二妙集 [M]. 光绪贵池刘世珩唐石簃刻本 .
[4]吴应箕 . 楼山堂集二十七卷 遗文六卷 遗诗一卷 [M].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1388、1389.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5]郑素明纂 , 丁士虎核 . 郑三俊文集 [M]. 南京 : 南京出版社 ,2023.
[6]黄宗羲 . 南雷文定 [M]. 辽阳靳治荆校订 , 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
(作者系池州学院副教授)
自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