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曾经有一把名为“言官”的利刃。
它本应寒光凛冽,涤荡污浊,是帝国自我纠偏的卫士。
然而,到了晚清,这把利刃却悄然淬上了党争之毒与虚妄之火,刃口翻转,最终刺入了那具早已步履蹒跚的王朝病躯。
当耿直的谏诤沦为精巧的诬陷,当国家的利益让位于私门的恩怨,一场以“风闻奏事”为名的狂欢,加速了大清这艘巨轮倾覆的进程。

甲午战争前后,这种畸形的言官文化达到了顶峰。
此时国家正值生死存亡之秋,亟需上下同心,共御强敌。
然而许多言官的笔锋,却更多地指向了主持洋务、应对危局的重臣李鸿章及其派系。在“爱国”的旗帜下,是不可与外人道的争权夺利。
张骞与翁同龢的密信中,就有“丁(汝昌)须即拔……似可免淮人复据海军”(大意是必须立即搞掉丁汝昌,这样安徽人就不能再掌控海军了)这样的“谋略”。
王伯恭曾经与翁同龢辩论,认为翁主战是错误的。
翁同龢辩不过,最后说了实话:我正要借这个机会检验北洋海陆军,好以此作为整顿他们的理由。
他们的参劾,不在意事实是否准确,只在乎内容是否惊世骇俗、出人意料,是否能在朝议中产生轰动效应。
私底下,这些流流文人们还会互相“切磋”,谁谁的那篇弹劾最为离奇惊人,令人叫绝。
在衣着光鲜、雍容揖让的下面,充斥着污浊与不堪。
一则关于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的弹劾,堪称荒诞离奇的典范。
有言官奏称,李经方不仅暗中向日本输送米煤,更“认倭王之女为义女,并定为儿妇”,李鸿章的孙子俨然成了“日本驸马”。
如此匪夷所思的情节,翁同龢看过之后,竟然大呼“语绝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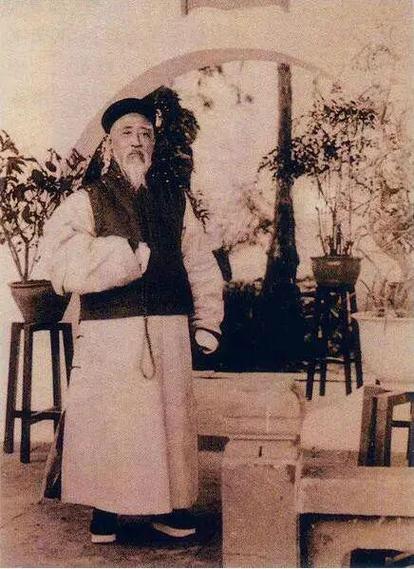
当言官由于编造的故事过于离奇而被朝廷降罪或罢官,反而会十分骄傲,认为自己敢谏、强项,清流士子也会将他们视作榜样,传为“佳话”。
这股风气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灾难性的。
它使得前线统帅李鸿章等人不仅要应对强大的外敌,还要分心应付背后射来的无数冷箭。
动辄得咎,举步维艰。
当北洋水师在黄海苦战时,言官们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实干官僚进行“道德绞杀”。
李鸿章“言官制度,最足坏事”的愤慨之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出的沉痛控诉。
言官们的“忠诚”表演,几乎耗尽了帝国最后一点的向心力和行政效率。
甲午的硝烟还没有散尽,随之而来的庚子事变,使得言官们再次兴奋起来。
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前后,不少言官和詹、翰林官员,不仅不能以理性的态度匡扶国是,反而成为盲目排外、鼓吹怪力乱神的急先锋。
他们声称“拳民神术可恃,能避枪炮”,将民间迷信拔高为救国战略。
更有甚者,比如翰林院编修王龙文、曾廉等人,主张借助义和团之力,围攻外国使馆,他们的奏疏内容,充斥着天方夜谭式的自信和外交知识的无知。

他们为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的疯狂决策,提供了看似“民意沸腾”的假象和“理论支撑”,最终将国家拖入了几乎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监督机制异化为互相倾轧的工具,任何试图挽救危局的努力,都会在内部无尽的攻讦与掣肘中化为泡影。
他们以笔为剑,自以为是在捍卫道统。
殊不知剑锋所指,已是支撑帝国存续的最后基石。
那些自命不凡的“忠诚”,最后成了为帝国送葬的哀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