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安》作者;尔曼·黑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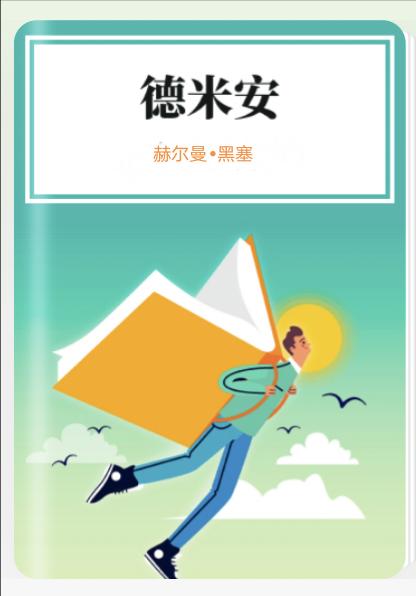
今天我们要讲的书,是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的一部代表作,书名叫作《德米安》。
赫尔曼·黑塞,是德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出生于1877年,天赋惊人,七岁便开始写诗。1904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一举成名,从此成为专业作家,代表作品有《在轮下》《德米安》《悉达多》《荒原狼》等等。1946年,黑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2年,他在瑞士家中去世,享年85岁。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德米安》,是黑塞创作于1919年的一部小说,讲述了少年辛克莱的成长过程。他经历了复杂世界的诱惑,在彷徨、孤独、叛逆和内心的矛盾中,一次次陷入对自我和外界的怀疑,直到遇见同龄人德米安,在他的影响下,从困顿彷徨,开始不断成长,最终走向新生。
黑塞的写作风格受到当时的心理学以及尼采哲学的影响,以深邃的哲思和精美的文字,影响着无数青年走向自我觉醒的追寻。心理学大师荣格说:“读黑塞的书,像在暴风雨的深夜,感受到灯塔的闪耀。”这本《德米安》更是畅销百年,是村上春树、塔可夫斯基等诸多名人挚爱的文学经典。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本书,走进少年辛克莱的内心世界。
第一次成长:遇见德米安
辛克莱10岁那年,他觉得自己生活在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一个世界是他的家,父亲母亲、姐妹们生活的地方。平日里,这个熟悉的世界弥漫着温柔的光辉,良好的家风,充满着爱、榜样和教育。一切井然有序,美丽和谐,有着笔直的人生道路通向未来。
而另一个世界,是家里的女仆和手艺学徒们构成的世界。在这里,辛克莱听到幽灵故事和丑闻流言,了解到屠宰场和监狱、醉汉和恶妇的生活,甚至有关于盗窃、谋杀的骇人传闻。
家境优渥的辛克莱当然属于第一个光明正统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总有几分无趣和乏味,有时,他也会悄悄向往第二个神秘且幽暗的世界,那个世界充满禁忌,却又引人入胜。
辛克莱就读于小城的拉丁语学校,一个午后,他和几个男孩在外闲逛,突然来了个年纪稍微大几岁的男孩,他叫弗朗茨,是裁缝的儿子,他父亲酗酒,全家在街坊邻居中口碑都不好。
弗朗茨才13岁,已经模仿着成人的模样做事,讲话也是大人腔调。他要这几个小点的男孩子,跟他去桥边,在狭窄的堤岸上翻垃圾,为他找一些有用的东西。在他严厉的发号施令下,大家都乖乖服从。
之后,孩子们坐在地上闲聊,纷纷吹嘘自己在学校里的英雄行径或者卑劣的恶作剧,辛克莱为了逞强,也编了一个故事,他说埃克磨坊附近有一座花园,自己和一个同学曾经趁着天黑,偷了那里的一整袋苹果。而且不是普通的苹果,是上等的好苹果。讲完后,辛克莱沉醉在自己臆想的故事里,浑身发热,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赞赏。弗朗茨眯着眼睛看向辛克莱,威胁着问:“是真的吗?”
辛克莱脸红心跳,但嘴上还是执拗地说是真的。
散伙后,弗朗茨一直尾随着辛克莱到家,胁迫辛克莱给自己两马克,否则就要去警察局告发他偷窃。辛克莱吓坏了,他还是个小孩,没有钱,他试图把自己的旧银表,还有其他东西,故事书、罗盘都拿给弗朗茨,但弗朗茨冷酷地拒绝了,他只要钱,如果明天放学拿不到,就要辛克莱好看。
弗朗茨幽灵般的身影从门口消失后,辛克莱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一片黑暗。他甚至迈不动步子,只能痛苦地缩在楼梯台阶上。那天起,他再也无法感受到家里的安宁与明媚,只觉得自己深陷罪孽和险境,被人恐吓、受尽惊吓,既耻辱又焦虑。
他对父母隐瞒了这件事,悄悄从母亲房间拿走了自己的存钱罐,把里面所有的钱都取出来,也只有可怜的65芬尼,连1马克都凑不齐。
第二天,辛克莱瑟缩着把这些钱都交给了弗朗茨,弗朗茨并不满足,继续勒索他尽快交上剩下的钱,只要他吹一声口哨,就是辛克莱“上供”的时刻。
那天之后,无论辛克莱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总能听见弗朗茨那可怕的口哨声,勒索已经持续了几周,辛克莱度日如年,他弄不到钱,只能偶尔从家中女仆放在厨房的菜篮子中偷拿几个芬尼,每次都被弗朗茨鄙夷地责骂。
弗朗茨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辛克莱深感绝望,失魂落魄,在日复一日的煎熬中病倒了。
这段时间,学校里来了个插班生叫德米安,他是一个有钱寡妇的儿子,比辛克莱大一级。德米安很独特,他从不合群,自信果断、举止成熟、像位绅士。很快引起了辛克莱的注意。
有一天,辛克莱和德米安一起在大教室上《圣经》课,老师讲了“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放学后,德米安主动和辛克莱打招呼,两人一起走了一程。
辛克莱家的拱门上,有一枚徽章,是一只古老的鸟。德米安告诉辛克莱,那只鸟应该是只雀鹰。辛克莱很吃惊,他没想到,德米安比自己更了解自己家的房子。
两人边走边聊,提到课上讲的“该隐”的故事。该隐是《圣经》中的人物,是亚当与夏娃的长子,因为自己的献祭没有得到上帝的悦纳,该隐嫉妒献祭成功的弟弟亚伯,并将其杀害。上帝对该隐施以流放之刑,额头赐予一个记号。该隐的故事体现出对罪恶与忏悔的警示,成为探讨人性善恶的经典例子。
然而,德米安对这个《圣经》故事有着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该隐的故事可以另作解释。他认为,该隐不仅不是坏人,还是个卓越的人。他和他的后裔的额头,之所以有个记号,有别于大多数人,正是他们的殊荣,代表着这小部分人的勇气和个性。在外界看来,这样的人因为特立独行而令人害怕,所以,人们为这种人杜撰了流言,也许是为了报复他们,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
辛克莱对德米安的思想深感震惊,之前,他从未用这样批判的观点去看待事物、思考问题。而德米安的讲述轻盈悦耳、引人入胜,眼神中充满智慧,这一切深深触动了辛克莱。从那之后,该隐的故事和他额头的记号,总是提醒着辛克莱,要用不同的角度去探寻知识,走向批判。
经过无数次在家中顺手牵羊,偷走一点硬币后,辛克莱总算还清了欠弗朗茨的“债”。但勒索并没有就此结束,弗朗茨仍在控制着辛克莱,他无数次追问辛克莱从哪里搞来的钱,还扬言要把一切都告诉辛克莱的父亲,辛克莱被吓得魂飞魄散。
这天,辛克莱被迫又和弗朗茨见面,德米安看到了他们。
弗朗茨离开后,德米安告诉辛克莱,不要吓唬自己,有些人有些事,完全没有必要害怕。辛克莱无助地望着德米安,他发现,这个睿智的男孩子似乎洞察了自己所有的秘密。
德米安安慰辛克莱,说会有解决办法的。弗朗茨不是他该交往的人。对付这种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
那天之后,弗朗茨魔鬼般的口哨声,再没出现在辛克莱家的附近。这个人似乎彻底消失了。被胁迫已久的辛克莱,起初一直不敢相信自己重新获得了自由,直到有一天,他在巷口迎面碰见了弗朗茨,弗朗茨一看见辛克莱,就大惊失色,飞快地转身溜走了。
这是辛克莱从未有过的胜利,敌人在自己面前逃走,撒旦害怕自己,惊讶和喜悦的潮水一阵阵洗刷着他的身心。
几天后,辛克莱又见到德米安,德米安问,弗朗茨是不是没再打扰他?辛克莱急切地问德米安,他是怎么做到的,是跟弗朗茨做了什么交易,还是打了他?
德米安摇摇头,说自己不喜欢做这样的事,他只是跟弗朗茨谈了谈,让他清楚,不招惹辛克莱对他更好。
德米安走后,辛克莱怔在原地,他又一次感受到德米安的强大。如果没有德米安的解救,也许自己会在忧思中度过患病和堕落的一生。这一刻,他百感交集,心中满是对德米安的钦佩和感恩,以及对自己的羞愧和惶恐。
第二次成长:和皮斯托琉斯谈话
几年后,辛克莱离开家乡,去外地上寄宿高中。一开始,他跟同学到酒馆里寻欢作乐,感受禁忌和叛逆的气息,与世界为敌。一次次宿醉后,他又深感空虚自责。
最终,他决定找回自己,清除内心的黑暗,重建光明世界。他开始静下心来,举止沉稳、步履坚实,在清晨,冷水沐浴,在夜晚,读书绘画。他画出自己的梦中人:一张半男半女的神秘人脸。后来还画了一副破壳而出的雀鹰,寄给了德米安,他已经好几年没有德米安的音信了。
这天课间休息时,辛克莱发现一张夹在书间的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几行字:
“鸟奋争出壳。蛋就是世界。谁若要诞生,就必须毁掉世界。鸟飞向神。神叫阿布拉克萨斯。”
辛克莱倒吸一口冷气,毫无疑问,这是德米安的回信。因为除了他,没人知道鸟的故事。看来德米安收到了他的画。可是,神叫“阿布拉克萨斯”,是什么意思呢?
辛克莱沿着“阿布拉克萨斯”这个线索,开始搜索一切与之相关的知识,听老师讲,阿布拉克萨斯源自希腊咒语,可以将它理解为神的名字,是一种结合了神灵与魔鬼的神衹象征。
一天,在城里散步时,辛克莱偶然听见一所小教堂里传出管风琴声,他坐下凝神倾听,觉得演奏者有着顽强的意志和独特的个性,演奏得相当精彩。
音乐停止后,管风琴师从教堂出来,是个走路飞快的年轻人。辛克莱跟着他进了一家小酒馆,看清了他的样貌,与他谈论音乐,两人就此相识。
这位教堂演奏者名叫皮斯托琉斯,两人谈到新神“阿布拉克萨斯”,皮斯托琉斯很感兴趣,他将辛克莱带回自家的老宅,参观家中藏书,并教辛克莱做哲学训练,凝神注视着壁炉里的柴火,在沉默中思考。
辛克莱和皮斯托琉斯常常交谈,互相诉说彼此的梦境。皮斯托琉斯擅长解梦,他总能在辛克莱的幻境和思想中发现价值,认真严肃地与他讨论,他教辛克莱在面对自我时,保持勇气和尊严。
当辛克莱感到悲伤时,皮斯托琉斯为他演奏管风琴,在非凡、热诚、令人陷入冥想的音乐中,辛克莱觉得内心变得无比充盈,准备顺服灵魂的呼声。
管风琴的声音消散后,两人常常会在教堂坐上片刻,看着微光从高窗照射进来,再渐渐黯淡下去。
皮斯托琉斯告诉辛克莱:人们所见之物,正是他们自身的内在之物。大部分人活得并不真实,是因为他们把外部世界当成了真实存在,却无视自身的内部世界。人,一旦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就不会选择走一条庸常之路。庸常之路易走,自我之路难行。但寻找自我的人,愿意走这条艰难之路。皮斯托琉斯的话给辛克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动。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了解的加深,辛克莱开始抗拒自己的朋友、也是领路人皮斯托琉斯。因为他意识到,皮斯托琉斯引导自己去寻找自我,正是因为他本人无法真正做他自己。
皮斯托琉斯对“新神”抱着希冀,梦想成为神父,宣讲新信仰,创造新象征。但这不是他的职责,也非他力所能及。皮斯托琉斯过分执着地沉迷远古,但他也明白,新信仰源自新土壤,而非受造于古籍。
在如今的辛克莱看来,应该破除偶像崇拜,因为一个觉醒的人,除了找寻自己的道路外,没有其他的义务。辛克莱相信,人只能渴求自己,渴求命运本身。在这条路上,皮斯托琉斯作为领路人,陪他走了一程,但他们终究要分开。
第三次成长:从寻找领路人到成为领路人
辛克莱的高中时代结束了,上大学前的那个假期,他去德米安和他母亲过去的居所拜访,从房子主人的口中得知,这母子俩早已搬离,不知道他们现在身在何处。
房主带辛克莱在屋子里转了转,并找出一本皮面相册,指给辛克莱看德米安母亲的样子。
瞥见那张小照时,辛克莱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他震惊地发现,德米安的母亲,竟然就是自己多年以来的梦中人,也是自己画作上那位半男半女的神秘人!她和德米安有几分相似,容貌美丽迷人,又带着男子英气。
几周后,辛克莱到大学报道,这里的一切都令他失望,哲学史课是空洞的说教,年轻学子们平庸无奇。大部分时间,他都躲在近郊舒适的老宅里,阅读尼采。
一天傍晚,辛克莱在城中漫步,偶遇德米安,令他十分惊喜,两人边走边聊,德米安说,自己和母亲就住在河边的一座花园里,邀请辛克莱来做客。
次日一早,辛克莱便前往德米安家中拜访,女佣打开门,领他进去,一入客厅,辛克莱便看到自己寄给德米安的那副雀鹰图,被镶进黑色画框,高挂在门上方的木墙上。
画下的门开了,一位美丽高贵的妇人站在那里,她是德米安的母亲,也是辛克莱从未见过,却出现在他梦里的神秘人。辛克莱向她默默伸出手去,和她温暖坚定的双手紧紧相握。这一刻,他觉得自己仿佛奔波了一生,终于回家了。
德米安的母亲指着墙上的雀鹰,说辛克莱的画给德米安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快乐。早在辛克莱10岁那年,德米安从学校回来,便告诉母亲,有个额头上有记号的孩子,会成为他的朋友,他说的就是辛克莱。后来,收到这幅画时,他们就知道,辛克莱正在走向他们的路上。
从此,辛克莱经常出入德米安家中,这里让他感到幸福和满足。房子之外,是真实的世界:街道、楼宇、教室和图书馆;房子之内,是爱、灵魂、额头有记号的人正在觉醒,他们专注于特殊的观念,走在特殊的道路上。他们交换思想,彼此信任和理解。
一天,狂风大作,暴雨挟着冰雹滚滚而落,辛克莱满身潮湿凌乱地前来,德米安把他带到自己的房间,告诉辛克莱,他梦见广袤的大地上,城市和村庄正在燃烧,命运的脚步隆隆作响,他有种强烈的预感,旧世界即将坍塌,新世界就要到来。
不久后,德国和俄国关系紧张,处处躁动不安。战争就要来了,德米安和辛克莱即将奔赴战场。现在,世界的洪流不是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而是直接穿过他们的胸膛。
临行前,辛克莱与德米安和他母亲共进晚餐。德米安的母亲告诉辛克莱,以后,如果再需要某位带着记号的人,就学着呼唤他,他一定能感知得到。
在战场上,辛克莱看到,许多活着的人、死去的人,都在庄严地靠近命运的意志。他们用坚毅深远的目光,带着几分狂热,一次次发起进攻。无论他们信仰什么,为何而战,都在准备交付自己,去塑造未来。然而,世界越是执迷于战争、英勇、荣誉和一切古老的理想,人道之声就愈发遥远,愈发难以置信。
血腥的战争是人类内在分裂灵魂的爆发。人们去仇恨、去杀戮、去赴死、去毁灭,只是为了新生。当巨鸟奋争出壳,蛋就是世界,而这个世界,终将化为乌有。
辛克莱在农庄前放哨时,被炮弹炸伤,他被抬上车,一路颠簸行驶在旷野里。尽管大部分时间,辛克莱都在昏迷中,可他强烈地感觉到有种东西在主宰自己,引领自己前行。
深夜,车子到达目的地,辛克莱被放在大厅的地板上,他感觉自己已经抵达了被召唤的所在。他环顾四周,看见自己旁边的床垫上,躺着一个人,那人额头上有个记号,他是德米安。
墙上的灯照在德米安脸上,两人长久地对视着。
德米安靠近辛克莱,轻轻地说,你还记得弗朗茨吗?
辛克莱对他眨眨眼,露出微笑。
德米安说:“听着,我得走了,也许你还需要我帮你对付弗朗茨,或者别的什么。假如你呼唤我,可能我不会再这么急匆匆地来找你。你必须倾听自己心底的声音。然后你会发现,我就在你心里。”
“还有,”德米安顿了顿,又说:“母亲说过,如果你身处险境,让我替她吻你。现在,闭上眼睛,辛克莱。”
辛克莱顺从地闭上双眼,他感到自己被轻轻一吻,之后,他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有人来给辛克莱包扎伤口,他清醒后,赶紧望向身旁的床垫,那上面躺着的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陌生人。
伤口很痛,但从那之后,辛克莱终于找到了钥匙,成为自己的领路人。
好,到这里,德国文学大师赫尔曼·黑塞的这本《德米安》的精华部分,我们就讲的差不多了。
这部小说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末尾对战争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欧洲文明的反思:“欧洲竭力造出了人类的新武器,但最终却处于精神沉重与极度的荒芜之中。因为它虽然赢得了整个世界,却失去了灵魂。”
在现代文明之下,个人的自我被无情地碾压,小说主人公辛克莱内心的矛盾与彷徨,正是一代人的写照。通向内在自我之路如此艰难,却又必须为之,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独立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