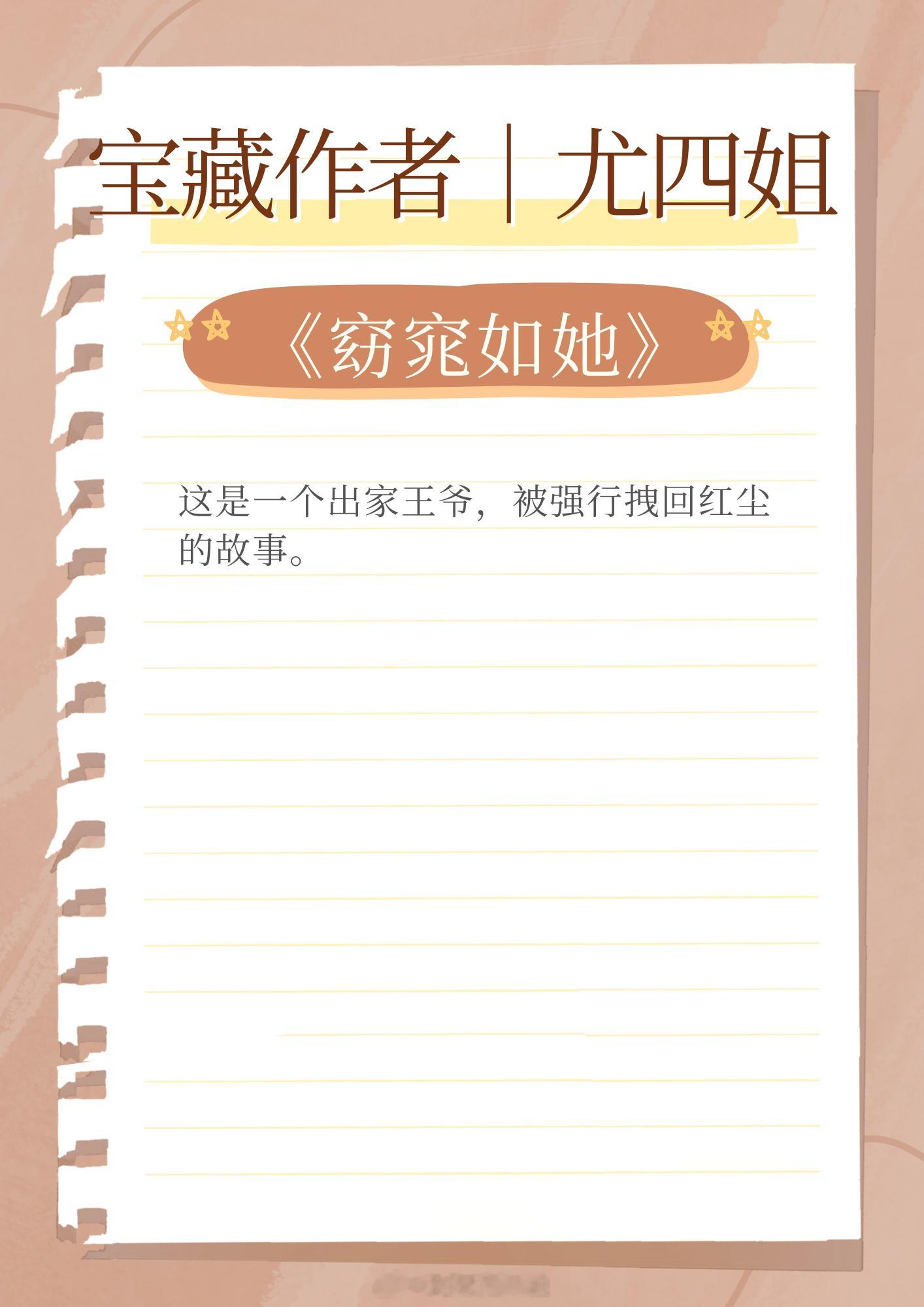成亲当天,我的夫君为了救他落水的青梅。
丢下满堂宾客与我,纵身跃入了后院的湖水。
我一个人顶着沉重的凤冠与盖头,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站了整整3个时辰。
直到我父亲赶来,他没有责问任何人.
只是轻轻掀开我的盖头,说:“丫头,跟爹回家。”
当夜,那蜿蜒十里的红妆,沿着来时的路,被原封不动地抬回了太傅府。
01
成亲那一日,我的夫君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后院的湖水里。
他要救的,是那位总穿着素白衣裳、说话轻声细气的表妹。
宾客们起初是惊愕,渐渐地,那些投在我身上的目光就变了味道,像是看一出编排好的热闹戏。
我一个人穿着沉重的嫁衣,顶着绣满金线凤凰的红盖头,在那布置得一片鲜红的喜堂里,足足站了三个时辰。
身旁那对高高的龙凤红烛,一点点燃尽,烛泪堆积在托盘里,凝成了古怪又凄凉的形状。
直到我父亲来了。
这位当朝太傅没有理会任何人,径直走到我面前,抬手掀开了那张几乎压断我脖颈的盖头。
他只说了一句话。
“茉儿,跟爹爹回家。”
那一夜,从城北到城南,那蜿蜒了整整十里的红妆队伍,沿着来时的路,又被原封不动地抬了回去。
而我的夫君,萧将军,据说是在后半夜才披着一身未干的水汽回到他的新房。
面对那间空荡得如同坟墓一般的屋子,他呆立了许久,一动不动。
第二日清晨,贴身丫鬟芸香急匆匆地跑进我的闺房,脸上带着复杂的神色。
“小姐,萧将军……他跪在咱们府门外头,已经跪了一整夜了。”
我正对镜梳理着一头长发,闻言,手中的玉梳微微顿了一下。
“是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那就让他跪着吧。”
镜中的女子面色苍白,眼底有着淡淡的青影,可那双眼睛里的神色,却和昨日之前完全不同了。
昨日的期待、羞涩,乃至对未来的一丝惶惑,全都消失了。
只剩下深不见底的平静,和一点冰冷的了然。
我太了解萧淮了。
他此刻的跪求,与其说是对我沈云茉的悔恨,不如说是对他自己所作所为必须付出的代价感到不甘,以及对将军府即将面临的压力的恐惧。
果然,父亲那边没有任何回应。
他照常上朝,回府后便在书房处理公务,仿佛门外那个身份尊贵却狼狈不堪的将军,只是一尊无关紧要的石像。
午后,宫里的內侍来了,带来了皇帝的口谕,宣父亲与仍跪在府外的萧淮一同进宫。
父亲整理好朝服,临出门前,才淡淡地对管家吩咐了一句。
“去告诉那位萧将军。”
管家躬身聆听。
父亲的声音像淬了冰的刀子,清晰地划过庭院。
“想娶我的女儿?”
他顿了顿,每一个字都砸得沉重。
“等下辈子吧。”
马车载着父亲驶向宫城,我独自站在庭院里的梧桐树下,看着叶子缝隙里漏下的细碎阳光。
我知道,从父亲说出那句话开始,我和萧淮之间,就真的彻底结束了。
不是赌气,不是试探,是真正意义上的,完了。
那些曾经在心中描绘过的、关于未来的模糊图景,此刻像被水浸过的墨画,氤氲成一团,然后彻底干涸,不留痕迹。
傍晚时分,父亲从宫里回来了。
他的脸色比平日更肃穆几分,但眼神中并无挫败,反而有种尘埃落定的沉稳。
他将御书房里发生的事,简略地告诉了我。
皇帝确实有意调停,但父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父亲没有纠缠儿女私情,他只问了皇帝一个问题。
“陛下,一个能在结发之礼上背弃誓约的男人,臣实在不知,该如何相信他能坚守对江山社稷的忠诚。”
这句话太重了,重到连皇帝都无法轻易接住。
萧淮在御前所有的辩解和恳求,在这句话面前,都显得苍白可笑。
最终,皇帝只是疲惫地挥了挥手,让萧淮退下,并言明此事他不再过问。
父亲说完,看向我,目光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
“茉儿,爹爹今日在御前把话说绝了,你可会怪我?”
我轻轻摇了摇头,为他斟上一杯热茶。
“爹爹做得对。”我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这条路既然走不通,那就不走了。女儿以后,只想好好侍奉爹爹。”
父亲的眼底似乎闪过一点水光,但他很快掩饰了过去,只是点了点头,接过茶盏。
02
日子仿佛又回到了出嫁前的模样,平静,规律,带着太傅府特有的书香与肃穆。
我每日陪父亲用过早膳,便随他进入书房,有时帮他整理文书,有时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看书。
父亲处理政务时不再避着我,偶尔会指着某份奏章,考教我几句。
他的问题不再局限于闺阁女子该懂的诗词女红,而是涉及朝局、民生甚至边关军务。
我明白,父亲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教导我。
坊间的流言却并未因为两府的沉寂而消失,反而像春日雨后的野草,悄悄滋生蔓延。
芸香有时会带着愤愤不平的表情,告诉我外面又传了什么难听的话。
无非是说我心胸狭窄,容不下一个孤苦无依的表妹,甚至在大婚当日言语刺激,才导致柳姑娘“失足”落水。
将军府那位萧夫人,更是将那位柳姑娘接进了主院,以“义女”之名精心照料,呵护备至。
这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
“小姐,她们简直是把黑的说成白的!”芸香气得脸颊发红,“咱们就不能做点什么吗?”
我放下手中的书卷,走到窗边,看着庭院角落里一株快要开花的晚香玉。
“急什么。”我淡淡道,“让她们说去。话说得越满,日后摔下来,才会越疼。”
我的目光落在书案一角,那里放着我那份厚厚的嫁妆单子。
指尖滑过冰凉坚硬的纸页,最终停在某一行小字上。
那是一套“四时清赏”白瓷茶具,前朝御窑的绝品,一共十六件,件件薄如蝉翼,绘着四季花卉与景致,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最珍爱的遗物之一。
我记得,萧淮曾随口提过,柳云薇酷爱白瓷,认为那是世间最洁净无瑕之物。
一个念头,如同投入静湖的石子,在我心中泛开清晰的涟漪。
“芸香,”我转过身,“去库房,把那套‘四时清赏’取出来。”
芸香愣住了:“小姐,那可是夫人留下的……”
“我知道。”我打断她,语气平静无波,“拿出来,我要卖了它。”
“卖?!”芸香的声音都变了调。
“对,不仅要卖,还要大张旗鼓地卖。”我走回书案后,铺开一张淡青洒金的笺纸,“我要办一场‘雅集会’,邀请京中有名望的夫人小姐们前来。”
芸香是个机灵的丫头,眼珠一转,渐渐明白了我的意图。
“小姐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咱们府上为了争一口气,如今竟到了要变卖夫人遗物的地步?”
“这只是其一。”我提笔,开始书写请柬,“世人总是容易同情看似弱势的一方。当他们看到一个被抛弃的女子,不得不靠着变卖亡母遗物来维持体面时,你觉得,他们还会相信将军府那些漏洞百出的说辞吗?”
但我的目的,远不止博取同情那么简单。
我要用这套茶具,织一张网。
一张看看柳云薇究竟是真纯洁无瑕,还是贪婪做作的网。
也要看看,那位刚刚在御前受挫的萧将军,为了博红颜一笑,还能做出怎样荒唐的选择。
雅集会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迅速飞遍了京城的贵人圈子。
请柬只发给有限的几十家,措辞清雅含蓄,反倒更勾起了人们的好奇。
流言的风向果然开始微妙地转变。
“沈太傅家那位小姐,竟要卖她娘的遗物了?”
“怕是退婚时为了争口气,把聘礼全数退回,伤了自家的元气吧。”
“唉,也是个可怜人,遭了那样的罪,如今还要受这种窘迫……”
这些议论,或多或少地传进了我的耳朵。
我只是平静地听着,然后在拍品名录的首位,郑重写下了“四时清赏”的名字。
底价,定在了八千两白银。
一个足以让绝大多数人望而却步的数字。
我要的,就是少数人的角逐,或者说,是某个特定人物的入局。
不出所料,将军府很快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据说,那位柳姑娘在听闻“四时清赏”四个字时,失手打翻了药碗。
而她看向萧淮的眼神,充满了欲言又止的哀戚和向往。
03
雅集会那日,天气晴好。
我将地点设在了府中临水的一处敞轩,四周竹影婆娑,清风拂过水面带来凉意,显得既风雅又不会过于奢华。
我特意选了一身天水碧的素缎长裙,长发只用一根简单的白玉簪子绾起,脸上未施脂粉。
我要的就是这副洗净铅华、甚至带着几分脆弱的样子。
宾客们陆续到来,大多是各府的夫人和未出阁的千金。
她们见到我,目光中或多或少都带着审视、好奇,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
我微笑着与她们见礼,举止从容,言谈得体,仿佛那场闹剧般的婚礼从未发生。
但当我的目光偶尔掠过那些陈列在紫檀木架上的珍玩,尤其在看到那套被精心摆放在丝绒上的白瓷茶具时,眼底适时流露的一丝黯然与不舍,还是被许多人看在了眼里。
气氛渐渐活络起来,夫人们低声交谈,欣赏着那些价值不菲的物件。
直到敞轩入口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
负责通报的家仆声音有些发紧,提高了音量。
“将军府,萧将军到——”
所有的交谈声,像被一把无形的剪刀骤然剪断。
所有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入口。
萧淮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常服,独自一人站在那里。
不过短短数日,他看起来消瘦了些,眉宇间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憔悴与疲惫。
他的视线穿过人群,直直地落在我身上。
那眼神复杂得难以形容,有愧疚,有痛楚,有挣扎,甚至还有一丝近乎绝望的期盼。
我迎上他的目光,心中一片平静,甚至微微颔首,露出了一个主人对待普通宾客的、礼节性的浅笑。
然后,我便转开了视线,仿佛他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迟来者。
“沈伯,”我吩咐侍立在一旁的老管家,“给萧将军看座,上茶。”
沈伯显然有些不愿,但在我的目光示意下,还是让下人在敞轩最边缘不显眼的位置,添了一张椅子。
萧淮的脸色白了白,但他没有说什么,沉默地走过去,坐了下来。
像一个误入他人盛宴的、不受欢迎的客人。
雅集会继续进行。
我如常向宾客们介绍着几件珍玩的来历与妙处,声音不高不低,恰好能让每个人听清。
我的镇定,与萧淮的沉默尴尬,形成了鲜明到刺眼的对比。
在场的人精们心照不宣,很快便恢复了谈笑,将边缘那道孤独的身影视若无物。
终于,轮到了今日的重头戏。
我走到那套“四时清赏”前,芸香小心翼翼地将其中一只绘着春桃的杯子捧起,对着光线。
近乎透明的杯壁上,灼灼桃花与翩跹的蝶影栩栩如生,仿佛下一刻就要活过来。
“真真是巧夺天工。”一位对瓷器颇有研究的夫人由衷赞叹。
我轻轻抚过冰凉的杯壁,声音里染上一点追忆的怅惘。
“家母生前最爱春日,常说生机盎然,万物可期。这套茶具,她珍藏多年,如今……”
我顿了顿,没有再说下去,转而清晰报出价格。
“这套‘四时清赏’,十六件一套,完整无缺,底价八千两,每次加价不少于五百两。”
敞轩内响起一片压抑的吸气声。
这个价格,足以买下京城一座不错的宅院。
一时间无人应声,场面有些冷凝。
几乎所有人的眼风,都有意无意地扫向角落里的萧淮。
这像一场公开的审判,等待着他的抉择。
时间一点点过去,就在有人以为这套珍品或许要流拍时,萧淮站了起来。
他的声音干涩沙哑,像是许久未曾开口。
“我出一万两。”
静。
死一般的寂静。
然后,是无数道目光汇聚成的无声浪潮,汹涌地拍打在萧淮的身上。
他真的买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用一万两白银,买下了前未婚妻亡母的遗物。
为了什么,不言而喻。
我静静地看着他,脸上依然维持着得体的浅笑,心却像浸在数九寒天的冰窟里,最后一点残留的温度也消失了。
“萧将军果然豪爽。”我语气平和,“这套‘四时清赏’,归将军了。”
芸香上前,小心翼翼地将茶具装入锦盒。
萧淮从怀中取出银票,厚厚的一沓。
交接时,他的指尖无意间碰到了我的。
很烫,带着一种不正常的灼热。
而我指尖冰凉。
他像是被火燎到一般,猛地缩回了手。
我接过银票,看也未看,直接交给了沈伯,然后对着萧淮,规规矩矩地行了一个福礼。
“多谢萧将军慷慨,解我之困。”
“解困”二字,我说得清晰又自然。
萧淮的身体几不可察地晃了一下,他接过锦盒,没有再看向任何人,转身大步离开了敞轩,背影竟有几分仓皇。
04
萧淮的离去,如同解开了某种封印,敞轩内的议论声轰然炸开。
“一万两!就为了一套茶具!”
“这真是……色令智昏啊!”
“沈小姐也真是好气度,这般情景下还能如此镇定。”
在一片嘈杂声中,我再次走到了众人面前。
手中,是那沓厚厚的银票。
“诸位夫人,小姐。”我的声音清亮,压过了嘈杂,“今日雅集会所得,共计一万四千七百两。”
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每一张神色各异的脸。
“小女子在此立誓,将此款项,全数捐予‘抚孤院’,用以照料抚养那些在边关战事中失去父亲的孩童。”
话音落下,满场皆惊。
连一直维持着优雅姿态的夫人们,也忍不住露出了错愕的神情。
我将银票郑重地放入一位早已等候在此、身着简朴衣衫的嬷嬷手中。
这位嬷嬷是“抚孤院”的主事,她双手微颤地接过,眼中瞬间涌上泪光。
“沈小姐大仁大义,老身……老身代那些苦命的孩子们,谢过小姐大恩!”
我扶住她,轻声道:“嬷嬷言重了。边关将士浴血奋战,护佑家国平安,我们能做的,不过是让他们的血脉得以延续,让孩子们有个温饱罢了。”
这一刻,之前所有的同情、揣测、甚至些许的看戏心态,都化为了真切的动容与敬佩。
我用萧淮的一万两,为自己,也为沈家,赢回了难以估量的声望与人心。
而他,则用这一万两,将自己钉死在了“薄情”、“奢靡”、“昏聩”的耻辱柱上。
当夜,将军府内。
萧淮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府中,手中的锦盒仿佛有千钧重。
他没有去主院,也没有回自己的书房,而是径直走向柳云薇居住的“沁芳阁”。
阁内灯火通明,药香混合着甜腻的熏香。
柳云薇显然精心装扮过,虽然仍是一身素衣,但发间簪了朵新鲜的玉兰花,脸上薄施脂粉,在灯下显得楚楚动人。
看到萧淮手中的锦盒,她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如同暗夜里点燃的星火。
“淮哥哥!你回来了!”她急步上前,几乎是抢过了锦盒,“你真的把它带回来了!”
她迫不及待地打开盒盖,当那套莹润无瑕的白瓷完整呈现时,她发出一声满足的轻叹。
“真美……比我想象的还要美……”她伸出手,痴迷地抚摸着光滑的杯壁,指尖微微颤抖,“淮哥哥,谢谢你,我就知道,这世上只有你最疼我。”
她抬起头,满眼都是依赖与喜悦,等待着萧淮的回应。
然而,她看到的,是一张毫无血色、写满了倦怠与空洞的脸。
萧淮的眼神,像是穿透了她,望向某个遥远而虚无的地方。
“淮哥哥?”柳云薇脸上的笑容僵了僵,试探着问,“你怎么了?是不是累了?还是……沈云茉又给你气受了?”
听到“沈云茉”三个字,萧淮的睫毛颤动了一下。
他终于将目光聚焦在柳云薇脸上,看着她眼中毫不掩饰的、对这套瓷器的贪婪与占有,看着她因为兴奋而微微泛红的脸颊。
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他拼了名声和前途去维护的女子,竟如此陌生。
他缓缓开口,声音嘶哑得像被沙石磨过,将雅集会上发生的一切,包括沈云茉最后的捐赠之举,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随着他的叙述,柳云薇脸上的喜悦如同退潮般迅速消失。
震惊,错愕,然后是不可抑制的愤怒,在她眼中交替闪现。
“她……她怎么敢!”柳云薇的声音陡然尖利起来,再无平日的柔婉,“她拿着你的银子去充好人!她这是故意做给我们看的!淮哥哥,你怎么能让她这么欺负到头上来?你当时为什么不说话?”
萧淮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他以为会得到些许安慰,哪怕只是一句“淮哥哥,你受委屈了”。
可等来的,却是毫不留情的指责和埋怨。
“说话?我说什么?”萧淮的声音里透出浓浓的疲惫,“那是她卖东西得来的银子,她想怎么花,我有什么资格过问?云薇,你知道我今天坐在那里,像个待宰的牲畜一样被所有人看着,是什么滋味吗?”
柳云薇被他从未有过的严厉语气惊住了,旋即,委屈的泪水迅速盈满眼眶。
“我……我不是怪你……我只是替你不值……”她抽泣着,眼泪簌簌落下,“我为你忍了那么多委屈,背了那么多骂名,我只是想要一件你送的东西,想证明你的心里是有我的,这也有错吗?都是沈云茉,她太恶毒了,她就是见不得我们好!”
又是这套说辞。
萧淮只觉得一阵强烈的反胃和无力感涌上心头。
他看着她哭泣的样子,脑海中却不受控制地浮现出敞轩里,沈云茉那双平静无波、清冷如寒潭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没有恨,没有怨,甚至没有嘲讽。
只有一片彻底的、冰冷的了然,和决绝。
就在这时,房门被叩响,老管家萧忠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带着不容置疑的冷硬。
“大少爷,老将军请您立刻去祠堂。”
萧淮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眼底最后一丝温度也消失了。
他没再看哭泣的柳云薇一眼,转身拉开了房门。
05
与将军府的阴云密布不同,太傅府的夜晚,宁静而平和。
书房里,我与父亲对坐手谈。
棋盘上黑白交错,局势胶着。
父亲拈着一枚黑子,沉吟良久,最终没有落下,而是将棋子放回了棋盒。
“今日之事,处理得极好。”父亲的声音在安静的室内响起,带着欣慰,“借他人之力,成自己之名。这一手,不仅挽回了颜面,更在道义上占据了无可指摘的高处。”
我捻着一枚白子,轻轻放在棋盘一处看似无关紧要的位置。
“女儿只是顺势而为。他既愿意演那情深义重的戏码,女儿便替他搭个更高的台子。”
父亲看着我的落子,忽然笑了。
“这一步,倒是暗藏玄机。看来,你是真的想通了,也长大了。”
我垂眸看着棋盘。
“经此一事,女儿明白了一个道理。女子的路,未必只有嫁人这一条。即使不走那条路,也可以活得堂堂正正,甚至……更有用处。”
父亲深深地看着我,良久,缓缓道:“你能这样想,爹爹很欣慰。往后,想做何事,便放手去做。沈家的女儿,不必看任何人的脸色。”
第二日,宫中来了旨意。
御前总管亲自登门,宣读了皇帝的册封诏书。
我被封为“宁安县主”,赐食邑五百户。
这道旨意,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京城激起了远比雅集会更大的波澜。
县主,虽非公主,却也是正经的皇封爵位,享有实实在在的俸禄与尊荣。
这不仅仅是荣耀,更是一个无比清晰的信号。
皇帝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他认可沈家的做法,认可我的品行。
至于将军府,那道曾经显赫的门楣,如今在舆论与圣意的双重压力下,已然黯淡无光。
册封典礼并不盛大,却足够郑重。
我穿着县主的礼服,接过那卷明黄的诏书与印信,向宫城方向行礼谢恩。
仪式结束后,一位身份尊贵的宫眷特意留下,与我闲话了几句。
她的言辞温和,却意有所指。
“宁安,你可知陛下为何在此时赐你封号?”
我恭谨地回答:“臣女愚钝,请贵人明示。”
她望向北方,那是边关的方向,微微一笑。
“北边的风,近来有些喧嚣。陛下需要一些能‘安稳人心’的存在。”
我心中微微一凛,隐约触摸到了一丝冰凉的、属于朝堂博弈的脉络。
但我面上未露分毫,只是柔顺地垂首。
“臣女谨记,必不忘陛下隆恩,安守本分。”
回到太傅府,已是黄昏。
父亲在书房等我。
他面前的书案上,摊开着一幅巨大的疆域图,烛火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茉儿,”他唤我的小名,声音有些低沉,“过来看。”
我走到书案旁,目光落在图上被朱笔重点圈出的北境区域。
“边关有军报传来,萧淮麾下,似有不稳之象。”父亲的手指敲了敲那片区域,“陛下,已暗中调派别处兵马北上,以防万一。”
他抬起头,目光如炬地看着我。
“萧家这棵大树,根基已经开始松动了。你如今是‘宁安县主’,不再是后宅之中可以随意轻慢的女子。无数双眼睛在看着你,看着沈家下一步如何落子。”
书房里安静极了,只有烛芯偶尔爆开的噼啪轻响。
窗外的天色彻底暗了下来,浓重的夜色包裹着府邸。
我凝视着地图上蜿蜒的防线与标注的城池,半晌,轻声问:
“父亲,若真到了树倒猢狲散的那一日,会不会……牵连太广,伤及无辜?”
父亲没有立刻回答。
他吹灭了书案上的一盏灯,书房内顿时暗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