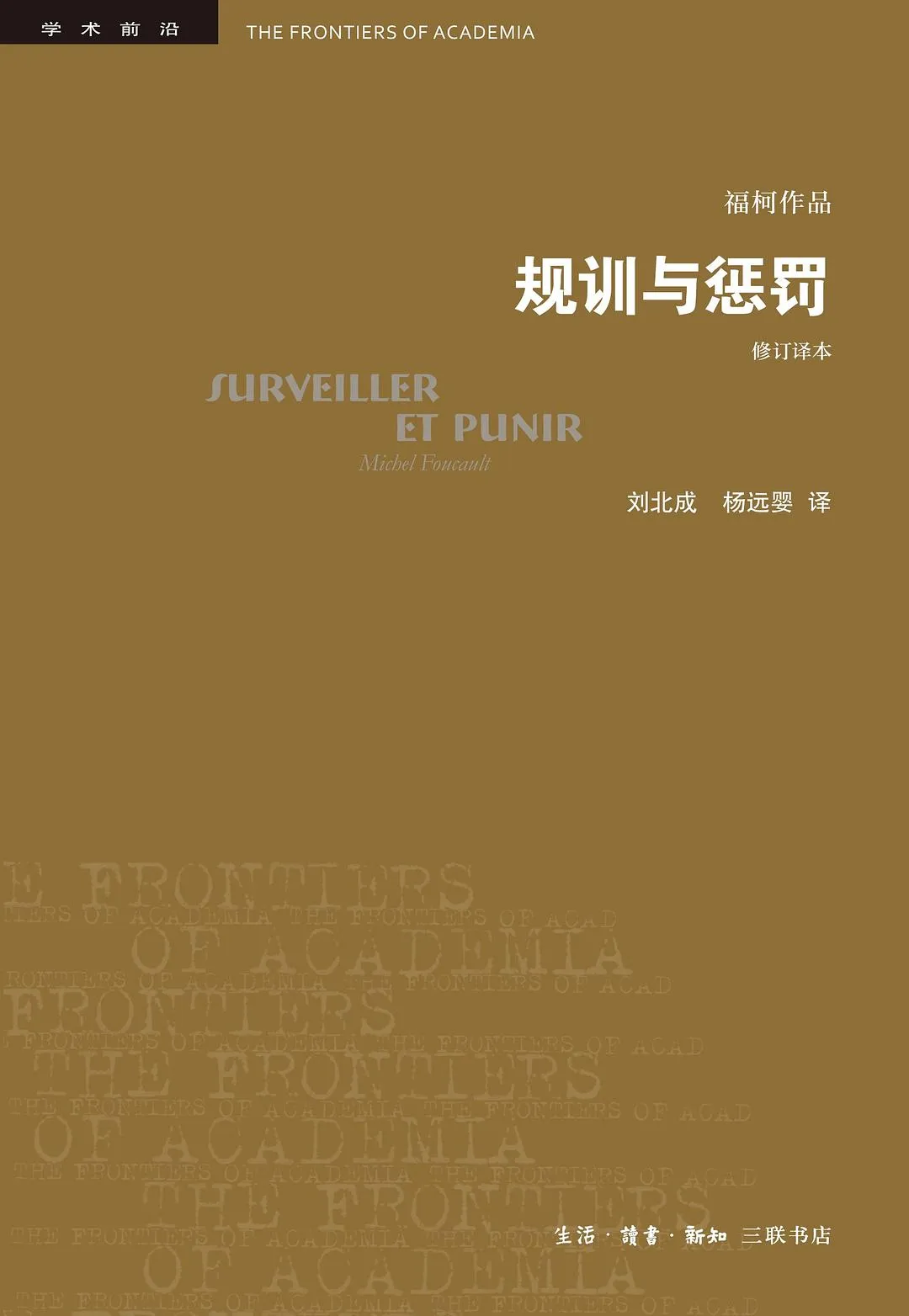
《规训与惩罚》,这本书福柯写于上个世纪70年代。
我本没有动机要翻开它,直到看到《叙事疗法实践地图》的作者怀特提到“人的问题内化倾向”时提到福柯,看到韩综《思想验证区域》偶然展现了福柯书里的“全景敞式监狱”,打开一看的动机便出现了。
这本书,不好啃。读来是一知半解。一在于偏学术化的用词造句,二在于要跟上福柯的视角和逻辑对我来说还是吃力。
此书之后,又按图索骥读了《福柯的生死爱欲》,传记作者米勒描绘了福柯的思想脉络,从尼采到康德到萨特…读着更晕了…
晕归晕,这次的阅读倒是有一股引力一直牵着我磕磕巴巴读了下去,那股引力便是《福柯的生死爱欲》里提到的四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人是什么?”
接下来就谈谈我在这本书里,能知道些什么。
一 宏观的司法史
此书开头上来就是一个重口味,福柯详细描写了刺杀国王未遂的达米安被处极刑的场面,血腥、惨叫,还有旁观的众人。这是君权时代的司法体制,内部判罪,公开行刑,以儆效尤。
罪犯是对君权的侵犯,而面向众人的公开行刑是对这种侵犯的报复和对君权权威的重申,看,这就是违抗你君上的下场!
这是公开行刑的意图,但有时确实人算不如天算。当罪犯被载着游街示众,关于犯人的八卦和民间故事被制成册子在坊间流传,当罪行在流传的氛围里染上某种悲壮色彩,当极刑之下的面孔显露对权威的蔑视和谩骂,公开行刑成了某种对抗权威和暴力对抗暴力的“民众狂欢”。
君权控制了罪犯的身体,但它控制不了罪犯在行刑现场能说什么、想说什么。民众不是在刑场被加固成顺民,而是暴戾之心在人群中被不断左右撩拨。
这是君权时代的司法惩罚,它充满了血腥暴力和对肉体的蹂躏。19世纪,这种做法被认为惨无人道,然后司法制度发生了变化。
公开行刑被废止,以前的内部审判变成了公示开庭,而刑罚则转移到了内部监狱。然而,这是人道主义的良心发现么?未必。
每个时代都会有被默认的非法活动的存在。当君权之下的暴戾之心蠢蠢欲动,资产阶级允许了它在民众之中势如燎原,直至君权被推翻,直至这股燎原可能会殃及新社会的根基——够了,我们要的是顺民,而不是暴民。
“与其说是确立一种以更公正的原则为基础的新惩罚权利,不如说是建立一种新的惩罚权力‘结构’…权力应该分布在能够在任何地方运作的性质相同的电路中,以连贯的方式,直至作用于社会体的最小粒子。”(《规训与惩罚》)
19世纪的新社会,没有五马分尸、凌迟处死,对权力侵犯的惩罚从一种报复和恫吓行为变成了一门经济学(如何以最小的惩罚措施发挥出最大的遏制犯罪的效果?)、一门美学(如何营造表象,让民众生发出自我遏制的犯罪联想?)、一门心理学(罪犯成了监狱中的“患者”,他们要经历被改造)…我有理由怀疑,19世纪各种关于人的学科的兴起,估计和司法惩罚的研究是相互纠缠着的。
以前,君权控制了身体,最多就是把人噶了,而现在,权力可达的程度是,再造可用的肉体。
与开头的重口味完全不一样,描写19世纪的监狱时,福柯提到了一张日程表,几点到几点,犯人起床、做工、祷告等等。血腥味散了,岁月静好的秩序之下,肉身被详细规划在时间表里。而这样的时间表,学校里、军队里,也有。
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被训练成什么样子,被放在什么位置,做怎样的事。它无需控制你的生死,但它会决定你能想些什么、说些什么。
如果以前的公开行刑是君权时代的仪式感,那么19世纪的权力仪式感便是各种“检查”,各种对人的“量化”。这便是福柯口中的肉体政治解剖学。
“这是一种操练的肉体,而不是理论物理学的肉体,是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肉体,而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是一种受到有益训练的肉体,而不是理性机器的肉体。”(《规训与惩罚》)
这是一种非常精妙的机制,它的目的是塑造同一的集体秩序,但它的电路并不单一,它的线路千丝万缕,分别通往每一个不一样的个体。你是谁,它可知道得一清二楚。
“个人的美妙整体并没有被我们的社会秩序所肢解、压制和改变。应该说,个人被按照一种完整的关于力量与肉体的技术而小心地编织在社会秩序中。”(《规训与惩罚》)
此书最有名的估计便是福柯所提的边沁设想的“全景敞式监狱”,所有牢房隔成一间一间,环形围绕着中间的监视塔楼,被监视的人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牢房里的人却看不到塔楼里一丝一毫。
福柯用笔霸气一挥,指向监狱外的社会,其实,这样的“监狱”无所不在。
至此,为了报复权力侵犯的惩罚演化成了一种温柔规训,而且成了一门可移植的规训技术。“监狱”,原来,是一场写实的比喻。
“当个性形成的历史一仪式机制转变为科学一规训机制、规范取代了血统、度量取代了身份、从而用可计量的人的个性取代了值得纪念的人的个性时,也正是一种新的权力技巧和一种新的肉体政治解剖学被应用的时候。”(《规训与惩罚》)
为了人道主义所作的改革,实则是更深的权力钳制,福柯的笔用力一戳,那所谓的知识、教养、道德,是不是也是某种由权力生成而被内化在心的敞式监狱呢?无需暴力,只需一道凝视的目光,便可大批造就温驯的现代人。
那这权力,是什么,来自于何?
二 微观的个人法西斯
福柯写作此书期间,曾亲历上个世纪60年代的政治风暴,甚至在执教的学校和学生们一起朝警察扔砖头。这是某种政治上的“极限体验”。
如暴力、非法、犯罪、疯癫、自杀、SM等,这些游离在理性和非理性边缘的“极限体验”是福柯一生所着迷的探究。
如果权力造就了如今这个理性世界,那何不让非理性来打破这一切,通过否定自身来寻找自身呢?
虽然《规训与惩罚》被福柯称为他的第一本代表作,他的残酷的社会批判力亮瞎众人,但本书也有学界硬伤,比如它虽列为史学著作,但“它具有福柯批判方法的那种令人不安的特点:难于确定,易于感觉”(《福柯的生死爱欲》)。
他的笔大刀阔斧,在论述历史,在解剖社会,他同时也在寻求自我的问题:“我怎样变成现在这个我,以及我为何要为做现在这个我而受苦受难?”
福柯的书可能描述出了社会的事实,也可能不是。我更情愿将它看作一种福柯视角,它补充着我能知道的部分。
当年,福柯并没有持续参与社会运动,或许,体验过后,他意识到批判社会容易,但改造社会何其艰难。
如《福柯的生死爱欲》这一段话所言:
“《规训与惩罚》最重要的段落都是最抽象的。这就是该书第一章为数不多的几段话,福柯在其中简洁地阐述了他的‘权力’概念的某些含义。
他现在这样断言:如果权力是‘被行使的而不是被占有的’;如果权力实际上是散在的,而不是集中在某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阶级手里;如果权力只能通过‘和某个知识领域相关联的政体’来理解;如果这种知识的影响可以在每一个单个的人的自然倾向和爱好中被识别出来;
——那么,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旧公式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为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除了需要改变经济和社会之外,还需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和我们所有的旧‘认识’方式。
因而,‘夺取’和行使某种专政式的权力,可能只是在新的名目下把各种旧的隶属化形式再生出来,就像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显然已经发生的那样,——那里,像同性恋者和吸毒者这样的人常常一如既往地受着粗暴的待遇。”
权力来自于统治阶级吗?是,也不是。
是,是因为统治阶级比常人掌握着更多资源和力量;不是,是因为统治和被统治只是自古以来的一种权力认知形式。可能统治者变了,但如果这个认知形式一直没有被打破,那社会运动之后还是新瓶装旧酒。
权力,来自于哪里?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它来自于所有人认知认同的合力。
整个社会存在规训的合力,分散来看,单独的个人身上又何尝不存在规训的权力呢?
当家长要求孩子变成自己眼里的样子,当领导让下属按特定风格行事,当恋爱一方以争吵或暴力强迫另一方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如福柯所说,每个人身上都有法西斯主义的影子。
我大胆断言,凡是存在两人以上的地方,就必有规训的存在。
那,规训是好的坏的?或能否这样一言以蔽之?正如道德、知识、教养,一样。这是一道很好的思考题。
总结之,福柯此书给了我一个甚是惊艳的提醒,那便是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它没有那么得远在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