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本文共2823字,阅读时长大约6分钟
前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中的这句千古名言,描绘的正是西周王朝鼎盛时期的恢宏气象。然而当烽火戏诸侯的闹剧落幕,镐京城的狼烟真正升起时,人们才发现:没有枪杆子支撑的王土宣言,终究只是一个纸糊的王朝幻影而已。

今天老达子要跟大家探讨的,就是西周王朝最引以为傲的两支精锐部队——西六师与东八师。这两支堪称西周版中央军的武装力量,曾经是周天子震慑诸侯、征讨四方的利器。
可当犬戎的铁骑踏破镐京城墙时,这些精锐之师却神秘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它们究竟去了哪里?为何在王朝存亡之际集体失声了呢?
西六师与东八师到底是什么?“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诗经・大雅・棫朴》中的这句诗,生动记载了周天子亲征时六师相随的盛大场面。这支被称为“西六师”的精锐部队,正是西周王朝最核心的军事力量。
根据《周礼・夏官・司马》记载,西周实行“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的编制。西六师作为天子直辖的中央军,常驻镐京周边,总兵力约3.5万人。他们装备精良,《考工记》详细记载了西周战车“车轸四尺,谓之一等”的制造标准,这些战车部队正是西六师的核心战斗力。
1980年,陕西长安县出土了多友鼎铭文,这上面记录了很多西六师的作战情况。铭文说多友率领西六师在郤地大败猃狁(即犬戎),“折首执讯”,俘获战车百余辆。这说明直到西周晚期,西六师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
而东八师的建立,则与周公旦的深谋远虑密切相关。《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公东征后,“营成周洛邑,以镇东土”。为了控制新征服的东方领土,周公在成周(今洛阳)组建了八个师的驻防部队,这就是东八师。
东八师的驻地分布极具战略眼光:伊洛河流域部署四个师控制中原要冲;荥阳一带部署两个师扼守虎牢关;其余两个师则驻防商丘附近,形成对东夷势力的战略威慑。这种布局使东八师成为周王朝控制东方的重要支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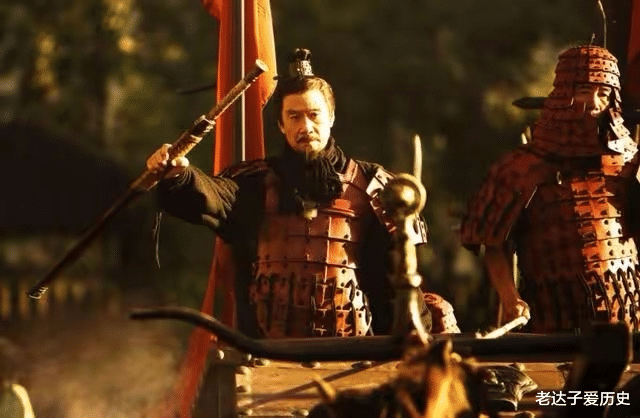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东八师还承担着特殊的“监军”职能。《周礼》记载其负有“监诸侯之邦”的职责,实际上是在诸侯国境内驻军监视。这种独特的军事部署方式,在世界古代史上都极为罕见。
两支精锐一西一东,互为犄角:西六师卫戍王畿,震慑西戎;东八师镇守中原,监控诸侯。它们共同构成了西周王朝的军事支柱,也是周天子能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根本保障。
然而谁又能料到,这两支看似强大的军队,最终竟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
西六师:死在“自己人”的刀下西六师的消失跟周幽王有很大的关系,而周幽王的麻烦,是从废太子开始的。
他的王后是申国的公主(申侯的女儿),生了个儿子叫宜臼(后来的周平王)。可后来他爱上了褒姒(褒国进献的美女),不仅把王后废了,还把宜臼的太子位也废了,立褒姒的儿子伯服当太子。
“幽王三年(或说五年)宠褒姒,生子伯服;八年废申后、黜宜臼,立伯服为太子。”——《史记》
申侯急了:“我女儿被废,外孙的太子位没了,这口气怎么咽?”于是他偷偷联系了“犬戎”(西边的游牧民族)和“缯国”(南边的小国),说:“咱们一起打镐京,灭了幽王,立宜臼当王!”
周幽王也不是吃素的,他听说申侯要造反,立马调“西六师”去伐申国(今河南南阳)。可他没想到,这一去,就是西六师的“绝路”。

《竹书纪年》(战国时的史书,比《史记》更可信)里写得很清楚:“幽王十年,王师伐申。”,可史料对伐申的细节没有记载,《史记》里只写了“幽王战败被杀于骊山”。
但根据当时的推测,西六师的主力应该是跟着幽王出了镐京,往南阳开。而申侯肯定也早有准备,他带着犬戎的骑兵绕到了骊山脚下,等着幽王回来。
等西六师走到骊山时,犬戎军突然从两边的山上冲下来,左边是犬戎的骑兵(骑着蒙古马,速度快),右边是申国的步兵(拿着长戈,能扎能刺),把西六师夹在中间打。
《史记·周本纪》里说“遂杀幽王骊山下”,其实被杀的不只是幽王,还有西六师的几乎所有士兵。
考古学家在“丰镐遗址”(镐京的遗址,今陕西西安)发现过一个“兵器坑”,里面有几十把刻着“六师”的青铜戈,戈刃卷了边,上面还有深褐色的锈(应该是血渍),有的戈柄上还缠着麻绳(士兵握过的痕迹)。
东八师:早已身不由己其实东八师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镇压东方诸侯(如齐、鲁、宋)及夷狄(如淮夷、荆蛮)。然而,它却是由多民族混编而成的,多民族混编的特性本身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当周王室衰微时,这些部族士兵首先想到的,不是效忠天子,而是如何保全自身。
周宣王时期,东八师主力因长期征战淮夷消耗殆尽。为补充兵源,宣王试图效仿现代人口普查,“料民于太原”(今山西一带)。然而,这一举措遭到了贵族强烈反对。《国语·周语》记载:“仲山甫谏曰:‘民不可料也!’”
贵族们担心,天子按人头收兵,会进一步削弱他们的势力。改革失败后,东八师只能依赖残余部队,分散为“炎师”“古师”“鄂师”等小股势力。这些部队要不依附诸侯,要不就得被夷狄给吞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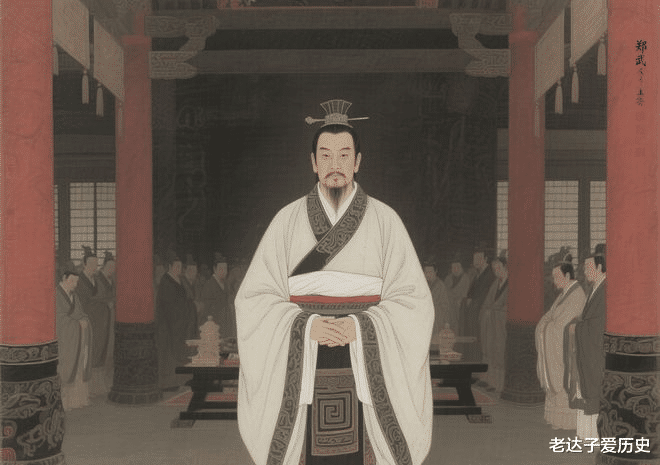
西周末年,郑国崛起了,郑桓公担任了司徒。司徒的权利有多大呢?简单来说,每当有大规模军事行动或者田猎时,司徒就会举起令旗,号召百姓组建军队,并负责管理这些人。
“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所以在犬戎攻打周幽王的时候,郑桓公没有让他们去平定王室内乱,而是自己假公济私,发展成了自己的私人力量,为郑国打稳根基。
西周的致命教训西周的军事体系其实就像一具被蛀空的巨树一样,在犬戎的第一波冲击下就轰然倒塌了。这场看似突然的军事失败,实际早就在制度层面埋下了2个致命的隐患。
1、军事制度的结构性腐败《国语・周语上》记载的“宣王料民于太原”,就暴露了西六师兵源枯竭的危机。
2003年陕西眉县出土的逨鼎铭文显示,西周晚期军队高层已形成世卿世禄的僵化体系,军官职位早就成了贵族子弟的镀金跳板,真正懂军事的职业将领基本都被边缘化了。
更严重的是装备更新的停滞,虽然《考工记》详细规定了“弓长六尺六寸,谓之上制”的兵器标准,但咸阳的车马坑考古显示,西周晚期战车更新速度比早期下降了很多。

当犬戎都用上了射程更远的复合弓时,西六师还在使用射程仅百步的单体弓,这怎么能打得过呢?
2、战略预警机制的失灵西周原本建有完善的边防体系:《周礼・夏官》记载设有关隘司险、烽火台掌修等职位。但幽王时期的烽火戏诸侯闹剧(见于《史记・周本纪》),彻底摧毁了这套预警系统的公信力。
更深刻的问题在于情报收集能力的退化。西周早期设有行人制度(《周礼・秋官》),专门收集周边民族动态。但到幽王时期,这个系统已被《诗经・小雅》讽刺的营营青蝇式腐败侵蚀了。官员都在忙着争权夺利,根本没人关注真正的边境危机。
老达子说西周的灭亡,本质上是“枪杆子”的丢失:当周天子失去对西六师、东八师的控制,当诸侯不再害怕周天子的军队,王朝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后来的历史,其实一直在重复这个教训:比如唐代的“神策军”(中央军),因为被宦官控制了,最后变成了宦官的私人军队,唐朝也跟着灭亡。还有宋代的禁军(中央军),因为重文轻武,战斗力越来越弱,最后被金兵灭了。
历史从来不会重复,但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