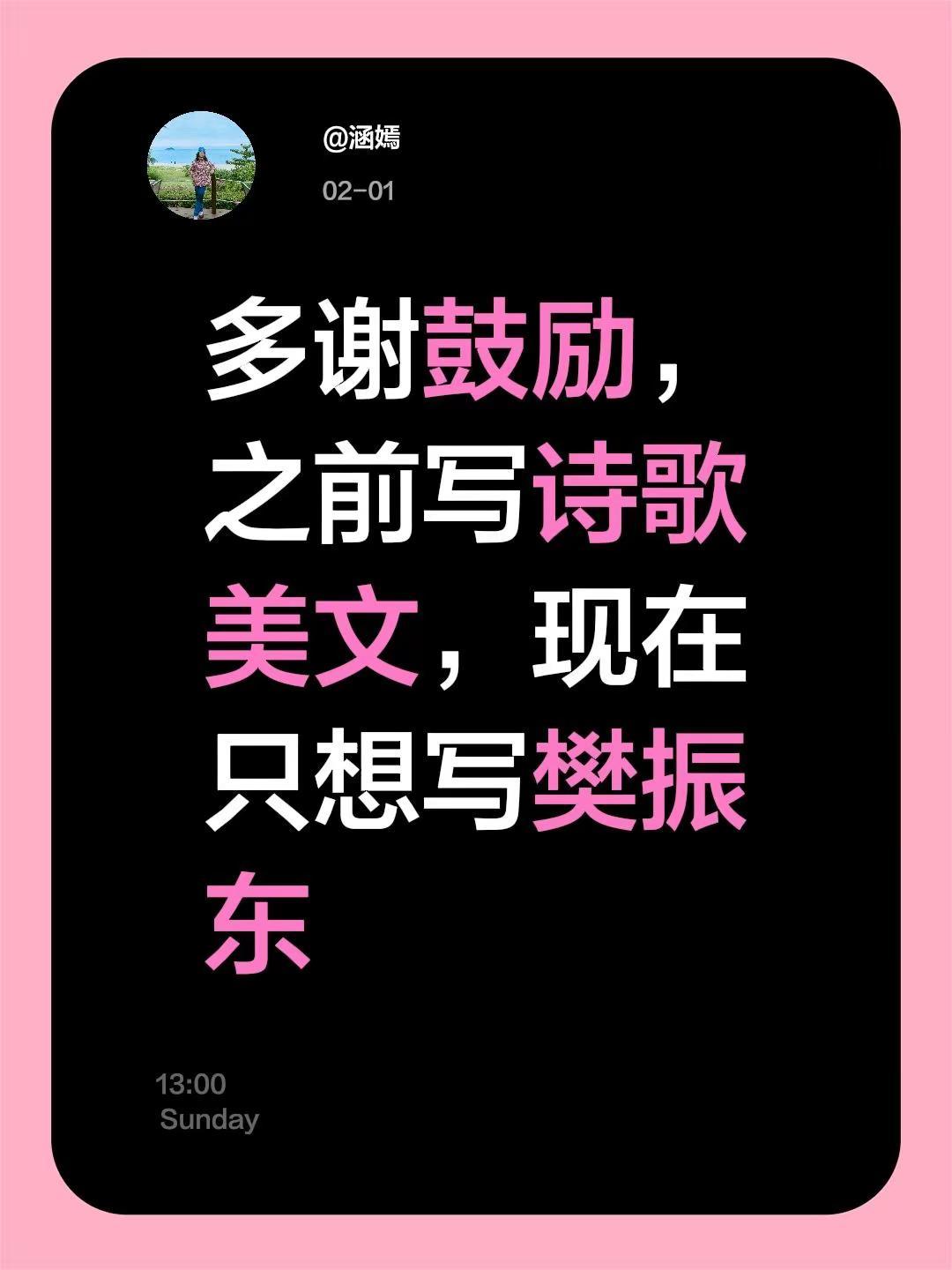一、 作家
二、 收入
三、 稿费
四、 外事
五、 出国
六、 彩电
一、 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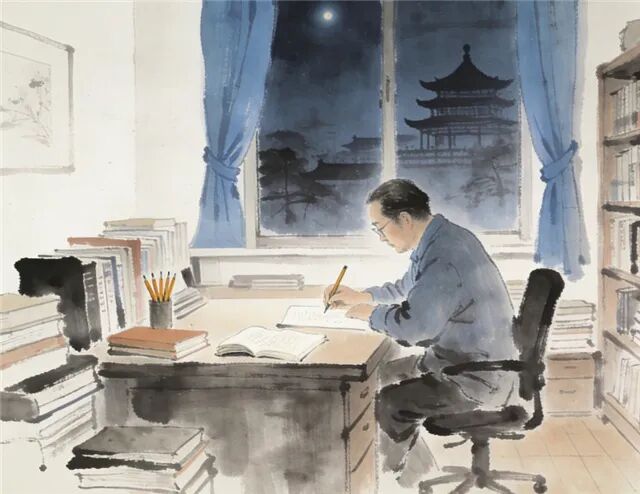
谁算作家?
一九八〇年代,一个人在中国能否算得上是作家,首先要看他是否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省一级的分会会员,相差一个级别。名正言顺的,必须是中国作协会员,这是关键。一旦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就可以被称为作家。省一级的会员是否也能算作家,概念不确定。虽然这类作家不会理所应当地自称作家,但在履历上都会注明自己是某分会会员。至于能否得到全国作协的承认则另说了。中国作协外联部在选派作家组团出访时,仅分会会员是不会考虑在册。
这种官方的“作家”称谓,以中国作协会员资格为前提,在当时是文学界的共识; 而想入会,前提要有作品。五十年代,丁玲有过“一本书主义”的提法,这意味着想当作家,起码要出一本书; 反之,没出过书的人就失去入会资格,成不了作家。零星发表再多、数量再大,只要没成集出版都不足为数。

北岛
除官方以会员资格来判定作家外,民间也有虽不是作协会员身份,但被社会承认是作家、诗人的,这种现象极为少数,最典型的要数北岛。
海峡对岸的旅美女作家陈若曦1985年春来京见胡耀邦时说:北岛这么好的作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诗人,但这次“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不让他去,她认为不妥。胡马上就问:“是我们的会员吗?”“当然不是。” 这问答间说明了两种不同观念、不同判断准则。在陈看来,只要有作品,名声在外,得到社会承认,有知名度,不仅是作家,而且还是好作家、名作家; 而胡首先要问问是否作协会员。所以说,一个人能否算作家,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
像北岛这样的民间作家,其生活来源除靠一份工作,就要看稿费了。自“西单民主墙”、“星星画派”事发后,北岛因此失去工作,没有单位再要他。按他自己说,即使无业,他也必须每天去街道办事处报到。北岛彼时的身份决定了他当时不可能在官方刊物发表作品。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杂志社要考虑的政治因素还很大,“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还没松,所以他不但工作成问题,若想发表作品,他只好跟伙伴们一起自己创办刊物。
二、 收入

然而,那些身为作协会员的作家又是何以为生?
八十年代初始,能称得上作家的,一般都在职,有一份具体工作,譬如在杂志社、出版社当编辑,任职拿工资;或在中国作协机关及地方分会当干部,根据行政级别取酬。那时有个单位很重要,这关系到分房,
住房是职工的最大问题。对在职作家而言,就不存在生活补贴问题。然而那时有一批专职作家,数量不是很多,就是说,这批作家本身没有工作单位,只是专业创作。要成为这样的专职作家,必须是中国作协会员,地方会员还不够资格,他们都具有全国知名度,是国内出类拔萃的一流作家,前提是发表过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品,或获过文学大奖。这类作家,国家给予补贴是为保障他们有经济来源,解除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得以安心写作。张洁就是当年这种专职作家中的一个。
此外还有黑龙江的张抗抗、上海的王安忆、天津的航鹰、大冯、山东的张炜、西安的路遥等。他们从国家领取的生活补贴不等,实质上这类补贴是一种工资待遇。至于决定这份工资多少的前提是什么,会以他们成为专职作家前的收入作参考。
在作协时,我做过比较,确认专职作家的收入均在大学生工资之上。拿自己举例,一九八五年元月我进文化部,拿的是研究生标准工资,每月 62元,高出本科生一级,6元; 同年三月我任职作协外联部,工资没动。那年头除工资外不发奖金,唯一补贴是5元独生子女费,而且文革前后十几年工资基本上没变。
印象中,如上提到的作家,补贴都高出我的工资,张洁工资最高,这或许跟她的年纪和工龄有关,能拿到 90多。张抗抗、航鹰、大冯都能拿到 70、80以上;相对来说,王安忆、张炜要低一些,但他们也年轻。就是路遥是个例外。
有一年西德作家团去西安访问,我跟路遥谈及他的收入,得知他的专职作家工资不到 60元,跟本科生相等。路遥的一生,物质生活始终是匮缺的,出访西德时他说,《人生》获奖,去北京的路费还得找人借。获奖后买书送人加应酬,还了债已所剩无几。在西柏林因推荐他的电影给《金熊奖》,谈及小说时路遥说:为等米下锅急需稿费,《人生》发表得很仓促,只写了中篇,几乎是个提纲。往后三年,他将《人生》扩展成了《平凡的世界》。

莫言
莫言的工资是个例外,跟地方上不一样。他在军队艺术学院,属部队编制。据他日前回忆,他那时已享受行政正连级待遇。我去微信问及此事,他找财务处还查实了三十八年前的老底。称工资单尾数达120强,里面当然已包括独生子女费和军队补贴。按常情,部队福利好过地方。
2008北京奥运年我回国拍电影,在京与张洁等作家重逢,她压低嗓门说:“小金你真不知道,我们老作家现在日子有多难过!政府说了,你们的工资都涨了三十倍了,不要再抱怨了!你想想,当时100元多好花,现在的 3000顶什么用?!” 这同时也证实了张洁当年的工资不过 100元。
中国从1962年至1977年,15年全国基本工资没涨,在职人员平均约42元,1978年涨至48.50元。恢复高考后,一个七七级毕业生月薪:北京56元,上海58元,杭州54元,这是三个不同类别的地区差价;工人满师定级,一般都到了二级就不动了,除特殊技工外。全国工资大致从36元至42元,而且近二十年基本没加。

日前,天津老作家航鹰在回忆当时职业作家工资时说:“八十年代中期,全国文人作家平均工资约 55元。在文艺界,天津只有我和关牧村‘跳级’至 62元。” 这是我一九八五年春进作协机关后才注意到了作家们的收入。
我去微信问航鹰:
一九八八年我们一同出访奥地利,你是专职作家,还记得月薪有多少吗?
航鹰答:
“经我和老伴共同回忆,我们那一代人从1962年至 1977年没涨工资,平均约42元。1977年涨到48元,80年代中期约55元。当年的级差6至8元,所以到了我出国留学的1988年,大约70多元。”
航鹰还讲了一个有趣的稿费故事,很具有历史感。她说:“我记得1977年恢复稿费,《天津演唱》发表了我的独幕剧本《计划计划》,那是我此生第一次得到稿酬,30元。那天沙尘暴刮黄了天,我说明天再去取吧,我们家的刘先生答应了,过了一会儿他还是决定骑车冒着风沙而去。因稿费单一旦寄去了“天津人艺”,我们须去南开大学对面的邮局取款,离我家很远。当老刘回来时,都成了个土人儿了。那是我们家庭的节日啊!能顶上半个月的工资呀!那年我女儿8岁,儿子6岁,是我们最穷的日子……”
航鹰结尾说:“谢谢你让我们回忆起当年贫穷时的欢乐!”于此,作家昔日生活可见一斑。
我在《路遥的德国之行》一文中提到,因路遥在西德被盗三百美元,我给他算过一笔账。按当时私下交易的美元价,就满打满算把路遥每年年薪算成八百元,他也一下子丢了整整四年的工资。此外,按当时三十至四十岁年纪的作家,正常收入除去生活开支,恐怕一辈子也买不起彩电,因为我们的收入,其中百分之八十是用来吃饭的,而且绝大多数家庭没有积蓄,是月月光。当时,二十吋彩电,市面价达一万元以上,西单商场有陈列。那年,万元户是全国首富。普通家庭包括作家在内,如果不出国就一辈子甭想有彩电。这么说来,张洁口口声声称,她写作一辈子就是为了给她妈买一台彩电,就不足为奇了。
到一九八八年年底我出国进修,中国作协刚恢复职称评定,我有幸被评上正翻译级,听外联部领导说,工资按行政靠副处,月薪涨到了93·50元,加五元独生子女费,一共不到100元。
三、 稿费
当年的稿费在作家生活来源中占什么位置?
除了工资,作家们日子想过得宽裕,尤其是专职作家,就得靠稿费。专职作家没有坐班的单位,也就失去了许多单位福利,尽管他们的人事关系会落在某一机构,但单位里不时的物质分发就酌情而定了。那时虽不发奖金,但是单位福利如分食品和生活用品不断。别说逢年过节的,就是平常机关后勤处会时不时地弄来食物或生活用品在员工中分发,像肥皂、洗衣粉、肉类等是常有的事。中国作协傍着文化部,我们外联部时而也去文化部传达室后面的小侧院买价廉物美的内部食品。从这点而言,专职作家不坐班,就没了单位福利,生活压力会增加。
一九八五年前后的稿费标准,普通稿子一千字七元,能拿到八元即是例外,要拿到九元,就是名家特约稿。多年后好的稿费才涨到了千字十一元。记得一九八八年我翻译了两部长篇小说《香水》和《狂人辩词》,拿到三千多元的稿费,那是一个天文数了。
根据“人尽其材,物尽其用”的原则,求得作品发表的极大值,作家们当年写稿、投稿,最大经济效益是“一稿三酬”,若能如此,就是“名利双收”:写出文章、小说后,力求三回稿酬,这样发表几率高,知名度就大,进账也多。当年作家们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加上社会活动多,应酬频繁,开支也大。
写了稿先找报纸发表,拿一回稿费;发表后再投杂志或刊物,因杂志、刊物的形式不同于报纸,不影响再次发表,如此再拿一次稿费;最后稿件多了合成集子出书,又得一次稿费。当时流行这么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有这样才能创收,增加效益。

路遥
篇幅大的作品或小说,虽一次性稿费较多,但精力投资也大,所需时间也长。若生活窘迫、吃了上顿愁下顿的,部头大的稿费一时等不来,就像路遥,为解燃眉之急,把长篇写成中篇发表。
从我自身经验,稿费最快、最便捷的要算投小稿,时间短见效快,花不了三个钟头写一篇,写个文艺、文学动态,报道一下国外新书,作个内容提要写个简评,都是唾手可得。
彼时《文艺报》在作协机关背后,编辑部同志时不时跑来要消息。机关订有德国周刊《明镜》、《明星》、《南德意志报》等,读到外国文艺动态或奖项颁发、新书发行,几百、上千来个字编个简报花不了多少时间,而且此类花絮稿还很受欢迎,会让版面显得活跃而丰富多彩。
写稿就有稿费,给稿费至少十元,再少了会给不出手。想想工人月薪不过四十元,花三小时拿人家四分之一月薪,这种付出经济上很划得来,所以每次接稿费单都会战战兢兢的。送来的汇款单,邮局就能兑现。
中、长篇小说除出书印行外,还有被改成剧本的机会。那些情节适合改编电影或电视连续剧的,更为理想。如果作者本人改编,当然求之不得,发表剧本后可以来一次稿费通吃;就是别人改编,因原作是自己的,发表时会有稿酬分成,这不失又多了一次收入。像莫言的《红高粱》被拍成电影,当然又多了一份稿费。
因正写到这一段,提到当年的一稿多酬,想到了莫言 《红高粱》改编后是否拿了稿费?有多少?月前我去微信问他有多少分成。他没直接回答,因1987年在波恩时,我记得他说过给了他稿费。没想到今天莫言在《星期一节目》里回答了我的提问:“稿费 800元”,而且他觉得当时是很多的钱!
是啊,航鹰为了30元稿费当时全家不是还兴奋了好一阵子,让她至今难忘!还有我在《莫言往事》里提过的:是因为他的小说写得好,张艺谋才把它拍成了电影。我的观点莫言在节目里快乐地表示了完全同意!
随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举国上下经济搞活,一派沸腾的经商氛围,文化、文学日趋市场化。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于家庭录像机的普及,作品拍成电影被制成录像带或碟片,其发行数量之大,让作家跟导演、制片人一样,版权分红就海了去了。
而且那时还没实行缴纳个人所得税,稿费再多都是如数尽收。到后来私有经济占据了更多的位置,作家当老板,文人下海经商,文化产品商业化成了日常现象。有一年,设计上海机场的工程师徐总率团来慕尼黑跟西门子谈判完后来我酒楼设午宴,那位长者虽不是文艺界人,但是个文化人,文学修养极好,稍稍一聊,上海文学界、出版界的知名人士、作家他都很熟。得悉了我的背景,他笑我弃文从商,染上了铜臭气。我说是生活所迫不得已,也顺应了国内“文人下海”的大潮流。他说我不一样,我是“文人下海,一下下到了地中海。”
……
几年的作家团出访,有个别团涉及到采访费、版权费,我们也称“稿费”:1985年王蒙带去西柏林的那个团,白纸黑字地跟德方签了合同,每人到手一千西德马克,买断了我们在西柏林十天的音响、影像、文字等媒体版权。介绍时,这钱名义上说的是版权费,但实际上其中包含了一定次数的餐费。就是说,只要组委会的活动有用餐招待,那顿饭自然是免费;但碰上没有活动安排,各自用餐就得自理,害得大家慑于下餐馆。那可是硬通货!按议价,一顿饭要吃掉150元人民币。那时,大学毕业生在京月薪56元,研究生加6元。为了彩电大家都很省。
康濯、航鹰、柳萌加我的访奥团,零花钱给得比较好,但事先明说了其中已包括版权费。我们主动向德方交涉版权费只有一次,那是作家团诗人公刘、少儿出版社社长王一地、上海作家赵长天、陕西评论家王愚和安徽刘祖慈加我,是访西德下萨克森州团,每人给了300马克零花钱。因有了以往出访经验,给钱时我问了一句:这钱已包括了媒体版权?州文化科技部部长说没有,任何音、像采访需我们自己跟媒体谈。结果德方除电台采访,电视台还要录制节目。团长建议我向媒体问清版权事宜。记者当着我的面电话请示,后每人追加200马克零花钱。那可是一大笔钱,为一个大学毕业生两年的工资,更何况还是外汇!……
1985年秋,我在作协外联部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声称需要找一位中国女作家,配合拍摄纪录片《中国作家的一天》。说话口音听得出是外国记者,他是当时影视界新秀沈丹萍的丈夫吴伟(Uwe Krauter)。沈丹萍因出演《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主角而一举走红,一夜间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吴伟称,这部系列电影要拿去德国公映,我才知道吴伟原来是德国人,接下去的交流改用德语就顺畅多了。
吴伟点了张抗抗的名,大概是我们跟他妻子沈丹萍同属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年龄段吧。那天傍晚我陪抗抗去「友谊宾馆」见的吴伟,还见到了沈丹萍和她的几个小姐妹,三四个女孩子正出浴从卫生间出来,那时能洗上一个热水澡都是奢侈。跟吴伟的谈话,我们对拍摄构想已谈得很细很深。取景放在长城,张抗抗需要手拿一本文学杂志,卷起握在手中,在长城上迎面缓步走来……
就是因为吴伟没有提及拍摄报酬的事,我们且又耻于主动提出演费,毕竟拍摄程序不是一蹴而就,要花去多长时间事先更无法估计,而且取景又在离开北京较远的长城,当时的交通跟现在无法相比。此合作项目最终不了了之。现在可能有人会说,为什么不主动问一句呢?然而,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何等难以启齿谈钱,更何况是主动要钱呢!
四、 外事
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而且工作一旦碰上与外事搭边,八十年代更是肥得流油。

中国封闭了十年,几乎没有外事往来,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跟西方几乎断了交往。乘改革开放东风,进入八十年代,我国外事活动一下子繁忙了起来。随不断加深与西方国家的人员交往,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了外汇。
那些年,凡有机会出席外宾招待会或宴请,外事即是美差。宴请怎么也少不了吃香喝辣。在缺油水的年代,能有机会打打牙祭是人心所向,当时买肉还要肉票呐!我们读研时跟本科生同住一楼道,国家每月发我们半斤油票,宿舍里煮挂面加一点菜籽油,满楼道宿舍的同学都跑出来大声嚷:“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缺吃的年代,一点油腥味就那么敏感,日子过得清贫的作家也相去不远。
平日里作家们喜欢清静,躲起来写作不为人知,但外联部是个例外,一到有外事活动召集,他们会人人一呼百应。这当中还自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外联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物色好了某个作家,决定安排他组团出访,有了目标后会先把他拉出来练练兵,接触一下外宾,适应适应外事场合及涉外纪律,这样到了出访时就不会感到唐突。想到有机会出国了,回来可以买彩电,谁都会兴奋异常!张抗抗曾对我笑着调侃,说,我们作家谁人出国,还不是你们外联部掌握着生杀大权!
那时,外汇是人人求知若渴的好东西,回国后在出国人员服务部买彩电必须用外汇。这种外汇也叫“硬通货”,是在国际上能自由兑换的货币。
当时的人民币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很遗憾不属于硬通货。现在国家强大了,人民币在国际间流通也坚挺了。那时,东欧国家的外汇拿回国不能用。冷战时期,东欧阵营虽是兄弟国,但货币不流通,彼此间不能自由兑换。
这种状况体现了货币的信用值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其中包括充足的商品市场。假设一下,若当年在莫斯科能自由兑换人民币,苏联人还不怕中国一夜间把莫斯科买空?如果苏联卢布在中国能任意流通,我们收了大量卢布,明天拿去苏联用时,万一卢布贬值了怎么办?那是因为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货币坚挺不起来。跟今日中国已大相径庭。经济不繁荣,货币就疲软。
职从外事工作,避不开的体验是,八十年代的外币换汇不失为一个生财门径,而且当时还颇为流行,这也是继文革后一段短暂的中国现代史。
那时我国实行“双币制”,是特殊时期的一段特殊政策。除普通百姓日常用的人民币外,还有人民币外汇券。外国人拿外汇去银行兑换,得到的是外汇券。在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商店等涉外单位及饭店,货品琳琅满目,质量上乘,但必须用外汇券,因这些机构本意只跟外国人做生意,国人想买也须同样付外汇券,而且商店不对国人开放,不做外事工作的普通百姓进不去。但在普通商店、街市上,就是外国人也同样可以用普通人民币购物。碰上这种情况,从事涉外工作的导游或陪同就有了换汇的机会。

换汇是把普通人民币变成外汇的过门。因拿人民币直接兑换成外币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先要换成外汇券。跟外宾相处一些时间搞好关系后就有这种机会,包括陪同外宾的作家。这种事在当时是个公开的秘密,但大家心照不宣,平日里从不当话题。现在这么回忆,是那截历史的如实写照。历史不容改头换面,而且不写下来就没了这段史实。
譬如陪外宾去普通餐厅用餐,七八人加导游及陪同一下子吃上好几百。相比当时的工资,这是一笔大额。付账时,导游拿普通人民币先替大家买单,之后,外宾再用同样数额的外汇券还给导游,如此,导游手里的普通人民币就变成了外汇券。虽然外汇券与普通人民币的官方价值是一比一,但市面上实际价值是一比二。也就是说,导游拿三百元人民币替外宾付完账,之后从外宾手里得回三百元外汇券,这样导游手里的实际价值就增加了一倍。相比月薪,一顿饭的功夫,导游获得了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
这种事官方当然不提倡,但氛围极宽松的八十年代是风靡全国。那一阵,举国上下朝钱看,也许是因为封闭了太久。这样做不但时尚,还很显能耐,也不会遭人唾弃、受到批判;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谁能发财谁英雄,谁人贫困谁狗熊。”国家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是得到普遍认可的社会风气及道德观念,似乎是中国人穷的时间太久了,是到了该发一发的时候了;为了钱,全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人争当全国首富“万元户”。当然,作家们也不例外。
走完了第一步,接着要拿外汇券再次换汇,换成外币,这时价值会有再次提升。当导游陪外宾去银行换钱,确认了兑换率,知道了外宾将会得到的外汇券数额后,外宾向导游换取外汇券。这样一来,导游手里的外汇券直接成了外汇,并且其价值具有更大跨幅。当时外汇稀罕,出国人员外汇不足,回国想买大件电器,就不得不私下购买外汇,而且还很抢手,没有门路还买不到,时常托人势在必行。
第二次换汇的价值提升幅度更为可观,因人名币成了可购买彩电的外币。此类近水楼台的实惠,只有职从外事的才有机会。是时的大气候,国家改开伊始,文革禁锢刚过,多有一种矫枉过正的势态,政策异常宽容、宽松,提倡“简政放权”,“猫论”鼓舞了人民,无论白道黑道,能捞到钱就是王道。单位领导也通融异常,第二职业盛行。虽然谁都三缄其口,但人人心知肚明,只是不挑明罢了。那是继文革后的第一段轻松的时光,是时颇流行的说法:这样做,虽不合法,但合情理!
当时私下弄到的外汇需要变成名正言顺,就是通过将钱带出境,再带回国。国家因外汇紧缺,所以外币出境管理相当严格。按当时规定,哪怕任何一个外汇出境都必须有中国银行总行的外汇携带证,否则就是违规。一旦被查到就有没收的危险,还处以严重的外事记过。出带外汇,大家巧用各自妙招,等回国时,白纸黑字地填进海关申报单。到这时,这些外汇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彩电了。有老作家事后打趣,私下携带外汇出境,把当年替八路军送鸡毛信的秘招都用上了。其实是时因形势宽松,海关实际上从不正经搜查。
随改革开放,国家领导人相继走出国门,看到了西方世界的发达,明白了自己落后的差距,感到愧对百姓。中国人过了多年的苦日子也该改变一下了,给人民在经济上更多的自由是最行之有效的政策,这或是对几十年来艰苦奋斗的百姓一次补偿。
此外,导游换外汇有个冠冕堂皇的托词,称其有可能出国,购物需要他国的货币,人民币在海外不流通,留住他们的货币作备用,这就合情合理了。外宾想到这钱最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对本国经济有好处,加上自己也没吃亏,还做了好人,何乐而不为?所以每到需要换币时,还会主动提醒导游。
我出国留学时的工资为93·50元,在当时算是中高薪阶层,但相比外事出差补贴,数额成了小巫见大巫。
外国作家团来访,为体现对外国作家的重视,在外事人员陪同去外地时,常常会配备一位作家随行。这样,作家除一路吃喝,住一流饭店,动辄公车出行,外联部有北京几大出租车公司的三联单,可随时随地叫车。
于陪同外宾的作家而言,实际好处是工资不减,食住行全包,加之,出差补贴就蔚然可观了。每天补贴费十元,想想大学毕业的普通干部,工资也就五十六元,单位发奖金都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如果作家随外宾团去地方三周,回京后的补贴就过两百,比起辛勤笔耕、爬格子挣稿费,一趟美差的收入既惬意又轻松。这也是作家们期盼参加外事活动的动机之一,不愧为增加收入的难得捷径。老诗人、时任《诗刊主编》的邹狄帆同志每次都会颇有感慨,他也是陪团最多的作家之一。
当时诸多外事规定即是如此。文革后百废待举,国家许多政策都是前所未有、是超验的,合理与否,只能执行一段时间后,根据实施效果再作调整。此类特权待遇到今天或会发人深省,但当时谁也不会往那里多想。中国百姓历来习惯了逆来顺受,且善于适应并认同现实。这也是改革初始流行的“摸石子过河”的方针。
总之,八十年代只要跟外事挂上了钩,保证穷不了。
五、 出国

相比出国,那时国内搞外事的好处则成了大为逊色。作家出国一趟一下子能买得起彩电了,否则,靠爬格子拿稿费,得披星戴月奋斗一辈子。于是,出国成了作家们致富最令人神往的弯道超车。
出国回来后可买免税家电,那是特殊待遇,可以不缴进口关税。国家之所以推出这种政策,目的是让外汇回笼,指望出国人员不要把钱花在国外。
八十年代作家团出访,我们每次都会带上一定的外汇作公款。一次碰巧财务处没有足够现金,而我们又出访在即,怕外汇到位来不及,于是我拿了作协介绍信去天安门广场边的中国银行总行提取。宽敞的大厅,高高的柜台,等着出纳员去金库取钱,我跟另一员工攀聊。我说,出国每人每天仅补贴一个美元,也是够少的。那女士马上说:“还嫌少?!国家现在的美元储存总额才二十六亿!”当时对这个数字我没有具体概念,而眼下听到的都是几万亿、几十万亿的数额,才知道当年的二十六亿确实少得可怜。
国家为尽快让外汇资金回笼,于是想出“出国人员服务部”这一妙招。通过易货贸易,从日本弄来大批彩电,给出国人员提供特惠价。通过不收进口关税,回国买电器既方便、又安全、而且更便宜!那又正赶上政策放宽、经济改型,提倡私有制,“万元户”成国人致富目标。于是,为更多来钱,钱来得更快,作家掷笔经商,自立门户、开公司,潜入市场做生意大行其道。然而,从投资到获利有个过程,经济收效最快捷的还是赶不上出国。出国无须投资,也无风险,而且还是一本万利!
那时短期出国,除每人每天一美元补贴外,还可以按平价兑换三十美元。当时国家官方牌价浮动在一美元兑三点五O元人民币上下,而私下交换能贵到十一到十二元人民币,还要看你有没有路子;在国外一天,国家发的每人一美元零花补贴也是势在必行,因为人到国外连上厕所也要钱,这在当时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天方夜谭,都让人笑掉大牙,我们无法想象外部世界。我初到德国时感触最深的是矿泉水比牛奶贵;种花的泥土要花钱买。
记忆尤新的是,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去的最频繁的是西德,我们虽跟奥地利、瑞士、东德等国都有文学交流协议,但互访的频率要少得多。我们跟联邦德国的交流在三个层面同时铺开,既有政府间每年不少于一次的对等互访,也有中国作协跟西德某联邦州的文学往来,因为德意志是个联邦国,各州在外交上享有国家级待遇,所以我们以国家层面与其某联邦州发生交往不违背外事对等;还有德方热衷中国文化的私人出资邀请。再加上零星不定期的文化、文学活动、中国文学周等等,汉堡几乎每年举办中国国庆文化活动,必定要请上中国作家代表团。而于我,往往前一个团人还在国外,下一个团的签证办理业已开始,所以须有两本护照。此外还有完成了第一个团的出访,干脆不回国,去第三国等待下一个团;要么两次出访任务合在一起,一次组团完成两个国家的访问。总之,怎么节省外汇怎么来。
我曾从东柏林搭乘奥地利汉学家施华滋的车前往维也纳,否则一张国际机票又要花掉上千马克,而且还是西德马克,当时国家又多么紧缺外汇!
一九八八年我们有其中的两个出访任务,先是访问民主德国,接着是访奥地利团,都是我的职责范围。为省去我来回的国际旅费,外联部就把两个团安排在前后,完成了访民德,我不回国,赶去维也纳迎接下一个访奥团。为省下飞维也纳的机票,搭施华滋的车前往。那时外汇不足是影响外事交流的最大障碍。
那年头,西德马克即使在西方国家的硬通货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甭说带回国更备受青睐,而且行情直线看好,兑换率日有涨幅。没忘记一九八五年我们到西柏林,要拿出三点五〇马克才能兑换一美元。很快,第二年涨到只需二点五〇马克就能兑换一美元。到了九十年代,尤其是海湾战争爆发,拿一点七〇马克就能换到一美元。设立欧元时的价值取向是按两马克兑一美元,本意是让欧元跟美元具有一比一的价值。
于是,当时西欧货币中马克最为抢手。荷兰的荷兰盾,法国的法郎,意大利的里拉,都远远比不上西德马克受人青睐。我们作家团到西德和荷兰的边境城市芬洛,在集市卖蔬果、花卉的农商听说我们是从西德过来,就会主动向我们收马克,在兑换率上还给优惠。
当时主宰国际金融的三大货币是美元、日元和西德马克。美元主导世界,日元统领亚洲,而整个西欧、北欧的货币对美元的兑换率,是随着西德马克对美元的比值变化而浮动,这就是说,英镑、法郎、里拉,包括全部北欧的货币与美元的兑换率要参照当日马克兑换美元的比值而定。这就是因为西德经济的强大。
作家们同样是一趟出国,但被派去哪个国家非常有讲究,能被派去西方国家还是被派去东欧国家诸如东德、捷克、南斯拉夫,会大不一样。出国的价值及经济效益和到访国的文化差异会迥然不同。虽然人人盼望出国,主要是为了免税彩电,而那年头有彩电,是高质量生活的象征。在有出国机会的前提下,大家更盼望能去西方国家。
不言而喻,首先是为了硬通货,东欧等国的货币拿回国无价值,就是当时的超级大国苏联的卢布也一样。我至今还有当时没花完的卢布、东德马克以及南斯拉夫的地那尔,以为日后会有机会故地重游,留着以后花。没想到,东、西德统一来得那么突然,一夜间东德马克成了历史文物。紧接着东欧的溃塌和苏联的解体,所有货币一夜间贬成一文不值。
出访到了西方国家,尽可能多地弄到外汇是每人念念不忘的心结,表面上从来不成话题,但谁都时时在盘算手里的外汇,以定夺回国买什么样的家电。于我而言,每次出访西欧国家,无形中也成了我为团里力争谋福利的目标。我会外语,了解国外行情,又频繁出国,那是一种责无旁贷。我们得事事、处处留意,争取外汇。若是出访东欧国家就免了操这份心。
出国后弄外汇的途径很多。
我们跟他国进行文学交流的原则是互访,即国际旅费自理,落地后一切费用均由对方招待。这种两国间对等承担经费对我国有很大的好处,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我们外汇短缺的困境,可以省去出访团在国外食住行的外汇开支。虽然当年哪怕是买中国民航的国际航班也必须是外汇,但不需要实体外汇,只是占用了外事经费的外汇额度,仅仅是国家机构间的外汇内部划账。等到外国团来访,落地后由我方招待,住西苑、北京饭店,去外地城市的车旅费、飞机票、住宿费都可以用人民币结算。而申请人民币外事经费要比申请外汇容易得多。
这样,我们到了西德,餐费由德方承担。通常,德国政府会给我们配备一名学汉语的陪同小姐,确实每次是小姐。我们无数次出访,陪同皆是小姐。看得出,欧洲人这方面的心理作业做得到位。西德小姐全程陪同,每顿饭由她付账,拿发票回去报销。在这一节点上就有了为大家谋取福利、赢得外汇的机会。
经团内大家商定,我们向陪同提出托词,借故去看望中国朋友,这对她会很无趣,我们可以自己行动,没有语言障碍,这样她可放假一天,午饭和晚饭由我们自理,餐费可以发给我们。陪同小姐会说,报销需要用餐的发票。
通常的餐标每人每顿二十五马克。当时国内大学生月薪,到德国换成马克还不够吃一顿像样的饭。是的,我们每走一步都在拿国内的收入标准作比较。忘不了一九八八年我留学初到慕尼黑,时遇入冬,一日,夜已至深,为省下两个马克的车费,地铁又不敢逃票,我们几个留学生,想想两个马克时值国内一个工人三天的工资,最后走路一个多小时回奥林匹克村学生宿舍。现在想来,当时的中国人真够贫困的。
但我们的餐费偶尔一两次还是可以超标的,过了三十,报销时就要说明,到了三十五马克只能偶尔发生。这样我们提出,希望每人一天得到六十五马克的餐费,声称要请朋友一起吃饭,餐标会高一些。这种从嘴边想方设法省出外汇,可以说是来外汇最便捷、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读者切莫觉得我们寒碜,这些可都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啊!
1986年中国作家团出访西德,路遥不慎被盗 300美金,事情弄得让人进退维谷,骑虎难下。我们绞尽脑汁仍想不出解决问题的绝招,最后只能在西柏林的两天全团吃方便面,省下餐费补贴路遥,才算解决了困境。
我们访问西德,行程一般在四个星期左右,整个旅程中,这种省餐费的事发生三、四次问题不大,当然要跟陪同搞好关系,获得她的配合。如此,大家不但有了一天自由闲逛的机会,主要是有了外汇积攒。而事实上,大家根本不舍得花掉任何一个马克下餐馆,那一顿可要吃掉一个月的工资啊!谁不心痛?算的还是官价,议价就更不得了。几年后我到德国留学,往国内打长途,路边的电话亭里,投进价值多于国内月薪的三十马克,通话没五分钟,投币箱里的钱已被全部吃光,说话语速迅疾得像发电报。
每当到了饭点儿,大家回旅馆吃方便面,反正早餐包在酒店,可以随意多吃火腿、香肠。除了第一次出国没经验,往下每次出国我都会带上满满一行李箱的方便面,以备急用。说来也巧,几乎每次都没白带,无论是路遥丢钱的那个团,还是出访东德时,天津老作家、作品 《白毛女》编剧作者杨润身因适应不了西餐,胃病闹得起不了床,每次的方便面都帮了大忙。
至于发票问题,就去中餐厅向跑堂要一张发票,把两顿餐费开在一起,声称那里餐不错,连吃两顿。完后给跑堂几马克小费作为回谢。那时德国还没有实行机打单体系,在盖了章的发票上写上几百马克很随意。可想而知,每人有三、四回六十五马克的机会,加起来可是一笔可观的财富,这会让每个作家无比激动和感动。一次王一地激动地说,没想到意外进帐这么多外汇,这次回国买家电要重新安排了!
此外,每次去西方国家,招待方谙悉中国国情,知道人民币到了国外不能用,每次出访,东道主会给我们数量不一的零花钱。这些钱是每个作家谁都不舍得花掉一分的。为节省投币,上厕所也要约好几人一起去,充分利用一次开门。
除从餐费上省下外汇,其他来源是媒体给的采访费。除八五年那个空前绝后的大团,其他访团给的零花钱,签收时均没提到版费。这意味版权仍在我们手里。但我们就是不好意思提钱,更不敢要稿费,让人感到羞耻,人到国外不了解行情更不敢了。
开始我们不领行情,但西方人思想意识不一样。你不主动要,人家不会主动给。那是我们不懂应有的权益。只要我们不啃声,对方不会主动提稿费;媒体跟我们版权交涉,跟邀请单位无关。
了解了行情,我们学会了“好意思”,旁敲侧击问及采访费。多次经验得知,给采访费本就毋庸质疑,关键是多少,这种尺度我们无法把握,由媒体根据预估的新闻价值而定。虽从没讨价还价,但有收获比没有强。加之我们是国家级访团,对方出手不至于太寒碜。
我们每次出国都会携带外事经费,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对公款拥有支配权,譬如请东道主喝杯咖啡,偶尔喝杯啤酒都属允许范围。西方人有给小费的习惯,中国人晓以入乡随俗,尤其生怕被别人看不起,有失国家脸面,每次的出访行前集训都会当作重要的外事内容加以强调。平时用餐喝咖啡,小费由东道主结账时一起给,但住旅店,为感谢清洁工,按常情每天在床头柜上要留下两、三个马克,而小费的放置,团里管钱的无法逐一进房间分派,于是小费包给团员自理。
每到一个城市,会根据住几天,事先一次性将小费发给大家,由自己处理。至于最后给了小费还是没给,或者给多给少是每个人的事,无法查证核实。中国文化人虽然喜欢外汇,但道德底线不会丢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明白小费事关重要,不会做害群之马,一定会给,但怎么给、给什么就另有讲究。
中国人从来有高明的变通手法。小费之事,人人心知肚明,从不当作话题。但同在一个团,朝夕相处好几周,时时交谈甚欢,不免漏点口风。其实拿马克当小费,谁都心痛,但表示感谢理所应当。于是大多人采用给礼品,而其效果还特别好。这些小礼品,国内又便宜,携带也方便,送给清洁工,新奇又值钱,可谓两全其美。一路小费积攒,又多出一笔意外之才。
六、 彩电

一个彩电是人生的奋斗目标。
现在四十不到的年轻一代或许很难想象,虽然时间只相隔了三十年,然而八十年代于中国人来说,家里能有一台彩色电视机是何等的事关重要!像张洁这样知名的作家当时对我说:“我写作一辈子就想买一个彩电,这是我搞创作的动力和目标,给我妈买的。” 且不说张洁对母亲的孝敬,可见短短的三十年前,中国人的人生追求又是何等的可怜,而我们亲身经历的那个时代就是如此。
碰上能出一趟国,好处实在说不尽,不光长了见识,看到了外部世界,而且得到的实惠非常之大,远超好几年的工资。最重要的是短期出国回来后,可以在出国人员服务部得到一大件、一小件的免税指标和一大件、一小件的上税指标,这些指标均具有不同的价值,尤其是大件的免税指标最值钱。
大件指标包括彩电、冰箱、照相机和大型组合音响设备等。是时,一般的老百姓家庭均还不具备这些家用电器,有个收录机就很神气了,而所谓的现代化生活,其象征首先是一个彩色电视机。众人期待的就是一个日本原装货。市面上较高档次的百货大楼,虽然也可以买到进口彩电,但无法保证是否原装,有可能是国内组装,而且价格上万,相当于那时的全国首富“万元户”,只有从出国人员服务部买的才能保证原装,才能显摆。
这里说的是临时出国不超三个月的,碰上出国半年以上的,免税指标还会增加。遇上在外两年以上的,就按长期出国算,回来免税八大件、八小件,待遇更不得了。
小件指标包括收录机、吸尘器、缝纫机、自行车等,当时买自行车还需要自行车票呢,而且很难搞到!但是,人人当时外汇有限,买一个 20吋的彩电需要 400美元以上,而出国人员官价兑换的美元额度及在海外每天的补贴都很有限,几乎谁都需要私下购买美元,而买私价美元,在当时是人尽皆知的普遍现象,没有谁会觉得奇怪。这样为了外汇,几乎掏空了所有的家底。所以上税指标一般都放弃。左邻右舍或单位同事之间关心的就是谁家新添了彩电。
一个彩电的正常税值在四千元以上,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四年的工资,税额每年还会随时调整。一个指标价值是多少,是根据购买时额外要缴的税款得出来的。
短期出访享受免税指标后,所谓免税指标就是买彩电时只需交电视机本身的价钱,进口关税可以免除。如果有人想买第二个彩电,可以利用第二个指标,即上税指标,正常缴纳进口关税。如果不想买第二个大件,这个上税指标就可以转让出去。一般的临时出国人员,都把仅有的积蓄变成了外汇,无力再交税买第二个大件。如果这个上税指标不利用起来,就会白白作废,但它本身有着价值,这并不是人人皆知。
改革开放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经济政策放宽,大批个体户出现,快速产生了第一批暴发户。这些人主要是做生意、开饭馆的个体户。这些个体企业,比起后来投资建厂的企业家见效要快得多,譬如西瓜摊老板,通过一个夏季没日没夜的辛苦劳作,可以挣到平常普通工人几年的工资。这一群族虽经济上发了财,但没有社会地位。不管他们再暴发,再有钱,但他们没资格在出国人员服务买彩电,他们也出不了国,免税商店跟他们无缘。然而他们可以出钱买下那个别人无钱交税、不被利用的第二个上税指标。大多人不了解行情,白白放弃纯属可惜。然而一旦有关系联络瓜摊老板,这合作可谓名副其实的相得益彰。
首先有了钱,瓜摊老板可以通过私下交易弄到美元; 有了美元,再找到不被利用的上税指标。一九八五、八六年价码在一千元左右,是当时一个大学生近两年、或普通工人近三年的收入。可想而知,出国一趟,就不算平价兑换美元,每天外汇零花补贴、访问时对方给的零花钱、所得版费、采访费等五花八门的进账外,光免税加上税两大件指标就价值在五千元以上,在此姑且不记免税、上税的小件。 所谓小件,可买电子琴、吸尘器等价值较低的进口产品。这些指标虽不那么起眼,但也拥有不菲价值,怎么也值几百元人名币,想想老百姓月薪在四十上下。
就这样,瓜摊老板用四百高价美元,外缴4000元人民币海关税,付给出国人员一千元好处费,如此就拥有一个质量保证的原装进口彩电。而那笔好处费又正是出国人员的额外收入。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国人谁都热衷出国的原因所在。一个作家往往苦苦拼搏二十年,不知爬多少格子,像路遥写得英年早逝。就是熬熬省省、不吃不喝的,抵不上别人一趟出国。这在当时是妇孺皆知的国情,所以出国热自然不言而喻了。
在海外得到的外汇,按最初规定,回国必须上交,但这项规定实际上没人执行,政策形同虚设。回国后人人三缄其口,领导也不过问。加之领导自己家里也缺彩电,自己出国回来,家人也指望着彩电,把外汇斡下亦是人之常情。最后大家都这么做,成了法不执众,规定成了一纸空文。尤其当时是国情一日三变,新政策、新规定不时出台,新老更替极快。
记得1985年第一次出访,行前还宣布了这一规定,但到了西柏林,组委会把版权费直接发到每人手里,签完字,这钱就成了私人财产。团里管财务的只字不提。团领导自然想着这条规定,钱带回国就得上交,不能违反国家政策。但领导有办法避开这条规定,做到没带钱回国,他在西德买了组合音响。国家不是规定带回外汇要上交,但没规定带回音响要上交吧?如此也避免了有可能犯的错误。团领导是资深作家,处理问题颇有水平,全体团员都认为这么处理非常得体,别人回国也不用上交外汇了!其实回到国内,再也没有谁问起那一千马克。
组合音响因为过大,检票时不让作随身行李带上飞机,尽管领导来时还被请进了头等舱,于是音响只好随机托运。但领导放心不下,觉得音响脆弱易损,一直介怀于心。
在法兰克福候机室里,我们碰巧看到窗外地上尚未装机的行李,其中就有音响。巧中之巧,我大学同窗正好在机场海关工作,于是让他从侧门把音响提回了候机室。上了飞机,机组人员又认出了团领导,冲着他的知名度,把他再次安排进头等舱,这样,组合音响也有了理想的着落。
2026年01月16日 德国慕尼黑
作者简介
金弢,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儒桥村,当过民办教师。1977级恢复高考进北外德语系,1981级北外德语读研。1985年元月进文化部,同年03月进中国作家协会,任职作协外联部。1988年中国作协恢复职称评定,获正翻译级。曾历次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张抗抗、从维熙、王安忆、北岛、舒婷等等作家并陪同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八十年代末获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者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长篇小说《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年编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由德国Spielberg出版社出版,并于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达三十五万字,504页,宽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为:陈染《空的窗》、陈建功《找乐》、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等;
2021年06月,于该出版社翻译出版东西长篇小说德文版《后悔录》;
2022年07月出版长篇小说《狂人辩词》(新译新版)【漓江出版社】,等等。
八十年代发表翻译及作品:【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长江文艺】、【钟山】、【百花洲】、【文艺报】、【中国妇女报】等,已发表20多位德语作家作品的译文;
来德三十六年,在德创业二十二年,文学创作及翻译辍笔三十年。五年前,金盆洗手,回归文学,写就新作及翻译两百万字。至今夙兴夜寐、孜孜笔耕;
近年,文字发表多家刊物:【北京文学】、【四川文学】、【花城】、【江南】、【收获】、【南方文学】、【青岛文学】、【香港文学】、【广西文学】、【三峡文学】、【延安文学】、【万松浦】等,并散见欧美及国内多家报刊:【欧洲新报】、【欧华导报】、【洛城小说报】、【华府新闻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人民日报海外版】等;
散文《话说张洁》2022年04月获“全国第二届散文大赛”一等奖;
散文《六秩同窗话三代》2022年10月获【文心奖】,“当代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
书评斯特林堡和他的《狂人辩词》2023年01月获【当代作家】杂志,“当代作家杯文学大赛”一等奖;
长篇小说《山道弯弯》2023年10月获第二届【中国知青作家杯】一等奖;
散文《读书改变命运》,「双争」有我,河北省第十五届“我的读书故事”、河北省作家协会征文优秀奖,2025年0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