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伙创业,始于梦想,终于陌路”,这或许是许多创业者不愿面对却又不得不正视的现实。当曾经并肩作战的伙伴因经营理念、利益分配等问题反目成仇,导致公司决策停滞不前、内部管理混乱时,公司便陷入了动弹不得的泥潭——我们称之为“公司僵局”。

那么,是不是一旦出现公司僵局,股东就可以向法院“告状”,要求强制解散公司,来一场“一拍两散”呢?答案并非如此简单。司法解散,被视为解决公司僵局的“终极武器”,法院在动用这一权力时,态度极为审慎。它并非股东之间闹矛盾、不想合作了就能轻易启动的程序。下面,我们将通过四个真实的案例,带您深入了解法院是如何裁判公司解散纠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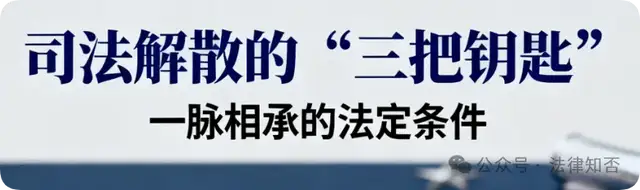
一、司法解散的“三把钥匙”:一脉相承的法定条件
在剖析案例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打开公司司法解散这扇沉重大门的,需要三把“钥匙”,缺一不可。无论是已被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八十二条,还是2024年7月1日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一条,其核心规定都保持了高度的延续性,即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这通常不是指公司资金短缺或业务亏损等经营性困难,而是指公司治理机制的“瘫痪”。核心在于公司的“大脑”——股东会或董事会等权力机构,是否已经长期无法正常运作,无法就公司的任何重大事项作出决策。

2、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这里的“股东利益”是指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而非个别股东的主观感受。它要求证明,公司的僵局状态若持续下去,将导致公司资产被不断内耗、商业机会流失,最终损害所有股东的投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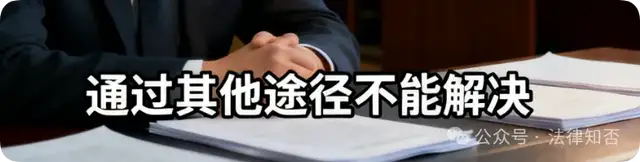
3、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这是司法解散的刚性前置条件,也是司法审慎介入公司自治的体现。在诉诸法院之前,股东必须证明已经穷尽了公司内部的自治救济手段(如协商、调解、股权转让、减资等),但均以失败告终。
只有当这三个条件同时被满足,形成一个无法自愈的“死结”时,法院才可能动用公权力,强制结束一家公司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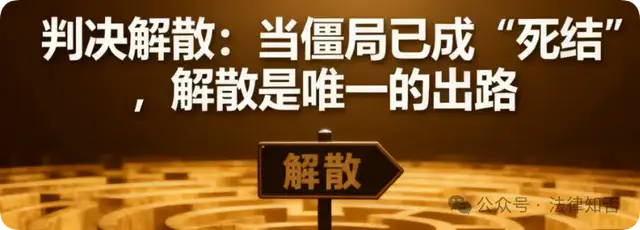
二、判决解散:当僵局已成“死结”,解散是唯一的出路
【参考案例1】:信任破裂,权力失灵——当“人合性”丧失导致公司彻底瘫痪
在“林某清与常熟市凯某实业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2010)苏商终字第0043号】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解散了一家陷入僵局的公司。
该公司仅有林某清和戴某明两位股东,各占50%股份。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且不包含本数,这意味着任何决议都必须两名股东一致同意。由于股东矛盾激化,公司自2006年起长达四年无法召开股东会,股东会机制彻底失灵。同时,监事(由林某清担任)无法对执行董事(由戴某明担任)进行有效监督,甚至连查阅公司财务的法定权利都被拒绝。
法院认为,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议事规则本身就极易导致僵局。股东间矛盾已使公司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全部失灵,公司治理陷入全面瘫痪。在这种情况下,股东的信任基础(即“人合性”)已完全丧失,继续维持公司只会让股东利益在无休止的内耗中受损,因此判决解散是打破僵局、保护各方利益的必要之举。
【案例启示】:当公司的股权结构(如50%对50%)和议事规则共同导致了“一票否决”的僵局,并且这种僵局已持续多年,导致整个公司治理结构完全失灵时,司法解散便成为最现实的选择。
【参考案例2】:貌合神离,管理混乱——股东僵局致公司经营停滞并持续亏损
在“鲁某、丽江某公司、田某公司解散纠纷案”【(2025)云07民终352号】中,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判决解散了一家公司。
该公司仅有鲁某(持股51%)和田某(持股49%)两名股东。双方矛盾尖锐,鲁某多次通知田某召开股东会,田某均不参加,导致无法形成任何有效决议。更为严重的是,公司自成立以来,股东均未实缴出资,没有任何营业收入,却因租赁经营场所而持续产生高额租金,导致公司不断亏损。
法院认为,公司股东之间长期冲突,无法通过协商解决,治理结构已然失灵。同时,公司在不产生任何收益的情况下持续亏损,继续存续必将进一步扩大损失,对全体股东造成实质性损害。在法院调解亦无果的情况下,解散公司是避免股东利益受到不可挽回损失的最佳途径。
【案例启示】:股东会机制失灵,若同时伴随着公司财务状况的持续恶化——即公司的存续不仅无法实现盈利的设立目的,反而成为不断“烧钱”的无底洞时,这就构成了判决解散的充分理由。及时止损,通过司法解散进行清算,对所有股东而言都是负责任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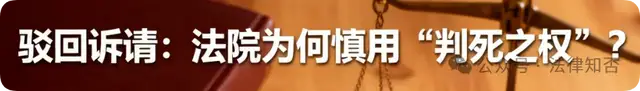
三、驳回诉请:法院为何慎用“判死之权”?
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公司解散诉讼被法院驳回。法院通常认为,只要公司尚有一线生机,就应鼓励股东通过自治方式解决问题,司法不应轻易干预。
【参考案例3】:矛盾虽有,但未到“绝路”——“两年僵局”是重要司法观察期
在“杜某、邬某涛与南昌市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2025)赣01民终2174号】中,持有公司合计60%股权的杜某和邬某涛请求解散公司,理由是大股东魏某独揽公司财务,侵害其知情权和分红权。
但法院审理后发现,该公司仍在正常经营并有收益入账。更关键的是,原告方虽然声称无法召开股东会,却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他们曾依法提议过召开股东会。直到一审判决后,他们才提议召集,显然不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中“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的僵局标准。
法院认为,股东权益受损,可以通过行使知情权、提起利润分配之诉等途径解决,并非只能通过解散公司。在还有其他救济方式可选,且公司仍在经营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判决解散。
【案例启示】:股东间存在矛盾是商业常态,但并非所有矛盾都足以成为解散公司的理由。法律设定“持续两年以上”的僵局状态作为重要考量因素,意在给予股东充分的时间去磨合与协商。在此期间,只要公司的内部沟通渠道未被完全切断,法院会倾向于让公司“再活一阵”,鼓励股东自我修复。
【参考案例4】:救济途径尚存,股东自治权利优先
在“张某、四川某公司、毛某公司解散纠纷案”【(2025)川14民终873号】中,持有公司35%股权的股东张某某请求解散公司,理由是其被大股东排挤,无法参与经营管理,股东权利丧失。
但法院指出,作为公司股东和监事,张某某依法享有诸多权利。例如,当执行董事不召集股东会时,监事有权召集和主持;如果其知情权、分红权受损,或发现董事、高管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完全可以提起相应的诉讼来维权。换言之,她有很多“武器”可以用来保护自己,而并非只有“解散公司”这颗“核弹”。
法院认为,在尚有其他法律途径可以解决股东争议、救济股东权利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已经满足“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条件,因此驳回了解散请求。
【案例启示】:司法解散是最后的救济,而非首选。股东在请求法院强制解散公司前,必须证明自己已经“山穷水尽”,用尽了公司内部和法律框架下的所有救济手段。如果股东“权利还在沉睡”,就不能以“走投无路”为由要求法院解散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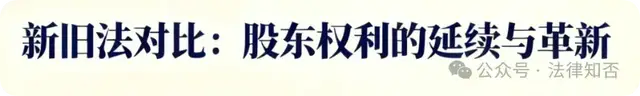
四、新旧法对比:股东权利的延续与革新
1、股东知情权的深化:从“看账本”到“查凭证”
●旧法(2018年修正)
赋予股东查阅、复制公司章程、决议、财务会计报告等文件的权利,以及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权利(第33条)。
●新法(2023年修订)
在旧法基础上,将股东的查阅权从“会计账簿”进一步延伸到了“会计凭证”(新法第57条)。这意味着股东不仅能看最终的账本,还能追根溯源,查看形成账目的原始单据和记账凭证。
在“孟某某王某某等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2025)苏03民终3014号】中,法院在旧法框架下,就基于查明案情的现实必要性,突破性地支持了股东查阅会计凭证的请求。新法则将这一宝贵的司法实践经验正式确立为法律条文,赋予了所有股东这项更具穿透力的监督权。这一变化使得股东能够更有效地发现并固定大股东或管理层滥用职权、侵占公司利益的证据,从而通过损害赔偿诉讼等方式维权,而不是只能诉诸解散。
2、股东退出机制的延续与创新
●异议股东股权回购请求权的延续与明确:
◆旧法(2018年修正):第七十四条已经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在特定情形下(包括“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异议股东有权请求公司回购其股权。
◆新法(2023年修订):新法继承并明确了这一重要制度。第八十九条(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和第一百六十一条(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对两种公司形式下的异议股东股权回购请求权作出了规定。因此,“连续五年盈利不分红可要求回购”并非新法的全新创造,而是对既有制度的延续和体系化完善,使其适用范围更清晰。
●更灵活的减资退出机制的创新:
◆旧法(2018年修正):对于减资,法律默认应按股东出资比例进行,缺乏灵活性。
◆新法(2023年修订):第二百二十四条明确允许“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另有约定”不按出资比例减资。这意味着,股东之间可以通过协商,达成一份“定向减资”协议,让某位股东通过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方式,合法、快捷地退出公司。这为股东和平“分手”提供了一个比解散清算更简便的全新工具。
总结:新法在司法解散的实体条件上与旧法一脉相承,但通过深化股东知情权、延续并明确股权回购权、创新减资退出机制,为股东提供了更多元、更有效的“事前”和“事中”救济手段。这也意味着,在请求法院动用解散这一“终极武器”之前,股东更有责任先穷尽自己手中已变得更丰富的“工具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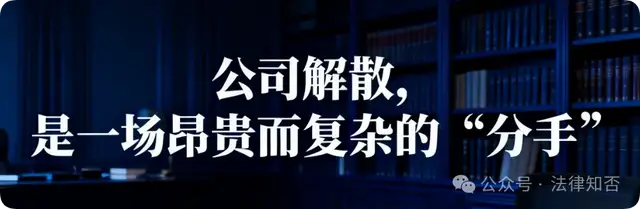
五、结语
公司解散,是一场昂贵而复杂的“分手”。它不仅终结了企业的生命,也往往伴随着漫长的清算程序和各方利益的博弈。法院对此持审慎态度,既是为了保护市场主体的稳定性,也是为了引导股东以更理性和成熟的方式解决商业纠纷。
对于广大创业者和公司股东而言,最重要的启示在于“防患于未然”。一份权责清晰、设计精良的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特别是其中关于决策机制、僵局处理和退出机制的条款,是公司平稳运行的“压舱石”。当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时,应首先寻求协商,并积极运用新《公司法》提供的多元化工具,通过股权转让、公司回购或减资等方式和平“分手”。毕竟,商业的本质是创造价值,而非在内耗中毁灭价值。
(免责声明:本文仅为基于法律规定及公开案例的个人解读和普法分享,不构成法律意见。由于个案情形千差万别,如遇具体法律问题,请咨询专业律师。)
【更多细节】请参阅原文
原文出自:微信公众号【法律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