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台上讲《强者》的那一刻,灯光打在脸上,嗓音软软的,像在聊天,她说,《卑微的人,贫穷的人,受伤害的人,受侮辱的人,他们依然可以强大,依然可以坚强,
是通过爱人,是通过创造,这些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台下很多人听着就红了眼眶,可如果你翻过她早年的《恶女书》和《只爱陌生人》,
再去听她说巴厘岛,说情欲,说那些失控的爱,又很难把这两个画面拼在一起,一个瘦小,说话细声细气的女作家,怎么会写出那样的恶女形象,

台湾女作家陈雪
又怎么会从夜市,债务,病痛里,一点点把自己写到今天,她叫陈雪,她说,如果没有小说,她大概就是个一辈子自卑,在噩梦里打转的夜市小贩的女儿。
《桥上的孩子》,从这里走出来的作家读过《桥上的孩子》的人,大多记得那条《复兴路》的小桥,十岁以前,她家其实日子普通但不算糟,爸爸是木匠,妈妈在工厂煮饭,乡下小镇,清苦一点,却安稳,
变故忽然就来了,为了翻身,父亲跟人合伙做生意,想从穷木匠熬成有钱人,结果被坑得很惨,债主上门,三合院被贴封条,
大人吵闹,爷爷奶奶责骂父亲,她只记得院子里乱糟糟的,父母低着头,很多细节都碎掉了,只剩下一个感觉,家没了。

接下来是很长一段夜市生活,父亲没法再安心当木匠,只能骑一辆电动三轮车,到镇上卖东西,前面是摩托车,后面拖个车斗,
白天装货,晚上摊子就搭在车斗上,他们在一条短短的小桥旁摆摊,桥叫《复兴路》,桥两头,摊贩挤得满满当当。
有人卖糖葫芦,有人卖棉花糖,卖卤猪脚,卖南北杂货,卖袜子鞋子,卖录音带,卖便宜女装,天一黑,灯一亮,叫卖声一片,整条桥像缩小版《清明上河图》,
陈雪小时候,就是那个推着录音带的小女孩,推车上堆满一卷卷录音带,高过她的头,她从桥这头推到那头,来回跑着帮父亲招呼客人。

妈妈平时内向,一到夜市就像换了个人,白天还病恹恹的,一站在摊子前,就像站在舞台上,说笑逗趣,手脚飞快,一边收钱一边找钱,还要盯着有没有人偷东西,
人多的时候,陈雪也得学着吆喝,拿着扩音器,对着人群叫卖,她说自己很怕羞,可嗓子喊哑了就得她顶上去,夜市不只是吵,还有危险。
她亲眼见过,有摊贩被人泼硫酸,搞到打官司,有人失明,毁容,父母怕出事,找过所谓保镖,
其实就是夜市里那些自认仗义的年轻人,一个舞双节棍,一个玩蝴蝶刀,附近风尘女不少,
她们来买便宜衣服,干完活也会脱了高跟鞋帮她妈卖货,陈雪后来回忆,说这些人都很有情有义。

以前台湾夜市场景(场景图)
但这种环境,对小孩的影响是实打实的,她穿着一条缎面红裙去学校活动,自觉美美的,同学却来一句,你怎么那么像酒店小姐,
她在教室里感冒,鼻涕直流,用袖子乱擦,袖子太脏,又拿衣角胡乱蹭,被全班笑成鼻涕虫,父母到处跑,到处躲债,有时候一两个月见不着人。
有一回,她去市场找爸爸,对上父亲的表情,那种好像突然想起来还有你这么个孩子的错愕,她记到现在,晚上收摊,父亲会把货铺平,
再把三个孩子像摆货一样排在车斗上,外面盖一层宝蓝色帆布,橡皮筋勒紧,里面一下子全黑了,车启动,哒哒地抖,一路开回家。
陈雪怕黑,弟弟妹妹很快就睡着了,她睡不着,只听见雨打在帆布上的声音,塑胶布窸窣地响,
她听见父亲的声音,在黑外面慢慢传进来,他说,现在到了卖卤肉饭的地方,这边是卖金鱼的,前面是拍卖古董的地方,要上坡了,要下坡了。

此照片为场景照
父亲的眼睛有一只受过伤,本来就看不清,夜路又湿又滑,他一边开着那辆没有避震的三轮车,一边报路,一边轮流喊着他们的名字,
很多年后,她在美国写稿时回想起那个晚上,才突然明白,当时父亲在做的那件事,其实是用一个笨办法让他们安心,
也是让自己撑着不睡着,她说,那时自己很怕黑,但在那个黑里,听着父亲的声音,就知道他们还没完。
写作,是她给自己挖出来的逃跑路线只看她后来在台上侃侃而谈,很难想象,她出第一本《恶女书》的时候,还在送货,大学毕业,她开始写短篇,得奖,写出了《恶女书》,
被贴上酷儿写作和恶女书写的标签,被邀请去美国做讲座,但现实是,她白天跟着司机在全台湾跑,给钟表商送像她手上戴的那种廉价手表。
家里堆满手表盒,滴滴答答的声音整夜响,她白天累到不行,晚上回出租屋,关上门,继续在深夜写小说,写作一开始,对她来说,就是逃,

著作《恶女书》
小时候在三合院,家门口被贴封条,她靠幻想来躲,幻想自己和妈妈是另外一户人家的孩子,幻想门外那群人不是来找他们家的。
长大一点,她还是在逃,一边谈恋爱,一边写大胆得惊人的小说,一边从一个关系逃到另一个关系,
从市场,逃进书桌旁,从现实里那个怕黑的小女孩,逃到纸上那些看上去无所畏惧的女主角,转折是1999年那趟美国。
她二十九岁,去加州那所大学做小讲座,顺便住两个月,朋友租的房子前面有花园,后面有小院,她住在中间那个卧室,带着一台小电脑,
对自己说,这次要专业写作,那两个月,是她第一次不用摆摊,不用送货,又可以不用管家里生意,只管写字。

写作思考的时候
刚开始她却什么都写不出来,每天坐在桌前发呆,脑子一片空白,后来有一天,一个画面突然闯进脑子,一个小女孩,在一座短短的桥上,
推着一车录音带,从这头推到那头,桥边是糖葫芦,棉花糖,卤猪脚,南北杂货,小玩具,叫卖声,人声,油烟,湿气,一齐涌出来。

吆喝声杂耍声此起彼伏
接着,是三合院里吵到天翻地覆的场景,封条贴在门上,大人骂父亲,接着,是被丢在乡下老家的几天,
冰箱空了,她去敲奶奶的门要米,学着自己炒鸡蛋煮汤,结果把锅烧穿,厨房熏黑一片,再接着,是那个带着弟弟妹妹去找妈妈的下午,
她拿着那封妈妈邮来的信,按着里面写的路线,一趟一趟转车,终于在城市的百货公司门口看见久违的母亲。
然后,是饭店的那间房,打麻将的阿姨叔叔,电视机前的三个小孩,还有那三位穿西装的男人,母亲塞给她几百块,叫他们下楼吃牛排,打电动,说一小时后会来接人,
他们吃完,玩完,等了很久,都没人来,弟弟都困得要睡着了,她心里第一次冒出被遗弃这三个字。
她结了账,带着弟弟妹妹坐电梯上楼,出了电梯才发现,她根本不知道房间号,电梯门开开合合,她只好带着两个小孩,在走廊里一间间贴着门板去听屋里的声音,

采访中回忆时的画面,释怀了
哪一间有麻将声,哪一间有笑闹声,哪一间可能是刚才的那一屋人,那一刻,她把所有的记忆和感官都调动起来,只为了在那栋陌生楼里,找到妈妈的房间,不被丢下。
等到门打开,三个男人从里面出来,妈妈和另一个阿姨站在门口,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喊她名字,让她们进来,他们又回到那个房间看电视,吃糖果,
旁边大人继续打牌,别人都当这只是插曲,她却在多年后才意识到,自己是多怕被遗弃,怕到连电梯门关上的声音,都记了一辈子。
在那两个月里,她就像坐在自己的人生电影院里,看这些画面一段段重新播放,她的手在键盘上停不下来,
飞快地打,把那些当年故意不去碰的碎片,全都记下来,那就是《桥上的孩子》的开头。

她从美国回台湾,继续送货,又熬了两年,才终于狠下心搬到台北,租了间十几坪的小房子,那时她几乎身无分文,
只是很固执地觉得,总得有一段时间,只做一件事,写,那十年,她写完了三本小说,《桥上的孩子》,《陈春天》,《附魔者》,有人叫它们家族史三部曲。
她一边在小说里努力理解父母的选择,也一边把自己,从那个自卑的小孩,慢慢拉向一个能平静讲出这些故事的大人,
那十年里,她经历了好几次精神崩溃,她写的不是酷的人物,而是那些她原本最想忘掉的场景,

场景图
市场,夜市,三轮车,黑道,债主,还有那个一直在还债,却总是翻不了身的父亲母亲,如果没有写,她自己说,可能永远走不出那种又恨,又怕,又羞耻的感觉。
《只爱陌生人》之后,她知道自己是个爱无能的人童年那块,她在小说里一遍遍写,慢慢能看得稍微清楚一点,可在感情这块,她原本是糊的,
她从小就一直在各种性的边上被卷进去,小学,隔壁有钱人家的大哥哥叫她去房间,手脚不安分,
公车上,总有人摸她的手,她的腿,国中差点被陌生人扯走,最后被一对夫妻救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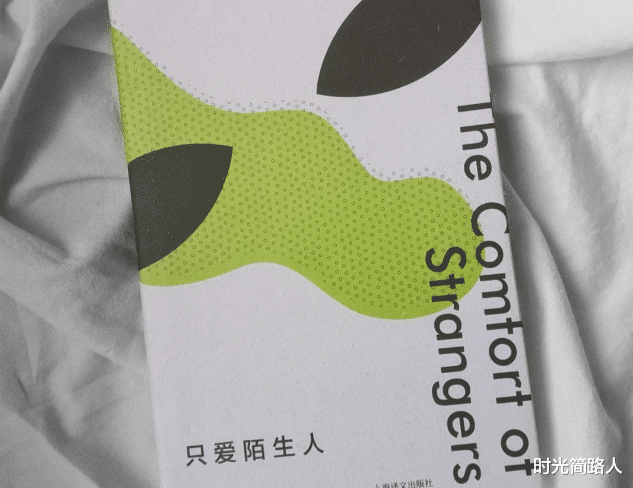
著作《只爱陌生人》
成年之后,她的爱情史同样密集,几乎没有空窗期,一段接一段,既渴望被爱,又老是想逃跑,
她常说自己有种解离,一旦发生特别严重或痛苦的事,她会抽离出来,看着那一切像看旁人的故事,毫无感觉,那次巴厘岛,是一个很明显的爆点。
她作为记者被派去写旅游稿,十四天的假期,她却把自己当成一个实验品,在巴厘岛,她吃下带点致幻性的蘑菇,跟海滩男孩,酒店打扫工,

日常生活场景
日本游客,连续卷进各种短暂的关系,像是要用尽所有极端的方式,把性这个东西拆开来看一遍,回来之后,她把这十四天写成一本书,《只爱陌生人》。
书一出,异性恋骂她不检点,同性恋骂她欺骗女同志情感,粉丝觉得她毁了自己建立起来的形象,
那时,她和最爱的那位女友一起生活,后来她在书里叫《早餐人》,坦白那趟旅程之后,两人就分开了。

陈雪和她的伴侣
陈雪后来回想,说那本书对她来说,更像一个爆破装置,它不一定是她最好的作品,但却炸开了她人生里几个被封得很死的地方,
她不再想维持一个完美女同志作家的形象,也不得不承认,在关系里,她其实一直是个爱无能的人,
她说,我想要爱,但在我找回自己之前,我只是个爱无能的人,这话像是在宣判过去的自己。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去一夜情的时候,都尽量不看对方的脸,她说,如果能不谈心,不分享秘密,只剩下身体,她反而比较放松,因为那样不需要负任何情感责任,
表面上,她的人生故事听上去刺激,绚烂,充满欲望,再往里看,她其实是个对爱极度失望的人,

李银和与陈雪
对男人,对女人,对自己,所以她一边用写作整理这堆情感废墟,一边往前活,直到身体先撑不住。
《迷宫中的恋人》和《强者》,她是怎么把自己拼回来的真正按下暂停键的,是病,大概四十岁前后,一阵阵像闪电一样的剧痛开始袭击她,有时整个躯干僵直,下半身动不了,像机器人,
有时反过来,腿废了,上半身还能勉强动,手拿不住筷子,只能用叉子吃饭,眼睛一再发炎。
有朋友看到她的状态,当场掉泪,说你怎么变成这样,对一个靠键盘,靠眼睛吃饭的小说家,这是最直接的威胁,
以前写童年,写家庭,写父母,再怎么痛,总还有一层时间的距离,这次是身体自己亮红灯,再不正视你是谁,你连写的机会都可能失去。
在这个节点,她写出了《迷宫中的恋人》,书里女主角鹿月,也是一个在病中回头看自己的人,

她回忆和小津,和阿撒的几段感情,才慢慢看清楚,自己一而再地用同一种方式把亲密关系推远,善妒,猜疑,逃跑,对方越想靠近,她越先逃走。
鹿月以为婚姻是归宿,却发现自己受不了丈夫去前女友的咖啡店上班,她曾经幻想的理想对象,多年后重逢,发现对方一方面极度包容她,一方面又严苛,不讲情面,
陈雪在这本书里,其实在做的,是对自己几十年逃跑行为的一次总检,她借着小说角色,对过去那个一再破坏关系的自己说,很多时候,你受的伤,是你自己先动了手。
这本书写完,她说自己人生的拼图,大概排好了大半,她也开始做一件以前没怎么做的事,不再只关在小说里想爱,而是去问人爱是怎么回事,
她去找大学导师聊,写《恋爱课》这样的问答书,把自己的困惑拿出来,让别人也一起讨论,慢慢地,她发现,原来世界上有很多连接人的方式,并不需要都靠性。
她会说,现在和朋友的关系,是以前想象不到的,她珍惜朋友之间的围炉,过年一起吃饭,切蛋糕,发红包,这些她小时候没经历过的东西,对她来说是新鲜的,她也学着和父母和解。

在三部曲之前,她心底对父母是有怨的,怨他们把家拖进债务,怨他们让她在夜市里长大,怨他们没给她一个安静的童年,
写着写着,她开始换一个角度看,八十年代的台湾,到处是想翻身的底层家庭,有人真的是撑不住,
就带着孩子一起跳楼,跳海,她的父母没那样做,而是像牲口一样,没日没夜地干,扛着那些看不到头的债。
她在书里写父亲开长途车时,自己甩自己耳光提神,所有人都睡着了,他一个人撑着,写母亲在饭店走廊喊她名字,写父母在桥上叫卖到深夜,
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今天熬完,画面写得越多,她越清楚,这些人当然有很多做得不对的地方,
但这些人,也是她现在还活着,还写得下去的原因,她常说,很感谢他们没带着孩子一起去自杀,也感谢他们给了她吃苦的能力。
债慢慢还清了,父母老了,还是在夜市摆摊,别人劝他们休息,他们说这是在做健康,
他们习惯了这样的日子,习惯靠自己的力气换钱,习惯在夜市灯光里站一整晚,陈雪看着,会觉得踏实。
她现在住在新北一条窄巷里的老公寓,对面是一栋半废的红砖楼,花草会开谢,鸟会停在电线上,

近期照,从容、有故事
她还是喜欢走进菜市场,在那堆戴着塑胶手套的手之间穿来穿去,闻鸡鸭鱼肉的味道,听人讲价,顺手买几样菜带回家,她说,她本来就属于市场。
只不过和小时候不一样,那时候,她是被车斗,被大人,被债务推着走的小孩,现在,她有一张自己的桌子,有一堆用自己名字出的书,
她可以用小说,把那些磨她,扭曲她,差点压垮她的经历,一笔一笔写出来,慢慢变成自己的底气。
她在《强者》那次演讲里说,真正的强者,不是冷漠,不是拒绝,不是把所有人都推开,装作什么都不在乎,

在《强者》中演讲的画面
真正的强者,是懂得去爱别人,是在知道生命有多厚,有多苦之后,还能继续往前走。
她说自己可能还没完全到那一步,还在路上,但她至少知道,从复兴路的小桥,到后来的摩天大楼,再到现在这条小巷,
这一路走过来,每一个要完了的时刻,都没有把她彻底打碎,小说,以及爱,让她还能站在台前,把这些故事讲出来,
也让更多跟她一样,从很低的地方走出来的人,看见,那些斑驳的记忆,不只是伤疤,也可能,是你身上独一无二的花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