俳谐者, 戏谑诙谐之谓也。以文字为游戏的俳谐式写作, 在以儒家观念为正统的传统文化语境中长期处于边缘性位置, 然而相关创作实于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 并在文、赋、诗、词等不同文体中逐渐演化出自身的传统。魏晋南北朝是俳谐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期, 宋代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个俳谐文学繁荣期,。笔者认为,对前代俳谐传统的吸收与化用能够成为后世作者改造语言形式、实验艺术创新的有效手段。
一、拟物为人,俳谐入诗本文所谓的俳谐写物传统具有特指性, 是指以南朝刘宋袁淑所作《诽谐文》为代表的一种类型化的游戏性拟人写物方式。简言之, 晋宋时期出现一种将动物戏仿为人的流行风气, 这既在当时的民间习俗中有所体现, 又为文人广泛用于游戏笔墨之中。

袁淑为其中的代表作者, 曾将自己所作这类文章结集后命名为《诽谐文》, 后世又有不少名称相近的续仿之作, 就此形成一种俳谐写物的文章传统。而就具体修辞而言, 拟物为人是这类文本所使用的共同手法, 也是制造俳谐效果的关键手段。

作者将鸡、驴、猪、修竹、甘蔗等动植物假拟为重要政治人物书写, 形成以庄叙谐的张力;同时又以谐音、双关、化用典故等文字上的暗示显露所写之“人”实为“物”的属性, 这些手法共同促成了文本整体上的“谐隐”艺术效果。
这一俳谐写物风气盛行于六朝, 却在漫长时段内一度沉寂, 直至中唐韩愈以《毛颖传》一文惊动文坛。修辞上, 韩愈将双关、谐音、以典故叙事等文字游戏手法使用到了极致。
如《毛颖传》中所写:“遂猎, 围毛氏之族, 拔其豪, 载颖而归, 献俘于章台宫, 聚其族而加束缚焉。”

表面是在叙述一场征伐之战, 然而围猎、拔毫、聚族、束缚、封诸管城等用词同时也是对捕兔、拔毛、束毛为笔、制作笔管等制笔过程的影射。文章的叙述即在人与物之间这一微妙的对应关系中展开, 保持着“言此及彼”“说东道西”的双层结构, 可谓俳谐写物的集大成之作。
《毛颖传》于唐代殊乏后响, 却在宋代受到了热烈追摹。据刘成国统计, 宋代共计有各类俳谐文一百五六十篇, 无论名家大手还是中小作者皆有问津, 南宋末年甚至出现了俳谐文的结集、唱和现象, 相关写作“颇有泛滥之势”。

这些文章大多以《毛颖传》为矩矱, 袭承假传体制, 并进一步扩展了俳谐写物的对象范围, 俳谐写物遂在宋代成为一种普遍化, 乃至趋于程式化的写物方式。在此风气影响下, 拟物为人的俳谐手法亦为宋人援引、吸纳进入了诗歌领域。拟人本是一种常见的诗歌艺术,然而俳谐式拟人因其沿袭了俳谐文的写作传统与文体特征而异于一般性拟人。
二、宋诗俳谐,文本趣味宋诗对俳谐写物的接受, 是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之书写爱好的体现。在俳谐式拟人写物修辞的影响下, 宋诗呈现出异于前代的艺术形态, 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诗歌文本趣味的强化。具体而言, 这一效果是通过以拟名称物的方式构词属对、“假物为人”“将虚坐实”的“假传”式叙事、通过使典形成文本的多义与互文效果等不同方式实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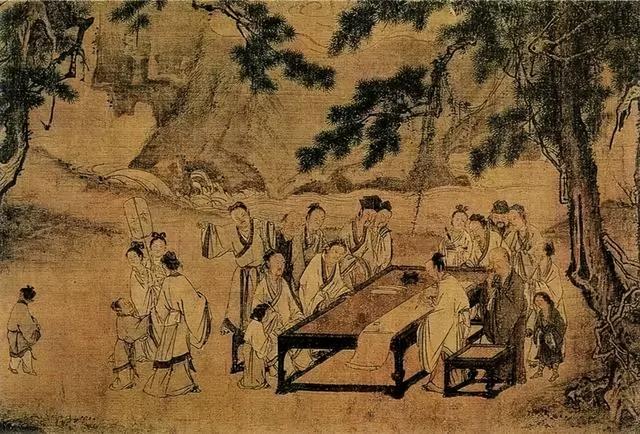
宋诗对俳谐写物传统的接受, 首先体现为以人类姓名、字号、官爵、身份称物的书写倾向。前文提及, “拟名”手法是俳谐写物的重要特征, 这是“以物为人”整体修辞结构能够成立的基础, 也是整个文本游戏趣味的直接提示。在《毛颖传》的影响下, 宋人诗中提及“笔墨纸砚”文房四友时常好冠以各类俳谐式的官职或人名。
如晁冲之《王敦素许纸不至戏简促之》“摩娑垢面戏陶泓, 拂拭苍髯笑管城。已与陈玄俱绝倒, 从君更召楮先生”。

其间便直接袭用《毛颖传》中称谓而成。陶泓故意用手抚面、弄脏脸, 引得管城抚须而笑, 陈玄亦大乐而不能自持。诗人将磨砚、蘸笔、倒墨以待纸的场景表述为邀请纸参与一场游戏, 借助俳谐拟人称谓点活整个诗境。
除此之外, 宋人诗中还有诸多发明。如以“黑头公”称笔“逢时尤作黑头公”更为巧妙的是, 毛笔笔管材质不同, 其名称亦各异。如芦管笔曾被诗人封为“卢国公”“翰林夜召陶学士, 草制进封卢国公” 。这些称谓或模拟物之形态、或戏用历史文本中的人名、或取同音双关, 手法不一, 取法《毛颖传》的俳谐旨趣却近似。

上述称谓不少见载于俳谐文、笔记、史籍等文本, 或流行于民间口语, 有一部分则为诗人自己的发明, 来源非常驳杂。然而即便早有记载, 这些词语频繁出现在诗中, 甚而凝化为固定的诗歌意象, 却是于宋代才显著的现象。
这一修辞意识的来源, 除了使典炫才、代指称物的意图外, 俳谐趣味的推动作用亦不可忽视。也正因此, 在苏轼、杨万里等以好戏谑、善诙谐著称的诗人笔下, 这类拟名称物现象尤为多见, 且不少并无前典可寻, 纯为诗人想象力的创造。

如苏轼曾寄语文与可此君庵前的竹子:“寄语庵前抱节君, 与君到处合相亲”。
苏轼称竹为“抱节君”, 既有“抱持节操之君子”之意, 又与竹节节相抱的形态相契, 还与文与可称其所画墨竹为“墨君”呼应, 颇为自然巧妙。苏轼还曾称笋为“玉版长老” , 笋与佛教本无联系, “长老”之称乃因诗歌所赠友人喜于谈禅, 是基于具体语境的个人化想象。
 诗人情志,抒情寄托
诗人情志,抒情寄托宋诗中的俳谐式拟人写物虽然延承了前代俳谐文的写作趣味与相关修辞, 然而诗、文到底分属异体, 俳谐传统并非仅在二者之间简单、机械地传递。宋诗中物的俳谐式拟人称谓并非仅仅来源于俳谐文, 而是利用了佛典、俗语等更为广泛的语言资源———俳谐写物并非由文至诗的单线演进。
此外, 前文也已提到两种文体在叙事容量、使典方式等方面的不同。除此之外, 诗、文写作的最大差异在于诗歌较文而言具有更强的抒情性。俳谐文所仿拟的公文体与列传体皆要求作者以与写作对象保持距离的第三人称进行客观化叙事, 文本空间中并无写作者个人的抒情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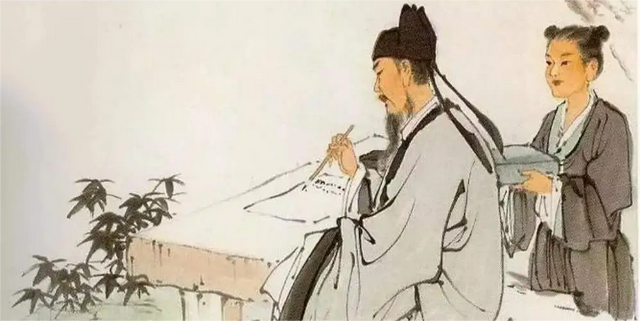
故钱锺书在《谈艺录》中称“《毛颖传》词旨虽巧, 情事不足动人。俳谐之作而已” 。
而诗歌写作以言志、抒情为其传统, 具有弥补这一情事之缺的文体优势。因此, 俳谐传统之入诗, 势必将与诗歌的抒情传统相融合, 其趣味亦会发生转化, 进而呈现出新的内涵。

首先, 物的人格化观照被用以呈现诗人与外物之间的亲密情感。在俳谐式拟人的眼光下, 日常物象俨然诗人生活中的亲密伴侣。物的实用功能淡去, 它们对诗人而言的情感意义则被强化。俳谐式拟人修辞得以显露宋人与物之间的共情关系, 是诗人移情于物的体现。
其次, 宋诗俳谐式拟人修辞的发达亦受儒家“君子比德”传统的影响, 在物的人格化形象中可见士大夫道德理想与人格精神之投射。俳谐写作好将物比以官员、士子等形象, 这一修辞本出于戏仿人类世界之意图, 但宋代诗人却在物的人格化形象上寄托了士人严肃的道德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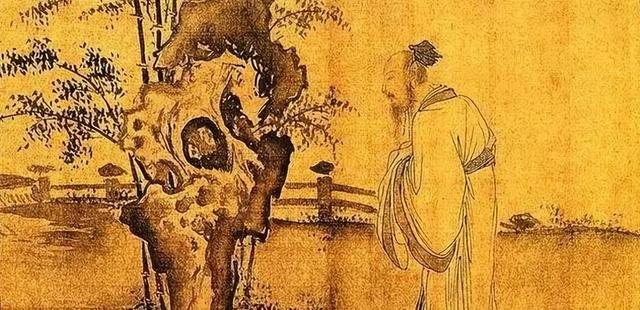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 对物的亲近与尊重态度显露出诗人对特定价值的选择与皈依之志。在以俳谐式拟人手法写物时, 宋人常将自我与外物间的关系表述为一种类似君子间的“知交”之谊, 诗中常常出现“论交”“相从”“知”“盟”等词汇。交谊观念描述人与物之间的情谊, 意味着诗人对物所象征的特定之“道”的认同, 即对某种人生道路或价值观念的选择与认定。
最后, 对物的俳谐式拟人书写还可于象征层面呈现诗人的人生处境与个体命运。俳谐文虽在形式上具有显著的游戏感, 然其人与物相互参照的文本结构蕴含了以物情喻人事的象征潜能。

事实上, “讽喻”功能一直受到传统文论家的重视。而在进入诗歌领域之后, 俳谐修辞的这一隐喻潜能便从泛化地隐射现实转而成为对诗人个体真实生存处境的指涉。

如黄庭坚《戏呈孔毅父》一诗,, 以俳谐式拟人称谓指代物, 构词奇绝、想象新妙。然而诗句的意义亦深刻:“‘管城子’既然为‘子’, 就不妨有食肉封侯之相;‘孔方兄’既然为‘兄’, 就不妨可以写绝交书。
不过, 应当封侯者却无食肉相, 应当亲爱者却给自己写了绝交书, 可见命运之乖蹇。”事物之“名实不符”带来句意颇具张力性的转折, 蕴含着诗人对“文章功用不经世”这一无奈现实的感喟。
频频出现于上述诗作题目中的“戏”, 皆有戏语言志的意味, 所指并非真正欢快的戏谑, 而是不乏苦涩感的自嘲。俳谐修辞使得诗人表情言志的手段更为曲折隐晦, 句意因而更显深沉, 留人以回味的余地。
 结语
结语俳谐修辞之入诗, 密切相关于“破体为诗”“化俗为雅”“以文字、才学为诗”等宋代诗学的经典命题, 构成了宋诗区别于前代的风格特征之一。宋诗中的俳谐式拟人写物也是俳谐传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经由宋诗“中转”, 物的俳谐式拟人称谓在宋词中亦频频可见, 更成为明清诗作中的常见意象。笔者认为,宋人对俳谐传统的接受与转化体现了宋代文化对谐与正、传统与新变、世俗与崇高的平衡, 从中可见时代精神之痕迹。
参考文献《宋史》
《全宋诗》
《毛颖传》
《谈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