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熙中先生是著名的《红楼梦》版本学语言学专家,他的《红楼求真录》[1]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著作,也是红学真功夫的代表。这本页码并不算多却十分厚重的书,使人对红学前辈油然生敬畏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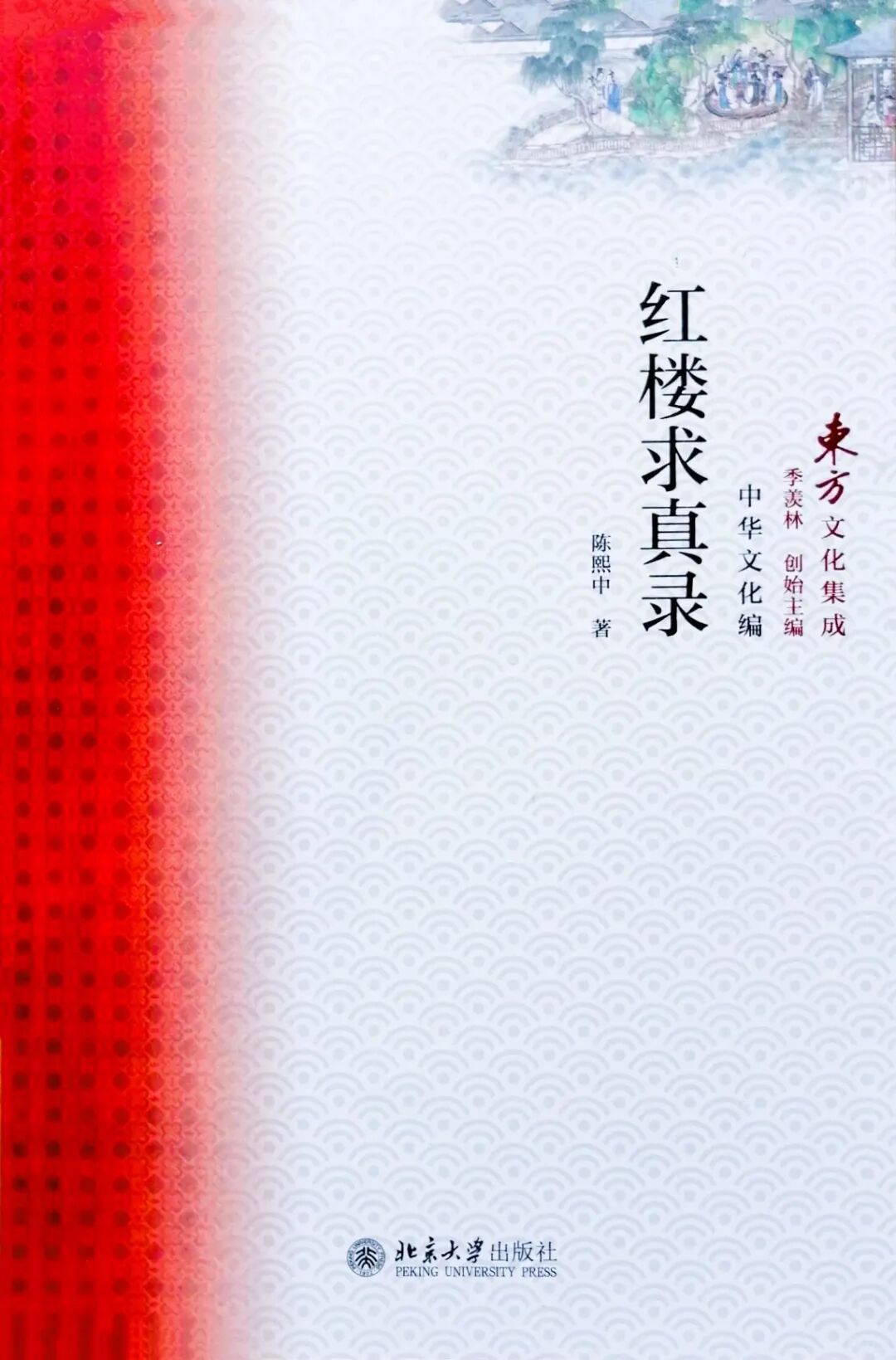
《红楼求真录》
吕启祥先生以《见微知著,言必有中》为题代序赞其“既有纵深,又能辐射,更可触类旁通,给予人的知识、趣味以至于智慧,就关涉到学问之大者了。”可谓一语中的。
即使语言研究之外的问题,也同样体现这种学术特色,能给人以“学问之大”的深刻启悟。《红楼梦》人物年龄问题就是一例。
一

陈老并未进行小说人物年龄的专门研究,书中仅有一篇《从贾宝玉的年龄说起》的短文(248-250页,以下简称“陈文”),大约写作于四十多年前。
其时,有学者以贾宝玉年龄“前后不一,忽大忽小”等为论据,对曹雪芹的著作权提出质疑。陈老坚决维护曹雪芹著作权,但并未参与贾宝玉年龄问题的讨论,而是别开生面地提出一个见解:
“人物年龄前后发生矛盾,这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中是常见的现象,而并非《红楼梦》所特有。”
这句话,有如当头棒喝。四十多年过去,笔者觉得,对于过分沉迷于贾宝玉年龄之类问题的红楼梦中人,也还是一剂清醒剂。他告诉人们,这只是个“应该引起作者们(按:并非读者)的注意的”“美中不足”的“小问题”。
为此,他从当时流行的《创业史》《红旗谱》开始,再及鲁迅《故乡》、屠格涅夫《父与子》、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直到《金瓶梅》等古今中外名著举例,并分析导致出现小说人物年龄问题的原因:有的属于作者偶然的疏忽或笔误,比较复杂而常见的则是故事发展中历史年代与人物年龄不一致,作者顾此失彼而致,而有的甚至是作家的特殊文学处理。
陈文的论述虽然简短,却很有启发性。
第一,他指出小说创作中人物年龄问题的某种常见性或普遍性,因而人们应以平常心看待。这就有助于消解读者对这一问题的不恰当关注甚至有意炒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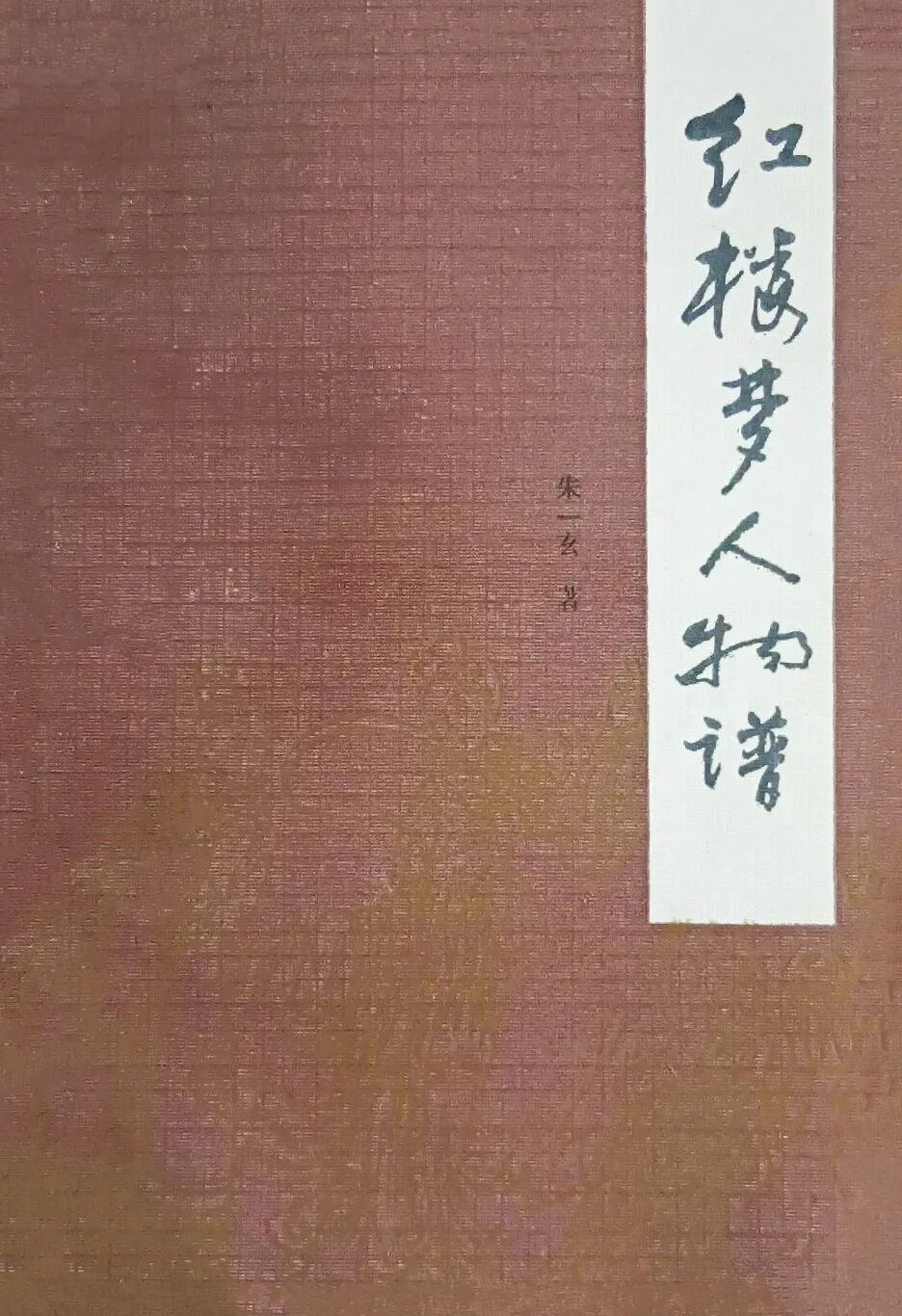
《红楼梦人物谱》
第二,他指出了产生这一问题的复杂原因,不能简单化对待,特别强调除了写作的失误等消极因素,也还有作者创作的积极因素,因而应该注重文学考察。而后者,正是习惯于现实生活逻辑的读者和研究者们所忽视的。
总之,平常心态和注重文学考察,这就是陈文对小说人物年龄问题的回答。题为《从贾宝玉的年龄说起》,却离开本题,引申论述对待小说人物年龄问题的基本观点,这与沉溺于本题的狭隘研讨大异其趣,显示了论者的独到眼光。这就是吕启祥序所谓“学问之大”的功夫吧。
值得注意的是,陈文谈到《金瓶梅》的人物年龄矛盾时,特别引出了张竹坡的为之辩护的观点:“此皆为作者故为参差之处”。

齐鲁书社版《张竹坡批评金瓶梅》
张竹坡的话见于《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现将这一段全文引述如下:
《史记》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时日也。开口云西门二十七岁,吴神仙相面则二十九,至临死则三十三岁,而官哥则生于政和四年丙申,卒于政和五年丁酉。夫西门庆二十九岁生子,则丙申年,至三十三岁,该云庚子,而西门乃卒于戊戌。夫李瓶儿该云卒于政和五年,乃云七年。此皆作者故为参差之处。何则?
此书独与他小说不同,看其三四年间,却是一日一时推着数去,无论春秋冷热,即某人生日,某人某日来请酒,某月某日请某人,某日是某节令,齐齐整整捱去。若再将三五年间甲子次序,排得一丝不乱,是真个与西门计账簿,有如世之无目者所云者也。故特特错乱其年谱,大约三五年间,其繁华如此。则内云某日某节,皆历历生动,不是死板一串铃,可以排头数去。而偏又能使看者五色眯目,真有如捱着一日日过去也。此为神妙之笔。噫!技至此亦化矣哉!真千古至文,吾不敢以小说目之也。[2]
陈老并不赞成张竹坡对作品的瑕疵“曲为之辨”的做法,但他显然看出了张竹坡的“与众不同”,并特别引用了这段话的后半部分让人体味。张竹坡确是一位很有眼光的文艺评论家。
他肯定“《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即承认它对史传文学纪实传统的继承,但却又把《史记》与《金瓶》并提并比较,特别强调作者有意打破纪实叙时的规范,“故为参差之处”,“特特错乱其年谱”,“使看者五色眯目”的“神妙之笔”,这使它不但不同于史书年谱账簿,也超越当时的一般“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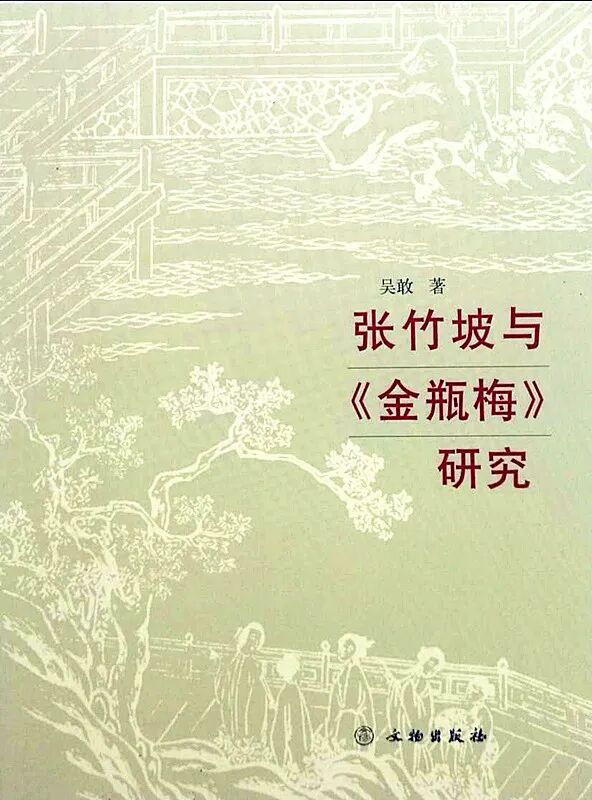
《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
在这里,张竹坡显然抓住了小说虚构的艺术本质。也就是说,即使是写实小说,作者也有必要通过有意“参差”“错乱”叙时的手法,使作品拉开与现实生活的的距离,制造“陌生化”的艺术效果,这才是“使看者五色眯目”的“神妙之笔”,这才是《金瓶梅》不同于《史记》成为”千古至文“的原因。
二

以贾宝玉年龄为代表的《红楼梦》的人物年龄问题,虽然并未影响《红楼梦》的阅读、传播和美誉,但一些学人关注已久,且多从小说增删过程和传抄过程的失误来研讨原因,有的甚至视为“致命性痼疾”,认为“现存文本的人物年龄矛盾,可能就是曹雪芹生前未能完全解决的难题”。这种认识显然有其片面性。
笔者一段时间以来对此有所关注和思考,读了陈文关于平常心态和注重文学考察的论述,觉得很受启发。更加认识到,注重文学考察,正是纠正认识片面性的有效药方,也是解开《红楼梦》人物年龄问题之谜的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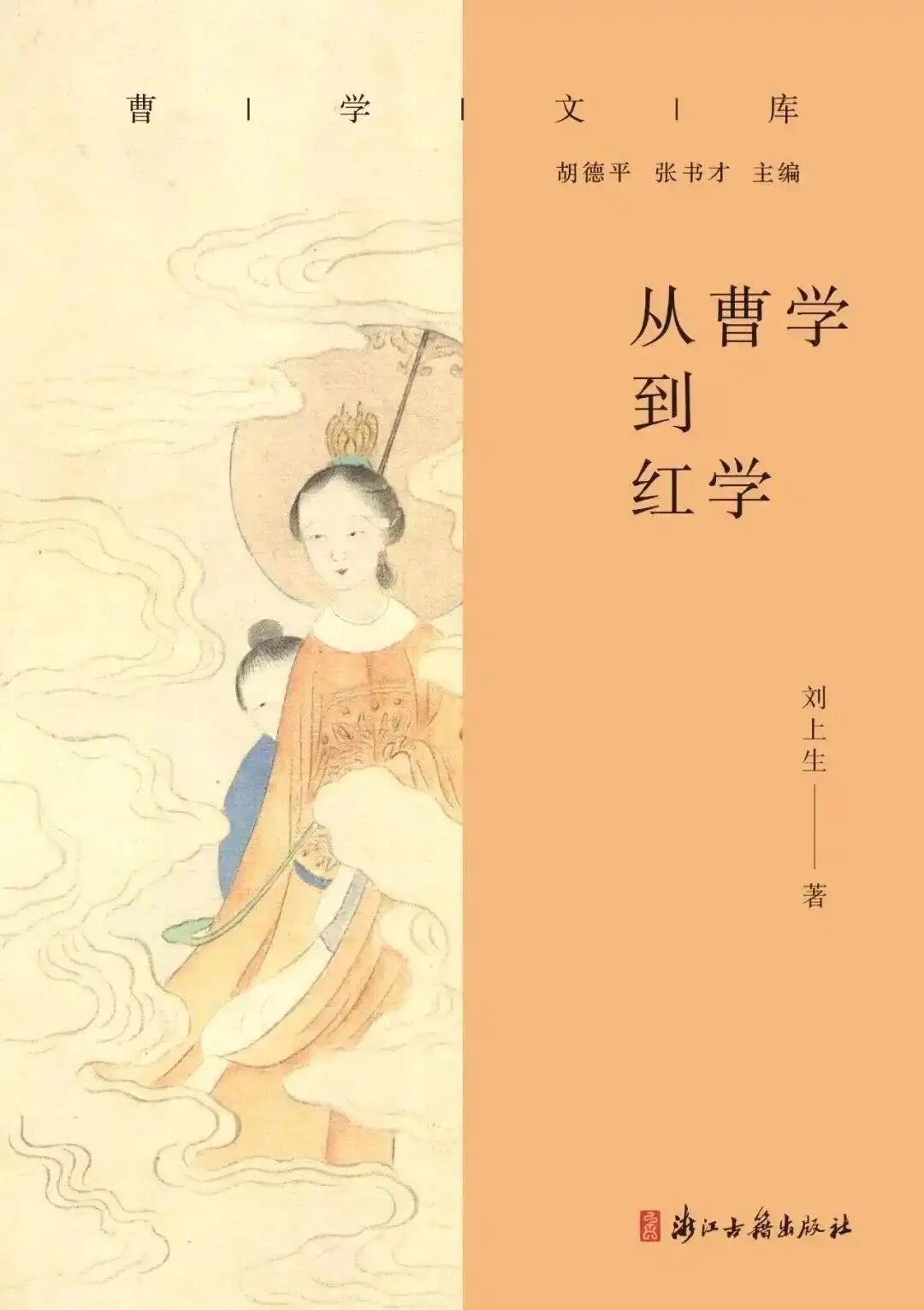
《从曹学到红学》,刘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这种文学考察,包括小说的特殊构思和写作手法,特别是作者在“大时间观”下追求的“新奇别致”的叙时艺术研究等。它使人们认识到,在被脂批称为“深得金瓶壶奥”的《红楼梦》里,张竹坡评论《金瓶梅》多少有所夸张的“故为参差之处”,“特特错乱其年谱”,“使看者五色眯目”的“神妙之笔”,在曹雪芹笔下,才真正焕发了奇光异彩。
《金瓶梅》是一部借宋时写明事的写实小说。学者梳理出它从宋徽宗政和二年开始到靖康二年结束,历时十六年,呈现“编年体”叙事的时间线。
然而《红楼梦》一开始,作者就用“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之语宣示了小说的文学虚构性质和基本写法,用石头下凡和木石情缘两个神话,奠定了主人公和主题情节的浪漫主义基调,并且以“无朝代年纪可考”表明了对史传叙时传统的无视和突破。
中国古代小说源于史传传统,长篇说部被称为“稗官野史”。时间叙事的精确性是“信史”的基本特征。如果《红楼梦》是一部纯粹的写实小说,那么,包括时间(年龄)叙事的生活逻辑的“事体情理”便是唯一的考察维度。
但《红楼梦》创作方法并非如此简单。在曹雪芹的笔下,写实、神幻、隐喻种种融为一体。作者特别宣称:
“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位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
可见,曹雪芹是把“不拘拘于朝代年纪”即非精确叙时作为自己创作“新奇别致”的“假语村言”的重要标志。小说是虚构的叙事性文学作品,时间包括人物年龄只是叙事的线索,而因果(因缘)即“事体情理”才是故事的本质。“不拘拘于朝代年纪”的非精确叙时,正是为了突出“事体情理”的本质艺术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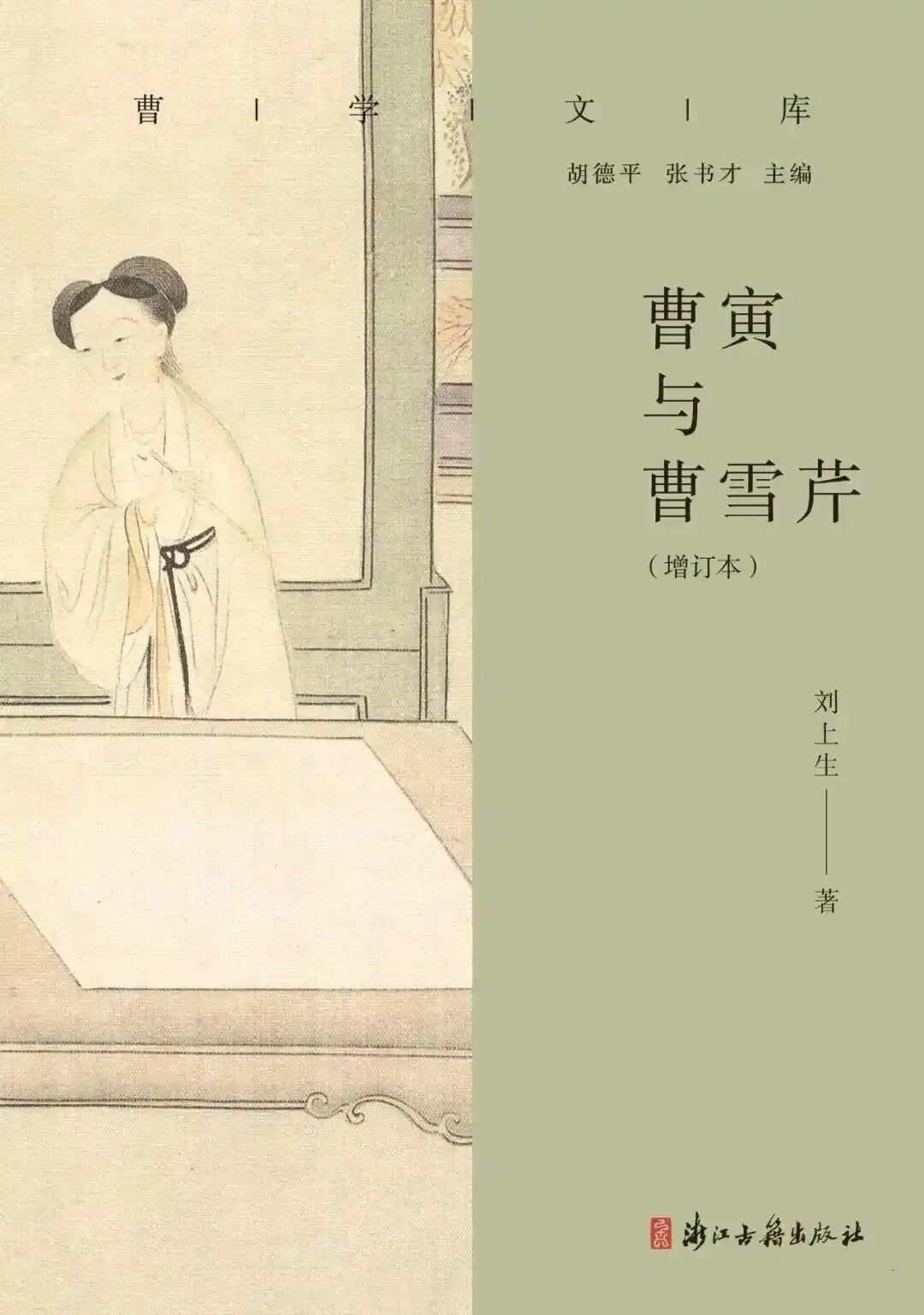
《曹寅与曹雪芹》(增订本),刘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过去,人们只从作家的“自我保护”策略理解这些话,实际上,它乃是作家创作的“大时间观”宣言。即从宏观上把握历史人生,而不执著于微观叙时的精确。
“年纪”一词在《红楼梦》中多次表示人物年龄,如第四十九回“叙起年庚,除李纨年纪最长”,又同回贾母说:“这是我们有年纪的人的菜”等等。所谓“无朝代年纪可考”,乃是曹雪芹“大时间观”下的叙时策略,大而言之,王朝世代:小而言之,人物年龄,都是具体物质的时间存在。
“大时间观”超越这些具体视点,小说石头下凡历劫回归记事的构思,和借助于佛家语言的劫运及“空-色-情”哲理思悟,使作家能够站在超越性的认识顶点俯视过往时间。所谓“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就包含对具体而微的时间的有意模糊和忽视,而凸显描写对象的概括性与典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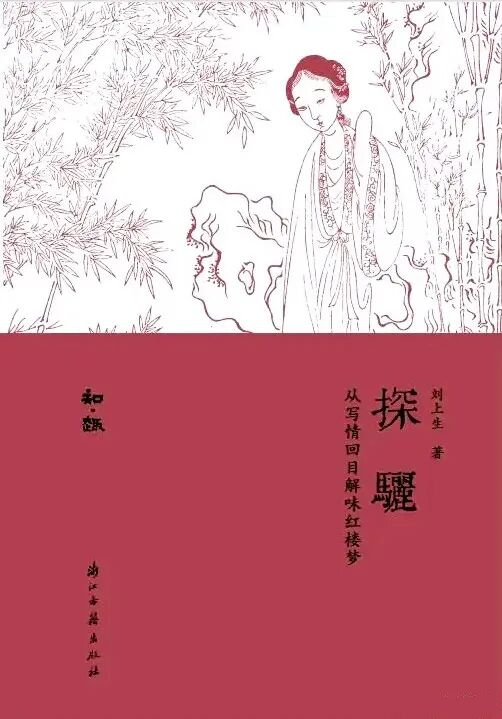
《探骊:从写情回目解味红楼梦》,刘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版。
从历史看,《红楼梦》着眼于盛衰记忆和变易规律,这就是它并不执着于一己家世和当朝政治,所叙贾府和四大家族”无朝代“可考的原因:从人生看,则着眼于年少青春记忆和情感理想,这就是它并不注重宝黛钗及十二钗诸册女子年龄精确性甚至不惜保留种种矛盾的原因。
过去,人们总是单纯从创作过程即所谓“增删五次”解释小说人物年龄的错乱,这的确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也许只是一种消极的理解。曹雪芹的“大时间观”,正是面对修改过程的矛盾而产生的认识飞跃。
“不拘拘于朝代年纪”的非精确叙时,正是他采取的写作策略。作者在第一回反复强调这一点,又是一种阅读导引。告知读者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人物性格、情节走向、艺术创造及其背后隐含的深刻寓意,而不要舍大就小,舍本逐末。而纠结于某些人物年龄矛盾细节,正是背离这种导引而走入了认识误区。[3]
三

经过《红楼梦》二百余年接受史的检验,程高本和现今通行混合本(红研所校注本)已经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所接受并作出了巨大贡献。
笔者认为,作为经典文本的历史形态,它们应该得到守护[4],但并不因此反对一切对小说文本的“修订”。由于后四十回并非曹雪芹原著,并与前八十回存在差距和矛盾,有红楼梦中人企图通过自己的修订,实现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较好融合,不管结果如何,这种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红楼梦》
然而,如果企图通过“修订”包括曹雪芹前八十回的文本,来解决所谓《红楼梦》的人物年龄问题,则是不可取的。因为从小说“假语村言”的虚构性质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伪问题,是一个属于作家文学创作范畴的问题,是他人不可能代庖而只能进行文学考察(以及文字考察校勘)的问题。
作为红楼梦中人,应该努力读懂《红楼梦》,走近曹雪芹。有学者指出,现在我们懂得的,比还没有弄懂的少很多。诚哉是言。有此自知之明,才能知道应该做什么,做多少,不能够做什么。
贾宝玉的年龄问题,是《红楼梦》人物年龄问题的核心。事实上,人们议论的所谓贾宝玉年龄“问题”,都是以现实逻辑和写实情理为标尺衡量的结果,根本没有考虑曹雪芹的艺术构思和设置。
贾宝玉的衔玉而生,使他成为艺术形象的“古今未有之人”,“通灵宝玉”前身“情根石”寓意的“行为偏僻性乖张”的叛逆本质,“木石前盟”的前世情缘和命定悲剧色彩,所有这些,都启示读者必须转换单一的写实视角和评价标准。逆反“男尊女卑”的“泥水骨肉说”,当然不是七八岁孩子的思维水平和能力所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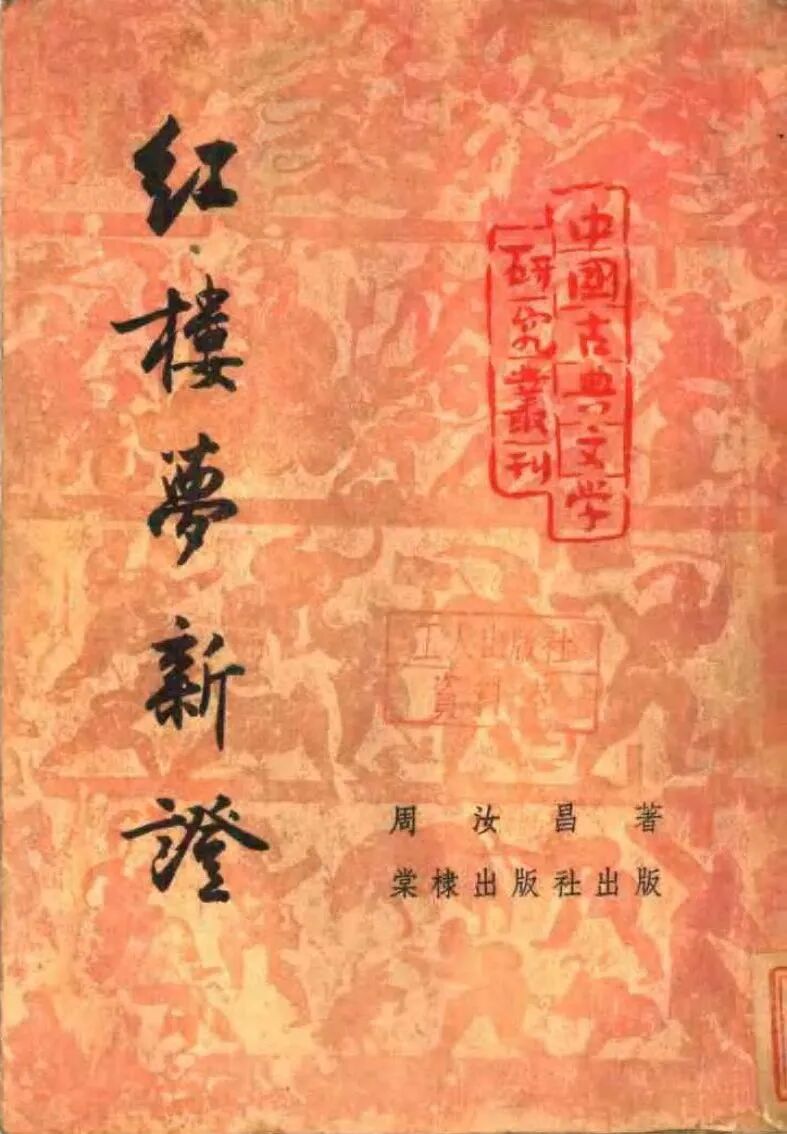
棠棣出版社版《红楼梦新证》
至于第五六回的梦遗和初试云雨,作者的意图只在于写出性发育,作为以后写“情”的生理性基础,是否合乎男子精通年龄,并不需要年龄的合理性显示。[5]因为导致这一事件的“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第五回回目)本身就没有任何“现实合理性”。
周汝昌所编《红楼年表》,以贾宝玉十三岁作为叙时标杆。但贾宝玉十三岁的依据,就是癞头和尚手执通灵宝玉所说“青埂峰一别,展眼十三载矣”的顽石下凡神话,而非实际生育和成长过程。
贾宝玉的外貌,定格在第三回幼年林黛玉所见“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面如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明显不合宝玉当时年龄和现实情理。
笔者曾用“童性年龄与少年青春气息的二重性”来阐释这种特殊的非写实笔法。[6]显然作家的意图,重在传人物思想性格之“神”,而非年龄和生命成长之“形”。
所谓“大小宝玉”,只是作品描写贾宝玉不同故事(如大观园内外交往)是给人的感觉,属于情节处理范畴,并非实际年龄变化。
怎么“修订”?为了要使贾宝玉“梦遗”的年龄合乎现实逻辑,煞费苦心地修改黛玉进府宝黛见面的年龄,结果林如海的早教没有了,宝黛因年幼“一桌子吃饭,一床上睡觉”(第二十八回贾宝玉语)的合理性没有了,顾此失彼,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此胶柱鼓瑟,犯了违背文学创作原理的错误。这样行吗?

刘旦宅绘宝黛情深
林黛玉的年龄也是一样。第四十五回林黛玉说“我长了今年十五岁”,把林黛玉的年龄提升了三岁,由于有庚辰批语,可以肯定是曹雪芹的手笔,至第四十九回又特别用群钗“皆不过十五六七岁”相呼应。
但修订者就因为与第二十五回贾宝玉十三岁年龄线相矛盾,擅自删去这两处年龄提升文字。表面看,似乎与宝玉十三岁年龄线实现了“和谐”,但这样一来,原来贾宝玉十三岁年龄线所遭遇的家族史叙事与青春梦叙事的矛盾就重新凸显出来了。
这正是曹雪芹有意提升林黛玉年岁所要解决的问题。[7]没有弄清楚曹雪芹的写作意图,也没有理解曹雪芹所创造的叙时手法,就以一己之见妄改原文,这样行吗?。
《红楼梦》是语言艺术作品。包括年龄因素在内的宝黛等人物形象都是曹雪芹语言构筑的虚拟图像,他们的故事又多半发生在虚拟的青春世界大观园里,这种双重虚拟使得精确的年龄叙事既不必要也无可能。

《红楼梦影视文化论稿》
今人改编红楼故事的影视剧演员选秀,都不能不提升年龄档次。何卫国先生《红楼梦影视文化论稿》引述王扶林导演所说,小说主人公十二三岁的孩子,却只能选十七八岁的孩子来演。[8]
可见文学形象与现实形象,艺术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差异。曹雪芹一再提醒“不拘拘于朝代年纪”,是深味创作甘苦的导读之言。
事实上,尽管是“假语村言”之作,曹雪芹为了解决人物年龄叙时与情节叙事的矛盾,已经做出了巨大努力,进行了“新奇别致”的艺术创造。对它的美中不足,红楼梦中人应当给予“同情的理解”,而不应过分纠结。
此刻,笔者又想到陈文所提的鲁迅《故乡》的例子,作品描述,“我”与闰土三十多年不见,见到闰土第五个儿子水生,“我”的反应却是:“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
这么明显的叙时失误,为什么鲁迅著作一再出版,却未曾“修订”改正呢?我想,这是因为《呐喊》所收的原文刊于一九二一年五月《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保留《呐喊》原文包含写作叙时失误的历史形态,这正是鲁迅的真实,也是后人对鲁迅和历史的尊重。[9]

《鲁迅全集》
对《红楼梦》历史文本的包括人物年龄叙时的美中不足,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取同样态度呢?
2025年10月21日于深圳
注释:
[1] 陈熙中《红楼求真录》,北京大学出版社,东方文化集成,2016年版。
[2]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齐鲁书社1988年版,36至37页。
[3] 参见刘上生《换一个角度思考——<红楼梦>人物年龄错迕问题新探》,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2024-9-15.
[4] 参见刘上生《守护经典文本的历史形态》,《红楼梦学刊》公众号2025-7-15
[5] 刘上生《探骊——从写情回目解味<红楼梦>》,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036至48页。
[6] 刘上生《探骊——从写情回目解味<红楼梦>》,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032页。
[7] 参见刘上生《林黛玉的年龄添加和曹雪芹的“大时间观”》,《曹雪芹研究》2025年第1期。
[8] 参见何卫国《红楼梦影视文化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版,333至334页。
[9] 《鲁迅全集》卷1《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476至486页。
相关阅读:
刘上生《走近曹雪芹——<红楼梦>心理新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刘上生《从曹学到红学》,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刘上生《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的叙时操作——再谈曹雪芹的“大时间观“》,古代小说网2025-5-14
刘上生《宝黛之恋情理矛盾的艺术处理》,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2025-5-8
刘上生《袭人进言的叙时误差——<红楼梦>叙时双线初探》,古代小说网,2025-5-22
刘上生《琪官事件的浓缩和留白——<红楼梦>叙时艺术再探》,古代小说网,2025-6-2
刘上生《生辰私祭为那般——读<红楼梦>新探》,光明网205-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