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人类学家》作者:奈吉尔•巴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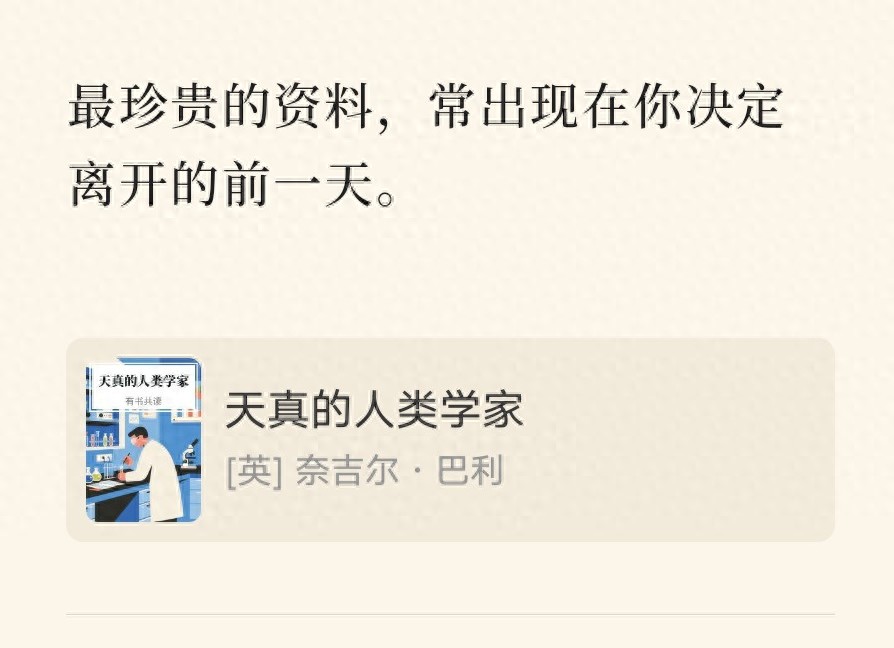
上一节,我们讲到作者巴利在田野调查期间遭遇了种种不幸和困难,但他并没有被吓倒,而是坚持了下来;与此同时,他也学会了利用多瓦悠兰的规则,推进自己的研究项目。
那么,在这一节中,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么变得不再“天真”的?
“无耻”地操纵祈雨巫师
巴利曾读过很多人类学家的著作,他们声称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最后终于赢得了研究对象的全面“接纳”,成为当地部落的“自己人”,进而掌握了他们的“文化密码”。但巴利觉得,这种所谓的“接纳”,往往只是人类学家的一厢情愿。
事实上,一个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的访客,根本不可能被全盘接纳,也不可能变得和当地人毫无二致。只能说他通过努力融入,会被相对接纳,借此看到一鳞半爪的“真相”,然后像玩拼图一样,用一种说得通的逻辑把它们拼在一起。
巴利发现,在多瓦悠兰,成年男性的年纪与地位成正比,就是说年纪越大地位越高。多瓦悠人如果尊崇一个人,就会称他为“老人”,比如他们会称巴利“老人”甚至“祖父”。而在“老人”交谈时,孩子不能插话,甚至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
巴利的助理马修就是个不到20岁的大孩子。他之所以能够跟随巴利,是因为他上过学,懂法语,有能力帮巴利翻译。可在部落里的老人看来,马修即便只是站在那里,也像个烂手指一样刺眼。也得亏马修家是个大家族,到处沾亲带故,所以很多酋长和巫师才能容忍他的存在,巴利也才有了能深入访谈的机会。
那么,男孩要怎样才能变成成人男性呢?这就需要一场割礼仪式。尽管他们要遭受肉体疼痛,但这在他们看来却是一种荣耀之举,因为能承受痛苦本身就是成人的标志,就像雨季转为旱季小米才能成熟,男孩要经历割礼才能变身成熟的男性。
而在割礼仪式中,猎豹元素可以说随处可见。小男孩们往往要以豹纹来装饰自己,而割礼人则手持利刃,发出豹子杀死猎物时的咆哮声。不止这一仪式,多瓦悠人的其它仪式也跟猎豹文化有关,比如头颅祭,村民们在举行仪式时会把死者的头颅摆到树上,模仿的也是在自然界中,猎豹把猎物拖到树上后才慢慢吃掉。
巴利进一步调查发现,在类似的“猎豹文化”中,总有祈雨巫师的影子若隐若现。他是无意中发现这一点的,那天他在树下躲雨,偶遇祈雨巫师卡潘的儿子。男孩看着雨水落下说道:“我爸爸死后会变成豹子,到时我就继承了雨的秘密。”这引发了巴利对卡潘老人的兴趣,他决定前去拜访,探讨祈雨巫师祈雨的秘密。
但是,想从一名见多识广的巫师嘴里挖出秘密绝非易事。每次谈到关键处,卡潘老人就会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他。后来巴利了解到他和蒙哥村的祈雨酋长是死对头,于是狡猾地“操弄”两人间的矛盾,像挤牙膏一样挤出了卡潘的秘密。
巴利先去蒙哥村拜访,告诉那位酋长说“真正的祈雨酋长”是卡潘老人,自己想知道他祈雨的故事,那位酋长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主动吐露了很多祈雨的机密。接着巴利又对卡潘如法炮制,说蒙哥村的祈雨酋长才是真正的专家,请卡潘告诉自己这位“专家”的故事。通过这一激将法,卡潘开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田野考察即将结束,巴利提出最后一个请求,他想亲眼目睹卡潘是怎么祈雨的。卡潘先是展示了自己常用的祈雨神器:一撮未阉割的公羊毛,帮助阴云快速聚集;一个铁环,可以把降雨控制在某个特定的局部区域,等等。
最后老人郑重地拿出一只蓝色小球,说这是他最伟大的法器,从未让外人见过。巴利定睛细看,是颗小孩喜欢玩的蓝色弹珠。他问这颗珠子是否来自英法等国。卡潘连连摇头,说是几千年前的祖先们传下来的,只要用公羊毛涂抹就会下雨。
但巴利还是怀疑这个弹珠的来源,于是他心生一计,专程到城里买了几颗蓝色弹珠,拿给卡潘老人看,并问道:“你上次给我看的祈雨石头,是不是跟这些一样啊?”卡潘惊呼一声,拿起一颗对着阳光细看,说:“一样的,只是这个石头里的云彩比较暗些!”
巴利又问:“那它们也能造雨吗?”卡潘瞪大眼睛说道:“这我怎么知道?我要试试看,才知道行不行。没亲身试过,我可不能乱下判断。”巴利哑然失笑,如此看来,卡潘老人还颇有些科学家的实验精神。
最后巴利终于获得卡潘的许可,要去参观造雨的神山。马修听了急得直翻白眼,说这会引来天打雷劈;巴利则提醒说多瓦悠的雷不会劈白人,马修只要紧紧跟在自己身后即可。他们爬上了神山,看到了祈雨洞,里面的石瓮装着祈雨的石头。那里还有一块巨大的白色岩石,卡潘说那是世界的防线,一旦移开大水将淹没整个大陆。
回程路上,他们遇到了超级暴雨。卡潘说祈雨成功了,他曾对着祈雨石吐出一种药草。被雨水打湿的花岗岩湿滑不堪,巴利狼狈地爬行。他恳求卡潘老人收了神通,让雨停止,老人淘气地笑道:“一个男人可不会在一天内既结婚又离婚的。”
最后的庆典和选美狂欢
巴利的田野调查开始接近尾声。除了割礼,其它能看到的仪式他都已经看到了。多瓦悠的年分为阳年与阴年,割礼只在阳年举行,而他来的这一年恰好是阴年。此外,割礼仪式还跟祈雨巫师的占卜情况有关,多瓦悠兰已经五年没举行了。
巴利是十月份离开喀麦隆的,刚好赶上这一年的国庆日大典。大典在波利镇的足球场举行,地方重要人物全部到齐。各个部族派出自己的歌舞队,顿足呐喊,以至于现场一片尘土飞扬。阳光晒得人几近枯萎,大家只能靠冰啤酒和冷饮来降温。
等到晚上,选美比赛开始了。镇政府的做法简单粗暴,发张公函给各部落酋长,规定他们当天选送规定数目的女子进城。这些参赛的女子大多是被迫而来,一脸不情不愿的模样,在观众面前走台步。有的泪汪汪,有的则怒目而视,呲牙咆哮。
有些观众想看得更清楚,爬到了树上居高临下看。他们发出的喧嚣影响到了坐在前排的贵客,于是警察用力摇晃树干,把树上的看客晃落在地,摔得呲牙咧嘴,引发旁边人一阵阵笑声。
某个来自偏远地区的女孩荣获第一名,被评为“波利小姐”。但她已经被吓坏了,当周围的人们起哄要她跳舞时,她泪汪汪地表示拒绝,最后被两名警察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扔出了场外,换第二名戴上“波利小姐”的桂冠,开始领舞。
巴利被镇上的医生太太捉住,跳了一场至少长达二十分钟的舞蹈。医生太太是个超级胖的女人,才跳了十分钟便疲态毕露,不是撞翻椅子,就是踩到自己的脚。因为担心中途叫停会让对方没面子,巴利也只能踉跄地跟着,累得气喘如牛。
一曲终了,巴利终于有机会坐下来,灌下一杯冰啤酒。接着,他和一位来自丛林的老师聊起天来。这位老师有个怪癖,不管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一把折叠椅,甚至在刚才跳舞时,他还和这把椅子欣然共舞,直到他人苦口相劝才停下来。
一群人喝光了现场所有的酒,还没有尽兴,又派一位已经喝得下半身瘫痪的男士去城里的酒吧买酒。这位男士醉得站都站不住了,但被众人抬上摩托车后,嗖的一声连人带车消失在了夜色中,并在五分钟后带着酒成功归来,真是个英雄!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醉醺醺的人突然吵了起来,然后开始干仗。巴利知道继续留下来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哪怕没有参与斗殴,只要是现场的目击证人,也会被警察传唤,后患无穷。于是他和那位老师,以及折叠椅迅速地逃离了现场。
接下来巴利需要办理离境许可。不幸的是,他的签证快要到期了。考虑到在喀麦隆办手续的习惯性拖延,他必须同时申请居留签证延期与离境许可。但办理人员告诉他,无线电坏了,他们无法和首都的主管部门取得联系,无法给他签发签证。
接下来的一个月,巴利被当成皮球,在多地的政府部门间被踢来踢去。他来回奔波,既破财又伤身,终于把某个部门的负责人惹烦了,下命令道:“给他签证!”而巴利耗时良久整理的盖满了章子的文件,人家看都没看一眼。
巴利决定在村里举办自己的离别派对。他通过各种渠道搞到了四十瓶啤酒,还请祖帝保的老婆帮忙酿了一些小米啤酒。但他支付小米的钱被某个男人拿走了,因为那人说祖帝保欠他兄弟一头牛,而这个人的兄弟的岳父又欠了他小米,所以他的兄弟要到他老婆的叔叔家,也就是祖帝保家来拿小米……复杂的关系把他绕晕了。
在派对上,马修负责分发啤酒。 他让大家排成一列,并指派一名助手分发每人一瓶啤酒,还详细解释啤酒是谁请的,为何请的。很快,全村人就陷入醉酒后的喧闹。一位老人领头,大家开始踏足舞蹈,绕着圈子,拍手顿足。有人趴在巴利脚边哀伤哭泣,鼓手则跪在他的面前,在摇曳的火光中奏出激烈的节拍……
突然,马修又神奇地现身了,手里抓着把百元的铜板。他大声“吩咐”巴利:“在每个人的额头贴上一枚铜板,主人!”巴利把铜板按在村民的额头上,赐福说:“愿你的额头隆起。”这是多子多孙的象征。村民们欢喜接受,舞蹈着离开了。
第二天,巴利准备开车离开。一小群村民现身送行,他们淡淡地微笑着,磨蹭着双脚,那些贪吃巧克力的小狗则用力地摇着尾巴。巴利挥挥手,引擎启动,离开了他待了一年多的村庄。一种淡淡的寂寞感涌上心头,那是分离所带来的空虚。
巴利终于回到了英国。他瘦了近40斤,皮肤漆黑如炭,因为患过肝炎而眼白发黄。当海关官员挥手让他通过时,已经习惯了西非繁琐的他总觉得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他故意地问道:“难道我不必大喊大叫、威胁你,或者给你钱吗?”
还有一次,送奶工把别人家订购的牛奶放在了他家门前,他大吼大叫地追了上去,习惯性地扯住人家的衣领。因为按照多瓦悠兰的规矩,这表明坚定立场,说明这不是他的牛奶;而在英国人看来,这却是粗俗无礼的表现。此外,他还无法直面超市里琳琅满目的货物,要么连绕三圈仍无法决定买什么,要么疯狂地购买一些奢侈品,并因害怕被人抢走而恐惧抽噎。
巴利花了很长时间,才逐步“走”出了这种西非后遗症。对他来说,一天里最棒的时刻莫过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英国的床上。他可没想到,仅仅六个月后,他就要回到西非,去见那些熟悉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