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暑期档,古装剧赛道本应是《子夜归》与《献鱼》的双雄对决,无数观众抱以厚望,期待又一部现象级作品的诞生。然而,当《子夜归》在迎来大结局时,其口碑与评分却一路走低。

《子夜归》宣传剧照
一、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当视觉美学凌驾于叙事平心而论,《子夜归》的“优点”是长在明面上的,甚至可以说是长在了观众的审美点上。
由导演侣皓吉吉操刀,标志性的唯美镜头语言、演员的服饰妆造、场景道具的细节打磨,都透着一股肉眼可见的精致与用心。光影、构图、色彩的和谐统一,准确地营造出一种引人入胜的奇幻氛围感,足以让观众被其“颜值”所俘获。

这份视觉上的成功,本应是剧集走向经典的坚实基础。然而,致命的问题在于,这个精美的外壳之下,包裹的却是一个逻辑混乱、情节潦草的内核。
剧集后半段,尤其是大结局的剧情,让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顽疾暴露无遗。当观众试图深入感受故事魅力时,却被一次次的情节硬伤和逻辑断层无情地推开。这份割裂感,成了《子夜归》留给观众深刻的观后体验。

在前一集中,梅逐雨为救众人,被常羲锏从背后穿心而过,这是一个悲剧色彩与视觉冲击力的“死亡”场面,足以让所有观众为其揪心。
按照正常的戏剧逻辑,接下来的剧情要么是主角团如何艰难求生,要么是通过某种高代价的方式将其复活。然而,编剧选择了——在下一集中,通过他人之口轻描淡写地解释为“他只是昏了过去”。

这句解释,瞬间让之前渲染的悲壮氛围沦为笑柄,并直接悬置了两个核心的戏剧性问题:
生理逻辑的缺失: 一个被武器穿透身体的凡人,是如何在没有任何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存活下来的?
转变逻辑的断裂: 梅逐雨复活后为何会妖化?这是他人设转变中关键的一环,但剧本却粗暴地跳过了所有过程,直接呈现结果,不负责任地让观众自行“脑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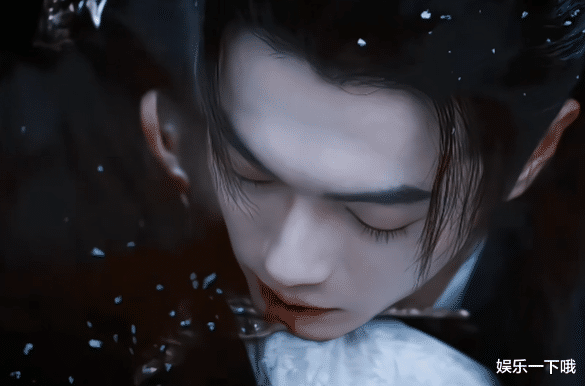
这种编剧技巧上的“偷懒”,本质上是对戏剧创作规律的漠视。它破坏了故事的“因果链”,让角色的行为失去了动机,让情节的发生失去了根基。
当主角的生死都能如此儿戏,那么故事中其他的情节硬伤,如角色随意穿越时空却不引发蝴蝶效应、强大的蛇公其弱点竟是区区硫磺等,便显得越发刺眼和不可容忍了。

如果说主角线的逻辑问题令人扼腕,那么反派阵营的“集体降智”和“草率下线”,则是浇灭了观众对一场精彩正邪对决的最后期待。一部剧的戏剧张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派的强度与魅力,而《子夜归》的反派,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雷声大,雨点小”。

动机浅薄的大师兄: 作为前期的核心反派,大师兄的黑化本应是推动剧情的关键。
然而,剧本给出的根本原因,仅仅是出于一些站不住脚的嫉妒心。
一个格局如此狭隘、动机如此浅薄的反派,不仅无法让观众共情,更拉低了整个正邪冲突的层次,让主角的对抗显得像一场“内部矛盾”的小打小闹。

脆弱不堪的无字书: 无字书作为中期的搅局者,被渲染得固执而阴暗,制造了大量麻烦。观众期待的是一场智慧与意志的较量来将其收服。
结果,它在发现自己“不被需要”后,竟脆弱到不堪一击地自我了断。这种处理方式,浪费了一个很有潜力的“概念型”反派,让之前的种种危机都显得莫名其妙。
一招制敌的BOSS: 全剧蕞大的败笔,莫过于反派的塑造。这个号称不死不灭、要毁灭人妖两界的灭世级存在,其危机铺垫得天花乱坠。然而,到了决战时刻,女主角武祯几乎没费吹灰之力,一出手便轻松解决。所谓的“灭世危机”,其烈度甚至不如一场普通的单元案件。

这种反派塑造模式,在剧中反复上演,形成了一种令人腻烦的套路。它让本该是全剧高潮的正邪大战,变成了一场场索然无味的过场表演。观众的情绪刚被调动起来,反派便应声倒下,这种重复性的挫败感,严重消耗了观剧热情。更重要的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对手,只会让主角的胜利显得毫无分量、廉价。
结语:华美的“空心病”,古偶剧创作的警钟复盘《子夜归》的口碑滑坡,我们不难发现,其根源在于一种创作上的“空心病”。创作者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打造一个华美的视觉外壳上,却忽视了故事才是电视剧真正的灵魂。

当剧本的逻辑基石不稳,当角色的行为动机缺失,当反派的塑造流于表面,那么再精良的服化道、再唯美的镜头,都无法拯救这部剧的内在贫瘠。它们反而会加剧一种割裂感,让观众在欣赏美的同时,愈发感受到故事的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