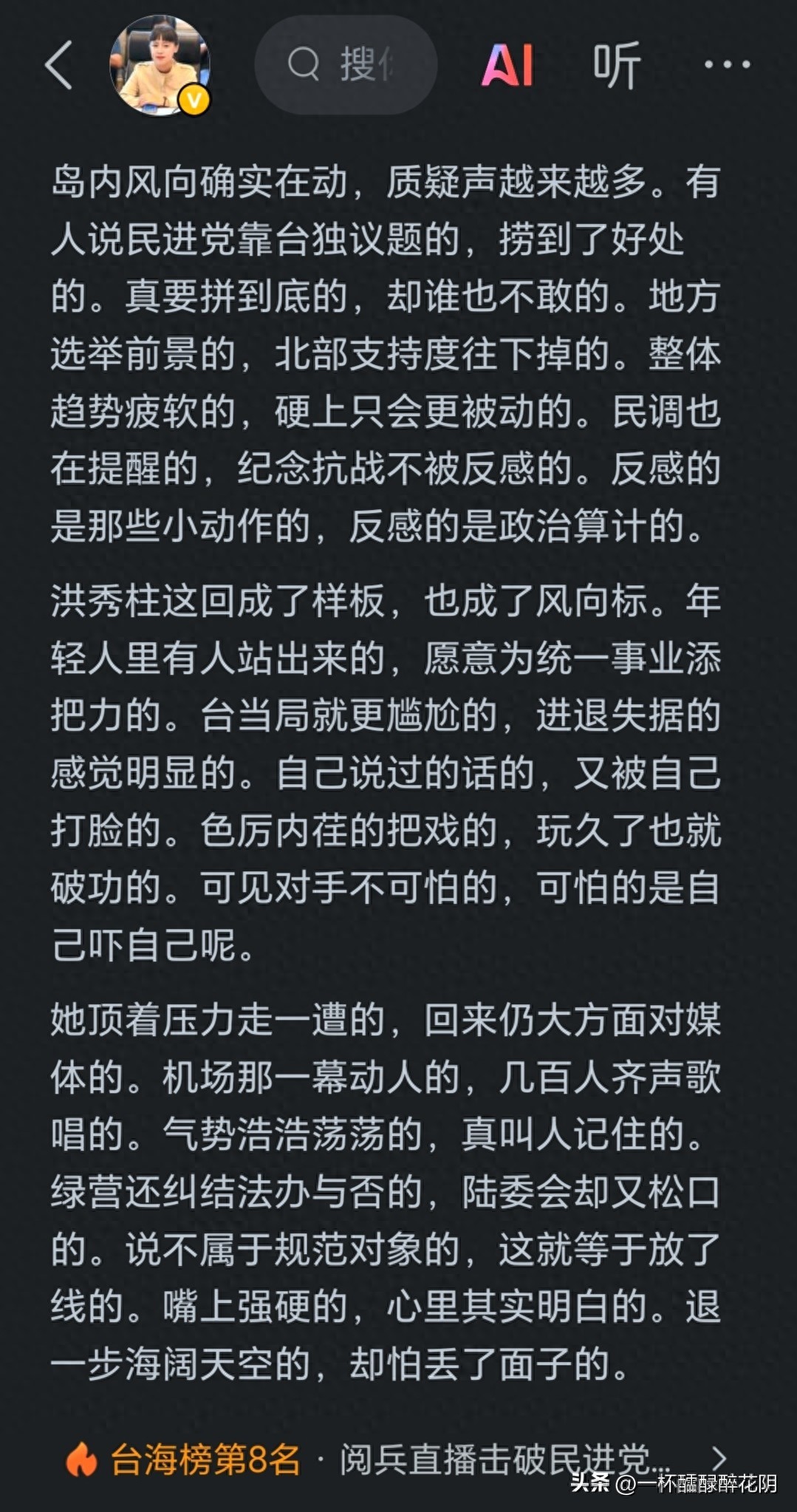
近日看到一篇出自中国人民大学老师飞岸之手谈“洪秀柱九三阅兵到访大陆,民进党拿她没办法”的文章引发评论区讨论。根据专业统计工具统计,文中含标点符号有2632个字,其中“的”字有207个。如果文章不含标点符号和其它格式符号,只是文字的话,其中“的”字共出现了 132 次,出现的频率约为6.65%,即平均每100个字中出现约6.6个“的”字。大量冗余、错位的“的”字、零散的口语化碎句,以及逻辑松散的分句衔接,让“大学老师文字功底差”成为评论区的焦点。
争议的核心并非“口语化表达”本身,而是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当大学老师选择用口语化风格进行文字创作时,是否可以抛开文法规范?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口语化从不是文法失范的“免责符”,尤其对长期与文字打交道的教育者而言,用口语化讲好时政热点的前提,恰恰是用文法守住文字的底线。
首先要搞清一个认知误区:口语化表达不等于口语化文法。前者是风格选择,后者是语法缺陷;前者追求通俗易懂、贴近受众,后者则是逻辑断裂、结构残缺。生活中我们会说“这场阅兵真震撼,看得人心里热乎”,这种口语化表达鲜活自然,但转化为文字时,需调整为“这场阅兵场面震撼,让人热血沸腾”。不仅保留口语的表达,同时遵循“主谓宾”的基本语法结构,避免出现“阅兵声势浩大的,场面很震撼的”这类“的”字残句的停顿。
遗憾的是,飞岸的文章恰好混淆了二者的边界:“台当局怕什么来什么的”“余音还在耳边的”等表述,把口语中的临时停顿习惯直接搬进文字,让句子沦为“未完成的语法片段”;“呢”“啊”等语气词的滥用,如“可到了关键节点呢”“踢皮球的套路啊”,则进一步割裂了文字的连贯性。这种“把口头聊天直接敲成文字”的做法,并非真正的口语化表达,而是对“文字载体特性”的忽视。发言时可凭语气、停顿弥补逻辑漏洞,文字却只能靠文法结构传递信息,一旦文法失守,再鲜活的内容也会变得拖沓啰嗦。

对大学老师而言,文字功底的核心从不是“辞藻华丽”,而是“语境适配能力”。根据文本场景调整表达,让风格服务于内容,而非让内容迁就随意的表达。作为教育者,其文字输出天然带有“示范属性”:可能是学生眼中的写作范本,也可能是公众认知中知识群体表达的缩影。
当选择口语化风格时,更需展现“化繁为简”的功力。用通俗的语言讲清复杂的道理,用规范的文法保证表达的流畅。比如同样讨论两岸议题,规范的口语化表达可写“洪秀柱赴陆参加阅兵,不仅打破了台当局的舆论垄断,更让岛内民众看到了两岸交流的另一种可能”,既直白易懂,又通过“不仅……更……”的关联词理清逻辑;而飞岸的文章中“她一亮相的,气氛就被点着了”“握手三十多秒的,细节被台媒反复解读的”,则用冗余助词破坏了句子的语法完整性,让本应清晰的逻辑变得模糊。这种“想口语化却失了文法”的情况,本质是缺乏“文字打磨意识”。即便追求轻松的风格,也需对“的”字的使用、分句的衔接、语气词的取舍做基础优化,这不是“吹毛求疵”,而是文字工作者的基本素养。
更进一步说,文法规范不是束缚表达的枷锁,而是让表达更精准的工具。口语化的核心是拉近与受众的距离,而文法的作用是确保信息准确传递,二者本可相辅相成。比如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常被赞“口语化却不失文采”,他写“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用逗号衔接短句,既保留口语的节奏感,又通过“明亮的、丰满的”的定语结构保证语法规范;老舍先生的小说更是口语化写作的典范,“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揣起保单,拉起车,几乎要哭出来”,没有冗余的助词,却用“揣起、拉起”的连贯动词,让口语化的句子充满画面感。

反观飞岸的文章,“岛内观看不少的,说有五百万观看的,社交平台热得发烫的”,三句本是“观看人数多-具体数据-平台反应”的递进关系,却因缺乏关联词、滥用“的”字,变成了三个孤立的碎片,读者需费力拼凑逻辑,反而失去了口语化应有的“易懂性”。这恰恰说明:抛开文法的“口语化”,最终只会让表达沦为“混乱的碎语”,既达不到沟通效果,也辜负了受众的期待。
回到最初的争议,人们质疑大学老师文字功底差,本质是期待教育者能成为文字表达的标杆。不仅能在学术领域写出严谨的论文,也能在公共表达中用规范的文法、恰当的风格,传递清晰的观点。口语化从不是“粗制滥造”的借口,尤其对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的人而言,把口语化的内容写得规范、自然、流畅、有温度,才是真正的文字功底。毕竟,文字的力量不仅在于内容的深度,更在于表达的精度。文法是骨架,风格是血肉,没有骨架的血肉,再鲜活也难以立起来。期待更多教育者能意识到:口语化表达可以有,但文法的底线不能丢。这不仅是对文字的尊重,更是对受众的负责,对“教育者”这一身份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