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戒烟的第三十七天,家里开始弥漫一种奇怪的安静。
从前,每天清晨六点,阳台便会准时亮起一点猩红,烟雾从推拉门的缝隙渗进客厅,像某种无声的宣告。接着是压抑的、从胸腔深处挤压出来的咳嗽,沉闷,绵长,如同老旧的发动机试图启动。那是二十年来我起床的号角。如今,号角喑哑了。阳台空荡,只剩那盆半枯的茉莉,在灰白的天光里静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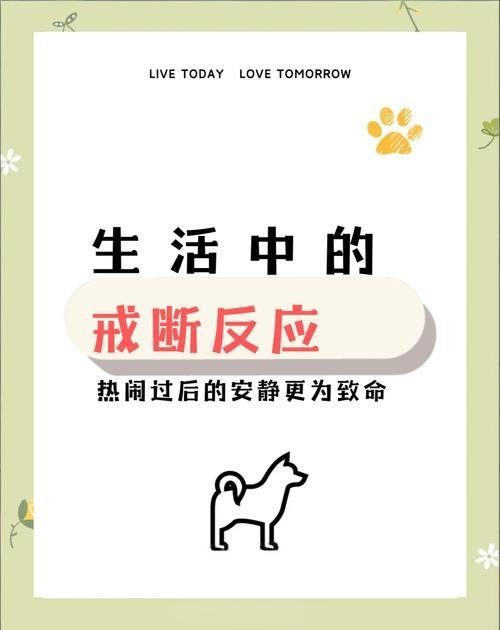
安静,本应是愉悦的。可这安静太重了,像吸饱了水的棉被,沉沉地覆在每一寸空气上。父亲坐在他惯常抽烟的藤椅里,双手无处安置——它们本该夹着一支“红塔山”。手指时而蜷起,时而张开,最终只能神经质地、一遍遍摩挲磨得发亮的竹扶手。他的目光没有焦点,穿过玻璃,投向楼下空无一人的院落。整个人的姿态,像一尊被突然撤去支撑的雕塑,勉强保持着形状,内里却是慌乱的失重。
家里一切如常,又一切都不同了。餐桌对面,他咀嚼的速度变得迟疑,仿佛味觉也随那一缕青烟飘散了。新闻联播的片头曲响起,他不再下意识地去摸口袋,转而端起茶杯,喝一口,再喝一口,喉结剧烈地滚动,吞咽下的,分明是另一种焦渴。夜里,我偶尔醒来,会看见他卧室门下透出的光,以及地板上那条长长的、来回踱步的影子。那影子被灯光拉得变形,摇曳不定,像一个找不到归处的魂。
原来,戒断反应不只属于生理。它是一种生活节律的崩解,一场小型死亡的演习。抽走的,不止是尼古丁,更是嵌在时间褶皱里的所有习惯仪式:饭后那一支的圆满,烦闷时那一口的灼烧,思考时那一道袅袅上升的视线。这些细小的齿轮,曾如此精密地带动他一天的生活向前滚动。如今齿轮徒然空转,发出刺耳的、只有他能听见的噪音。他戒掉的是一种瘾,留下的,却是生活本身被打散后的茫然与空旷。

直到那个周末的清晨,我被细碎声响唤醒。走到客厅,一幅画面让我驻足。
父亲依旧坐在阳台的藤椅里,侧影沐在薄金般的晨曦中。他手中没有烟。取而代之的,是一杯茶。他双手捧着那只厚重的白瓷杯,举到唇边,并不急于喝下,而是闭着眼,深深嗅着杯中蒸腾的热气。白雾濡湿了他的眉眼,他脸上有一种久违的、近乎虔诚的平静。然后,他极小口地啜饮,让茶汤在口中停留片刻,才缓缓咽下。一套动作,缓慢,专注,自成庄严的节奏。
那一刻我恍然。阳台仍是那个阳台,清晨仍是那个清晨,人仍是那个人。猩红的火点与呛人的烟雾确已缺席,但一种新的仪式,正带着试探性的郑重,悄然填补那巨大的虚空。茶杯很烫,白雾氤氲,将他与世界温柔地隔开。他不再望向虚空,而是看着杯中旋转沉浮的叶片,像在凝视一个初生的、尚显脆弱的新世界。

原来,戒断的终点,或许并非“戒除”,而是“置换”。当旧日依附的实体烟消云散,生命会本能地寻找新的凭依。那凭依可能是一杯茶的温度,一段更长的晨走,或仅仅是与家人多聊的十分钟。它可能更健康,也可能同样微不足道,但其核心,是人类对“秩序感”永恒的渴求。我们借由这些自设的仪式,在时间的荒原上打下界桩,告诉自己身处何地,去往何方。
父亲喝完茶,起身,轻轻舒展了一下肩膀。他回头看见我,脸上掠过一丝赧然,随即释然,笑了笑:“这龙井,还挺香。”
阳台上,茉莉枝头,竟冒出了几个怯生生的、洁白的花苞。晨雾正在散去。我知道,往后的清晨,依然会有点什么,准时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