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一是观光上国的颂美之情,描写山川雄绝、风物奇异,讴歌国朝盛世、帝王功业,崇壮美,尚豪迈,风格悠容闲雅、平实质直。二是感伤身世的羁旅之思,基调消极低沉、飘零愁苦表达颂美之情的诗人群体以非汉族作家和北方文人为主,南方文人大多表现出愁苦倾向。笔者认为,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和心态,受创作群体的族群、地域身份影响,与元代的科举、根脚、任官制度等社会背景有关。
一、斯人亦何幸,生时属休明
经过对上京纪行诗的翻检,可以发现表达颂美之声的诗歌占到绝大多数,其中又以歌颂大元、歌颂皇帝为最,从元初到元末层出不穷,且创作群体覆盖度广。
首先,从整体来看,上京纪行诗表达赞叹之情的诗篇和作者数量居多,身份多样,包括勋贵世臣、中原文臣、释道名流和布衣文人。
耶律铸字成仲,是元初勋臣,“宪宗征蜀,诏铸领侍卫骁果以从”宪宗崩,独身归于世祖,后拜中书左丞,制大成乐。世祖北征,他曾“征兵扈从,败阿里不哥于上都之北”。

耶律铸《凯乐歌》《凯歌词》等诗多记征战之余的所闻所感,从中可见元初武力强盛与其赞颂之情。其他如王恽《观光》、刘敏中《上都视草堂书事呈郑潜庵》、柳贯《滦水秋风词》、黄溍《上京道中杂诗》、胡助《滦阳杂詠》、马祖常《北行歌》《驾发上京》、等,在诗中主要表达的是对元朝升平气象的歌颂和对君王德政恩泽的感念。
柳贯、黄溍是江南人士,又是馆阁名臣,儒术标榜一时,马祖常是受汉文化影响极深的色目文士,薛玄曦、张嗣德是道教名士,释梵琦是释教名流,柯九思曾入朝为鉴书博士,又与杨维桢、倪瓒、张雨等人在玉山草堂流连觞詠声光辉映,同仁交游,声气相通,影响着当时的江南文坛。以此管中窥豹,可见上京纪行诗此类倾向之繁。

其次,上京纪行诗的积极心态体现在文士对大元盛世的描绘,流露出躬逢盛饯的自豪骄傲。这一类型与前一种的歌颂除了诗歌表达侧重点有所不同,其他特征如作者群体分类、时代先后几乎重叠。
再次,上京纪行诗自然悠容的风格多出现在风物描写中。这类诗歌普遍呈现出去主观化、去情感化的特点,作者较少掺杂自己或喜或悲的情感杂质,而对异域风光采取观察、欣赏的态度,抛开仕途顺蹇、遭际泰否、年齿老去的感伤,避免单方面沉浸式的自我表达。

观光上国的积极倾向在上京纪行诗中除上述三类外,还有一些诗作。没有明显的感情表达,只在景物描写中含蓄地体现出作者疏落开阔的襟怀和畅达悠然的心情。

“滦水亭亭带玉京,风霜朝暮写官城。深秋还幸山川丽,侍史登高暑气清。”深秋登高,远眺滦水,山川清奇,使人暑气顿消,心境明朗开阔。
“云边薄雾初开障,雨后清风不起沙。路入天关还作客,境非人世欲忘家。涓涓石溜鸣苍玉,闪闪林霏散彩霞。一望浮屠遍山谷,南薰偏发傍岩花。”雨后过居庸关,薄雾消散,清风拂面,仰视山势峥嵘,山泉涓涓,竟有出尘隔世之感。在整首诗中看不到作者个人的主观介入,即“无我之境”,但处处都可感受到诗人的闲适心情。
二、家在千山外,思归未有期元代统一之后,文人的活动范围远超前代,南仕北游是当时的社会潮流。元代中期一批馆阁文臣因职务之便大量前往上都,亦有少部分布衣文人千里北上。远赴异域,也催生了“他乡视角”下被寄予乡愁情结的“江南书写”。同时,也因为有了地域隔膜,上京纪行诗中便也出现了消极低沉、凄凉哀叹的色彩。

首先便是作为游子的怀乡客愁。这种漂泊在外的零落之感、故园之情往往和羁旅愁病、客途疲乏、蹉跎岁月连在一起,悲叹自己虚度年华,整日劳碌却只是徒劳奔忙、一事无成。诸如胡祗遹《投宿洪赞》《过龙门》、马臻《得家信》《滦都旅夜》《昔闻》、陈义高《范侍郎自燕都来惠韭》、揭傒斯《滦河晓月》《望云感秋》等诗。
这些诗里有宦海沉浮数年依然官职低微的牢骚,有节序匆匆短鬓生白蹉跎岁月的遗憾,有羁旅风尘多病缠身的愁苦,这些大多最后都会落脚在思家怀归上。以上是从上京纪行诗中遴选出的具有代表性、类型特征明显的诗歌情感倾向。这类诗歌除主题情感高度类似外,还有大致统一的风格特征。

揭傒斯《望云感秋》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天涯节序去匆匆,秋色人情特地同。昨日轩窗犹酷暑,今朝庭院已凄风。苍凉短发侵晨镜,牢落羁怀怯候虫。乡国三年归未得,又将愁眼送归鸿。”
首联写自己独自零落天涯,惊风白日光景匆匆,不知不觉节序变更秋意侵人,萧瑟秋光与客子羁怀两相映衬,更添愁情。昨日尚且酷暑逼人,今朝却已秋风席卷,一夕之间天地暗换,不由人惊心于光景飞驰。再看镜里短鬓斑斑,刘秉忠有句“年去年来鞍马上,何成。短鬓垂垂雪几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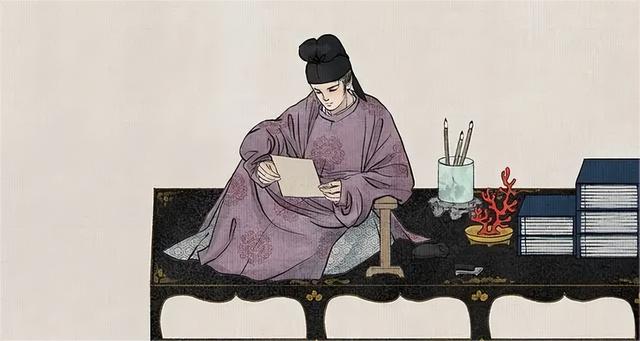
作者虽未明说,但同刘秉忠一样有短鬓沾雪之叹是一定的,感伤自己老之将至。独自一人流落此地,心中满载零落芜杂的客子愁情,甚至怕听到随节序变更而鸣的候虫声。故园已经三年欲归未得,只能将自己一片游子之心寄予归鸿。
此诗以节序、秋色、酷暑、秋风、候虫、归鸿串起全诗,作者因时节偷换引起感兴,包含了时光飞逝、短鬓染霜、芜杂羁怀、思归不得、归鸿传意的多重感情倾向,其他此类诗也多是这种写法。消极低沉的感情倾向还表现为对上京生活习惯的不适应,在汪元量、马臻等南方诗人的诗中都有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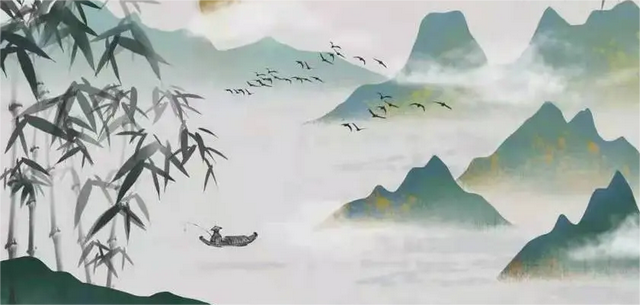
刘鹗《九月三日龙虎台接驾晚宿新店》:“关南九月草凄凄,又见征人护跸归。日落毡车团野宿,天寒塞马觅群嘶。徬徨恋阙孤忠在,俯仰随人百计非。犹幸诸公同笑语,归来茅店谩鸡栖。”

首先这首诗并不是作于前往上都的途中,而是因接驾所作。元代制度规定,皇帝出巡上都,从大都北门健德门出城,百官要为皇帝引导送行,一般送到大口。“大驾时巡,千官导送至此,其迎驾如之。”大驾南还,官员要出城迎驾。
迎驾一般在龙虎台,也即新店纳钵,距大都约有百里,上京纪行诗中有很多迎驾诗。至大口,“独守卫军指挥、留守怯薛、百辟于此拜驾;若翰苑洎僧道、乡老,各从本教礼祝献,恭迎大驾入城。”
其次,它体现了刘鹗对扈从、迎驾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感到俯仰随人不得自由,身处宦海百计皆非,另一方面虽然彷徨纠结,却又因为一腔孤忠恋阙不去。同时,虽然内心煎熬痛苦,幸而还有同僚好友相与忘忧聊作慰藉。
 三、上京纪行诗,情感与创作
三、上京纪行诗,情感与创作上京纪行诗之所以出现上述情感差异,虽然有创作主体个人才性的缘故,但应该看到背后的必然性,而不是把这个问题简单化,用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情感表达的主体差异来解释。其背后的必然性,与作者群体的身份有关,也与元代文人的社会境遇密切相关。
所以,笔者将对上京纪行诗人群体进行初步归并,再以此为基础,从元代的族群、地域以及科举、选官等社会、政治制度、政策出发,结合上京纪行诗人群体身份归属,以历史的眼光,对之进行细致分析。

上京纪行诗诗歌、作者数量众多,是不争的事实。有相当一部分作者仅仅留下吉光片羽,在其他作者的作品里能够看到相关唱和,证明其曾到过上都且有过文学活动,但其本人创作却已难以窥见全貌,大多仅仅留下一两首诗。
《文学评论》中提到:“上京纪行诗人群体中,根据作者籍贯按照元代行政区域划分,南人占到绝大多数。”

按照生年排列元初北方文士占绝对优势,至元后期南方文士后来居上。不论来自南方还是北方,上京纪行诗中以积极昂扬豪迈壮阔的笔调歌颂王朝、以欣赏好奇的态度书写悠容闲雅的上都生活的内容占到多数,成为主流。

而色目诗人,在诗中或是极力赞颂元朝圣君贤明、武力强盛,或是对上京物产风俗、宫殿景观极尽描摹,沉浸其中。在诗中消极低沉的笔触写自己的思乡怀归之情、羁旅漂泊之愁的作者,多处于元代前期这些诗人的感叹内容大致相同,思乡怀归、年老思亲、道途困阻、羁旅漂泊,这些是人之常情,官职低微一项则是政治诱因。
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在上都旅行中怀念故乡、思念亲友,感叹羁旅漂泊者大部分是扈从文士中的汉族文化菁英。而与之相反的是,布衣文人和低阶官员,反倒较少这种消极低沉的感叹。社会地位较低的文人来到上都往往歌颂皇都壮丽、山势高峻,对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北地高远的风貌景观充满好奇和赞美。
之所以出现上述反差,其根源在于元代独特的社会背景。诗人群体有南北地域、不同族群、时代先后之分,这既是元代特殊社会状况在上京纪行诗歌创作上的反映,也是造就上京纪行诗情感多样的原因。

上京纪行诗作为一个整体,其中内容经过前文的条分缕析已经可以明晰,大致有三类:第一,豪迈壮阔,以歌颂赞美为基调;第二,纯粹写景纪实;第三悲苦惆怅,以思乡怀归为旨归。第一类直接表达对元朝一统的认同,第二类写景纪实实际上也是对大元疆域的描写体认,体现的也是对元朝统治的认同。
而第三类诗歌的出现则是因为诗人心态情感的多样性、复杂性,导致了上京纪行诗内容看似复杂矛盾的特点——文人一方面表达认同以期获得晋身的机会,另一方面是想要达此目的困难重重。正是这样看似矛盾实则互为表里的政治架构导致了上京纪行诗内容上的复杂性,也使得进退出处间的矛盾成为元朝文人最普遍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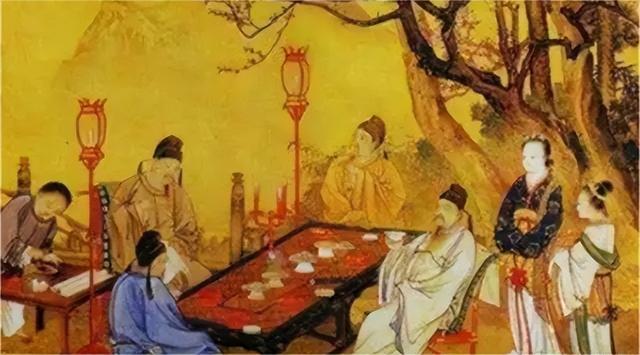 结语
结语积极的歌咏盛世与消极的自我感伤,这是上京纪行诗歌情感态度倾向的两面性。笔者认为,元代的社会和政治状况直接影响上京纪行诗人群体的创作心态和对上京这一煌煌帝都的认识,营造了上京纪行诗中积极、消极两种情感基调。
参考文献《元史》
《全元诗》
《草木子》
《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