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在廊坊隆福寺举行的瑜伽感恩大会,在我看来充满了戏剧性,因为活动不算顺利,闹了很多小插曲。
当大多数练习者如期抵达寺院办好入住,被通知参加一场临时召开的活动。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蛮横地转动。隆福寺住持告知,课程安排有变化,只是因为国外老师进不了寺院。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些人离开了,他们觉得主办方是骗子,既然练体式没有老师辅导,又为何要在寺院练习;有些人留下来了,有些态度相对坚定,或许跟主办方有些交情,相信主办方遇到了难处,期待他们后续的调整,还有一些持观望态度,毕竟他们只是普通的练习者,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活动第一天早上的体式课程取消,现场不乏从当地教室组团去的人群,有的老师在寺院里协调了一间会议室,先完成自我练习,再辅助其他学生练习。在老师眼中,纵然大会行程有变,还是要坚持练习,并力所能及地帮助学生。
出乎意料的是,主办方的协调能力很强,第一天下午就安排了Usha老师的一序列口令课,据说有些练习者表示早上已经练过,口令课就不练了,但会坐在旁边旁观。这种回复得到了Usha老师的肯定。毕竟,体式并非瑜伽的全部,阿汤强度如此之大,一天一次已然足够。
上课的地点改到了隆福寺旁边的功夫小院,走路10多分钟能到,只是要跟周末武术班协调上课的时间。
于是,第二天和第三天的练习课程只能安排到5:00-7:00,大家会于4:40在普贤院门口集合,再大部队集体从东门出,前往功夫小院。
只不过,第二天早上寺院还有小插曲,会停电,东门的电动门开不了,大家只能跟随主办方从西门出,一路沿着小树林徒步一小段,再绕到功夫小院,大约要走20多分钟。
那几天,恰巧要到新月了,仰望天空,只能看到一个小月牙,由于四周一片漆黑,月亮圆盘的影子若隐若现,大家甚至看到了类似月全食的神奇景色。
真可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尽管因为停电,要多走几百米,可是这奇特的自然现象,冥冥之中就像是给大家的奖励,可遇而不可求。
在功夫小院练习也有挑战,因为不是平地,而是武术垫上练习,亲测上面颇软。难怪Usha老师给我们演示站立手抓大脚趾上提时,会晃,她低调地说,是自己走神了,我倒觉得跟垫子软关系很大。
我缺席了第一天的体式练习,第二天来晚了,在旁边地上练的,只有第三天,才在垫子上完整练习了一序列,越练越感叹,这垫子实在是太软了,恨不得普通的站立前屈,或者向两侧打开的体式,我都要晃几晃,就更别提单腿平衡了。
可当我用眼睛斜扫旁边的同学时,他们倒是都泰然自若,会不会他们进入第三天的练习,已经适应了软软的武术垫呢?
三天的行程中,有一项是纪念掌门人,给他庆生,在主办方的安排下,我们坐车到了一个宴会场地,听老师们分享了与掌门人的故事,还吃了蛋糕。据说,这样的安排源自印度的传统,当一个人离世一年内,家人会找机会为他庆生,因为他们相信,他并没有真的离开。
尽管这次感恩大会的插曲颇多,难免让人觉得抢了主旋律的光环,当有些练习者没有第一时间离开后,反而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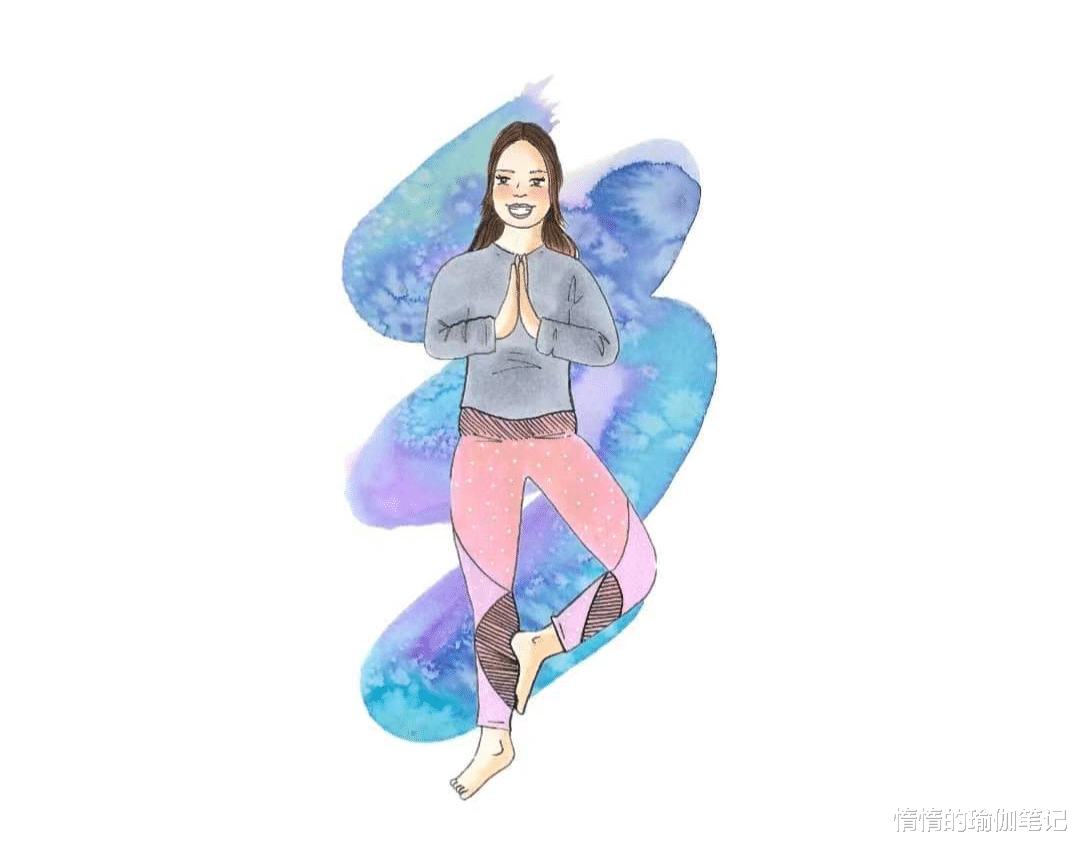
就像Usha老师后来提到的,或许,当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可以给自己多些时间和耐心吧!
两位老师在这几天的课上,不止一次提到瑜伽并非仅仅只是体式,还有其他七支,瑜伽练习也并不局限于垫子,垫子外还有很多机会,让我们练习瑜伽。
我能感受到,这样的观点是两位印度老师非常想传递给我们的,虽然我听了课,但我仍有点不确定,我理解的24小时瑜伽,是在生活中实践前两支yama和niyama,即调整自己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以及与自己的关系,这并不容易,但有意识开始实践还是可行的。
倘若有一天,我真的能自然而然地在生活中践行这前两支,才敢以yogi自称吧,不然,我最多只是瑜伽练习者。谁让yogi这个词,在我眼中特别神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