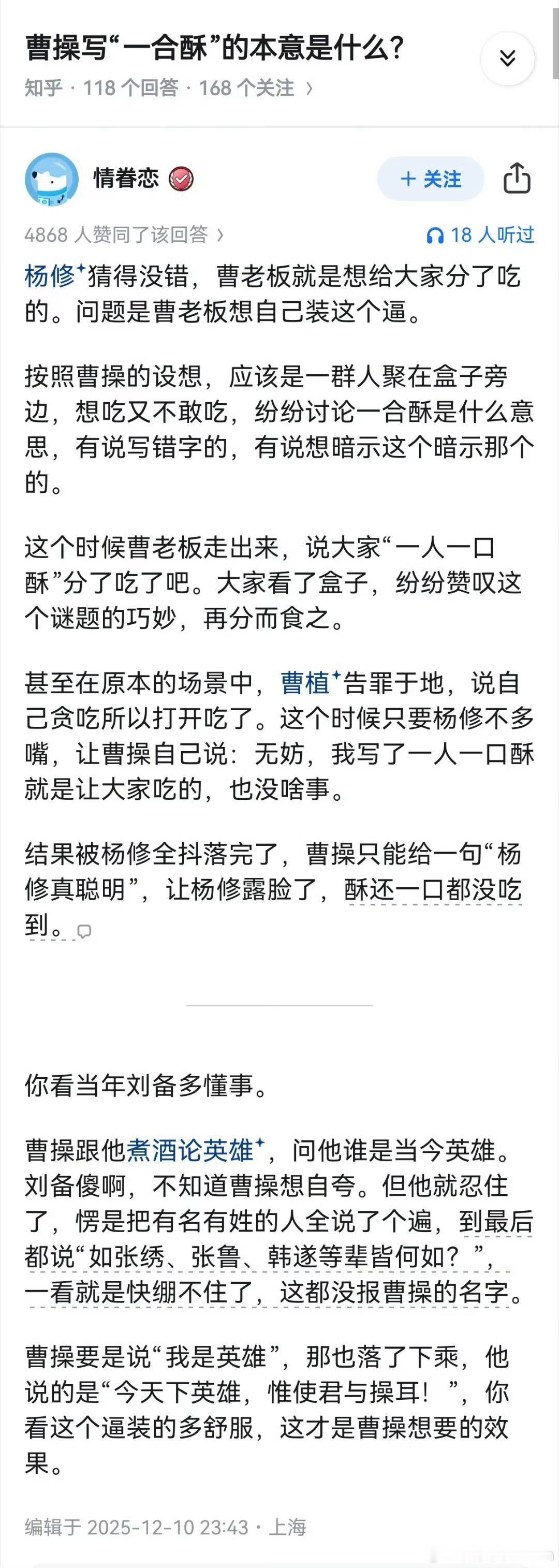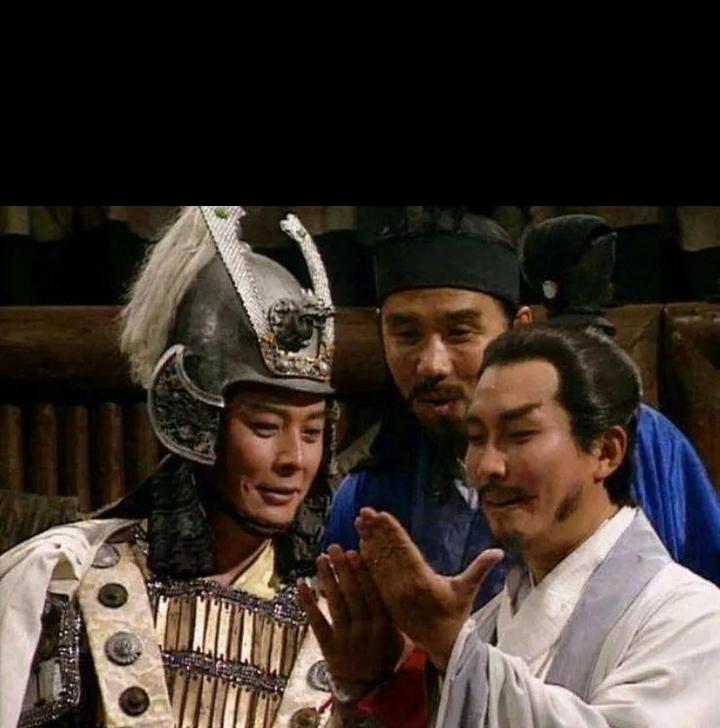洛阳城的雨已经下了三天。
司马懿站在铜雀台的最高处,望着被雨幕笼罩的皇城。
七十二岁的他身形消瘦,脊背却挺得笔直,玄色朝服下摆已被雨水浸透,但他毫不在意。
下面广场上,曹爽及其党羽的尸首尚未完全清理干净。
十天前的高平陵之变,司马懿以雷霆手段终结了曹魏宗室最后的力量。鲜血从广场石缝中流出,汇入洛河,将河水染成淡红。
“太傅,陛下有请。”内侍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
司马懿没有回头,只是微微颔首。
他知道,十六岁的曹芳此刻正缩在龙椅上,如同受惊的兔子。
从今天起,曹魏政权彻底落入司马家手中,曹操打下的江山,终于被他这个曾经的小小文学掾握在掌中。
想到这里,司马懿干瘦的脸上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
他想起四十年前,曹操在世时,曾拍着他的肩膀对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那时他吓得浑身冷汗,连夜写万言表忠书。而如今...
“告诉陛下,老臣稍后便到。”司马懿转身走下铜雀台,铁靴踏在湿滑的石阶上,步步沉稳。
雨越下越大了。

三个月后,司马府密室。
“父亲,这是从曹操陵寝暗格中发现的。”司马师将一只铜盒放在案上,脸色凝重。
司马昭凑上前来:“自高平陵事后,我们按父亲命令搜查所有曹魏宗室重要人物的府邸和墓葬,尤其是武帝曹操的。这盒子藏得极为隐秘,若不是工匠偶然发现机关,根本无从寻觅。”
司马懿缓缓睁开眼。自两个月前那场大病后,他精力已大不如前,但头脑却依然敏锐。他示意司马师打开盒子。
盒中只有两件东西:一卷竹简和一只小巧的铜制虎符。
竹简上的字迹让司马懿瞳孔微缩——那是曹操的亲笔。
“念。”他简短地命令。
司马师展开竹简,读道:
“余纵横天下三十余载,扫黄巾、破吕布、灭袁绍、逐刘备,终定北方。然观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汉祚已衰,吾儿丕虽承大统,然曹家天下能传几代,未可知也。
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久必生祸。若后世曹氏衰微,司马篡权,则依此符令行事。兖州陈留郡有‘寒门’一处,持此虎符往见,可保曹氏血脉不绝,亦有反制之后手。曹孟德绝笔。”
密室中一片死寂。
司马昭先反应过来:“陈留郡的‘寒门’?这是什么意思?是指寒门学子吗?”
司马师摇头:“父亲,这可能是曹操留下的复仇手段。我们应该立即派人前往陈留,查明所谓‘寒门’究竟是何物,将其彻底铲除!”
司马懿沉默良久,枯瘦的手指轻轻摩挲着那只铜虎符。虎符做工精巧,却看不出有何特别之处。
“不,”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却坚定,“曹操多疑,这可能是疑兵之计。若我们大张旗鼓前往陈留,正好中了圈套。暂时按兵不动,加强皇宫守卫,监视所有曹氏宗亲即可。”
然而司马懿心中清楚,这绝非虚张声势。曹操的谋略他再了解不过——这位曾经的主公从不做无谓的布置。
那天夜里,司马懿独自一人站在庭院中,仰望星空。
他想起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赤壁大战前夜,也曾这样仰望星空。那时他作为曹操的谋士之一,亲眼见证了一代枭雄的兴衰起伏。
“曹公啊曹公,”司马懿喃喃自语,“你死后二十四年,还要与我下一盘棋吗?”
一阵寒风吹过,司马懿剧烈地咳嗽起来。他感到寿命已经不长,必须为司马家的未来扫清一切障碍。
第二天清晨,司马懿召来了最信任的暗探首领——影鸦。
“你带三个人,暗中前往陈留。”司马懿吩咐道,“查明所谓‘寒门’所指何物,但切勿打草惊蛇。有任何发现,立即回报。”
影鸦领命而去。
一个月后,影鸦带回的消息令司马懿困惑不已。
陈留郡并无名为“寒门”的组织或地点,但有一处废弃的铜矿,当地人称其为“寒门矿”,因矿洞中常年吹出阴冷之风而得名。该矿已于二十年前废弃,周围人烟稀少。
与此同时,司马懿安插在皇宫的眼线报告了一个异常现象:
少帝曹芳近日常常在深夜秘密召见一位老宦官,两人有时会在先帝曹操留下的那面“冰鉴”屏风前驻足良久。
“冰鉴”屏风是曹操生前最爱之物,由北海极冰玉制成,夏日可使整个殿堂凉爽如秋。屏风上雕刻着九州山川图,精美绝伦。
司马懿立即警觉起来。
他亲自入宫,以“天气渐热,借冰鉴屏风消暑”为由,要求将屏风移至司马府。
曹芳脸色苍白,却不敢拒绝。
屏风送至司马府那夜,司马懿屏退左右,独自审视这件艺术品。
他发现屏风上的雕刻似乎暗藏玄机——山川走向与实际地理略有出入,反而更像某种密文图案。
突然,他注意到屏风底部一行小字:“镜中花,水中月,寒门开,天命绝。”

司马懿猛地想起曹操生前最爱说的那句话:“用兵之道,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他立即唤来司马师和司马昭:“影鸦查到的寒门矿是假象!真正的‘寒门’可能指的就是这面屏风!曹操将秘密藏在了我们眼皮底下!”
就在司马懿说话的同时,他的手无意中按到了屏风上兖州的位置。
只听“咔哒”一声轻响,屏风背面弹出一个小巧暗格。
暗格中藏着一卷羊皮纸。
司马懿展开羊皮纸,上面是曹操的亲笔手书:
“司马仲达,若汝得见此信,则曹魏已危如累卵。余知汝才略,亦知汝野心。然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余纵横一生,杀人无数,然始终坚守一道底线:不使华夏覆灭于胡人之手。”
“余在时,已见北方鲜卑、匈奴、羌、氐诸部日渐强大。若中原内乱不休,必引狼入室,重蹈周朝犬戎之祸。故余虽知汝有不臣之心,仍留汝性命,唯望汝能护中原安宁。”
“然若汝子孙篡位自立,则必依此计:余已在北疆诸胡中散布消息,言司马氏得国不正,且暗中支持诸部独立。待司马氏篡位,诸胡必以为中原内乱,趁机南下。届时汝等将面临内外交困之局。”
“唯一破解之法:持余虎符,前往并州黑山,见一名为‘守墓人’者。唯有此人可化解北疆危机,保汝司马氏江山不失。”
司马懿读罢,手中羊皮纸微微颤抖。
第三章:答案与应验他终于明白了曹操的全盘谋划。
那位奸雄不仅预料到了司马家会篡权,甚至布下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局。
如果司马家安心做曹魏的臣子,那么这个后手永远不会启动。
一旦司马家篡位,就会触发北疆危机,而解决危机的钥匙,却掌握在曹操安排的“守墓人”手中。
“好一个曹孟德...”司马懿长叹一声,既有敬佩也有愤怒,“死后二十四年,还要将我司马氏置于你的棋局之中。”
司马昭急切道:“父亲,这可能是陷阱!所谓‘守墓人’或许是曹操留下的刺客!”
司马师却摇头:“曹操若想刺杀父亲,有的是机会。我看此计更深——他要的是父亲或者我们司马家的后人,去求他曹操留下的人救命。这样,司马家的江山,始终欠着他曹家的情。”
司马懿闭上双眼,沉思良久。
此时,门外急报:北部边境传来烽火,鲜卑部落大规模集结南下,兵力空前!
“果然来了...”司马懿睁开眼,目光如刀,“曹操的局已经开始。准备车马,我亲自前往黑山。”
“父亲不可!”司马昭急忙劝阻,“您年事已高,黑山地处偏远,舟车劳顿且风险难测!”
司马懿缓缓起身:“曹操了解我,正如我了解他。他既然布下此局,就料定我会亲自前往。因为我必须知道,他留下的到底是什么后手。”
十天后,司马懿的车驾抵达黑山脚下。
按照羊皮纸上的指示,他独自一人登上山顶。在那里,他见到了一座简陋的茅屋和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
老者正在院中打磨一面铜镜,见司马懿到来,并不惊讶,只是淡淡说道:“司马仲达,曹公等你很久了。”
司马懿凝视老者:“阁下就是‘守墓人’?”
老者点头:“我曾是曹公麾下谋士,名不足道。曹公于我有一命之恩,故答应为他守墓五十年,并完成最后嘱托。”
“曹操的墓在邺城,为何你在黑山?”
“曹公真正的智慧,不在墓中,在这里。”老者指向茅屋后方。
司马懿随老者转到屋后,看见了一座石碑,碑上刻着“汉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是曹操年轻时最初的梦想,不是称王称帝,而是做汉朝的征西将军,为国拓边。
老者缓缓道:“曹公一生最大遗憾,就是未能实现年轻时的理想。他知道天下三分非长久之计,北疆胡人才是华夏心腹大患。他更知道,无论曹家还是司马家,若只想着一家一姓之天下,终究会重蹈覆辙。”
司马懿沉默不语。

老者继续道:“曹公在北疆诸胡中散布的消息已经生效。鲜卑、匈奴等部认为中原内乱,正是南下良机。若不制止,不日将烽火连天。”
“你说曹操留下了解决之道?”
老者点头,从怀中取出一卷书简:“这是曹公毕生研究胡人部落的心得,包括各部的矛盾、弱点、可分化拉拢的势力。依此计行事,可让诸胡自相残杀,无力南下。”
司马懿接过书简,略一翻阅,心中震撼——这确实是化解北疆危机的无价之宝。
“代价是什么?”司马懿直接问道。
老者微笑:“曹公只有一个条件:司马氏篡位可以,但必须承诺三件事:第一,保全曹氏血脉,不绝祭祀;第二,统一天下后,须以华夏安宁为重,不只想着司马一家之权位;第三,将来若司马氏失德,也当效仿此法,让位于有德者。”
司马懿长叹一声:“曹公果然...至死都在下大棋。”
老者点头:“曹公曾说,天下如棋局,世人皆棋子。但他晚年明白,真正的高手不是棋手,而是愿为棋局牺牲的棋子。他希望你我能明白这个道理。”
带着复杂的心情,司马懿携书简返回洛阳。
依曹操之计,司马家族成功分化了北疆胡人部落,化解了危机。
次年,司马懿病逝,但司马家的基础已经稳固。十五年后,司马炎篡魏自立,建立晋朝,但遵守诺言,保全曹氏血脉,并最终统一天下。
然而司马家族并未完全吸取教训。晋武帝司马炎死后,皇族内斗激烈,引发八王之乱,最终导致五胡乱华,中原陆沉。
那时才有人回想起曹操的深谋远虑和司马懿最后的醒悟——一家一姓之私欲,终不敌天下大势之浩浩荡荡。
黑山上,守墓人望着陷入战火的中原,长叹一声:“棋局终了,未有胜者。”
风吹过墓碑,仿佛传来曹操的笑声——那笑声中有得意,有嘲讽,但最深处的,却是一种无人理解的孤独与悲凉。
天下如棋,人人自以为棋手,实则皆为棋子。唯有时间,才是永远的下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