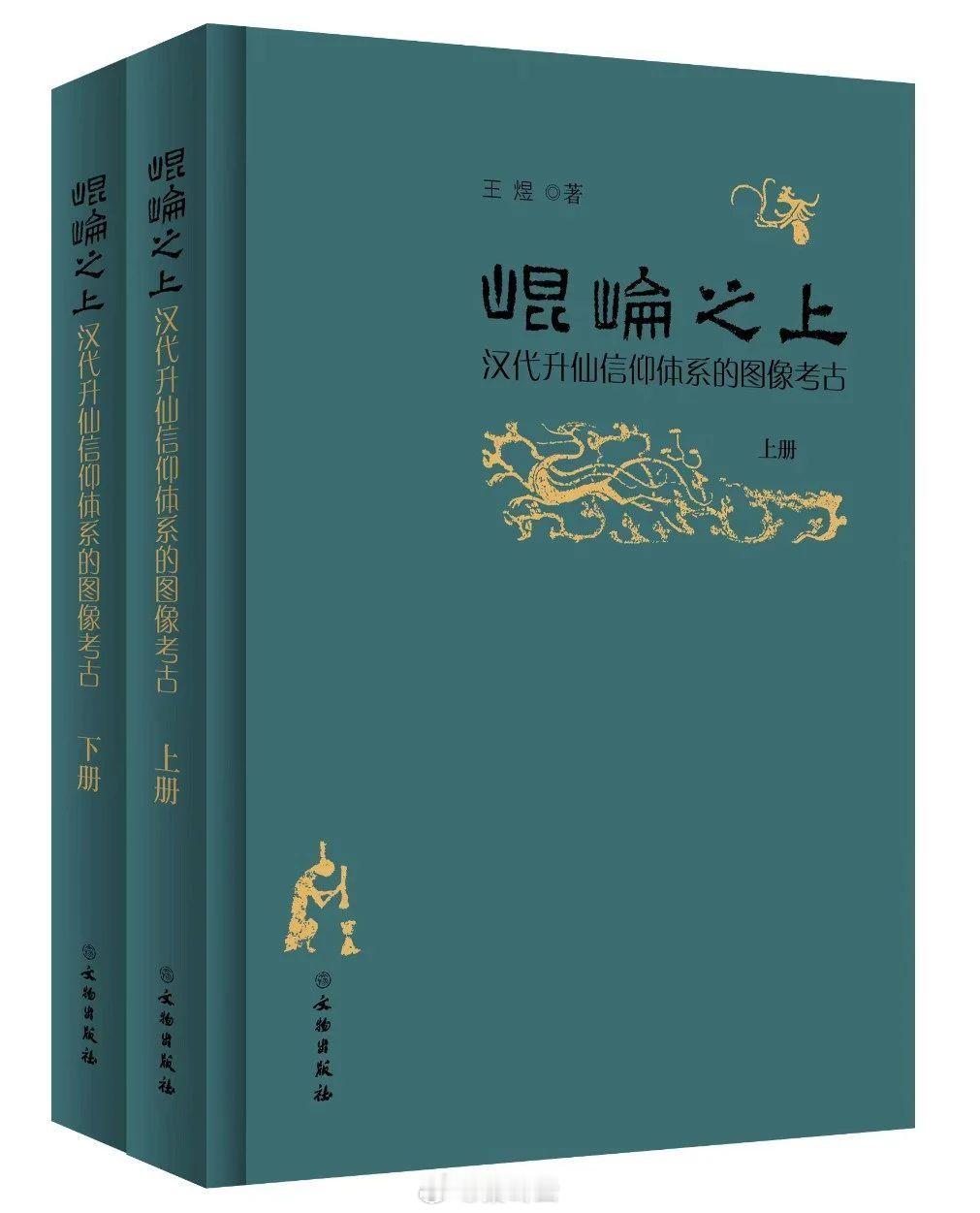【王煜:天上应有扬州鹤】
《殷芸小说·吴蜀人》中记: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
对于中国古代墓葬形制、图像、随葬品的理解,“事死如生”一词似乎是一把万能钥匙,随处可见,随处可用。它来源于儒家的丧葬观,《中庸》中已见其文。经常被学者引述的是《荀子·礼论》中的一段话:“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和安排,自然须得从现实出发,人的各种现实需求,自然也需延续到死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事死如生”或“大象其生”确实是丧葬文化的基础,尤其对于实用主义倾向强烈的中国人来说。不过,儒家并不是就这个意义来说的。他们是要极力为各种繁缛的礼(包括丧礼)找到应该继续践行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所以特别强调“事死如生”的层面。其实,就在《荀子·礼论》的这段话后面,不仅指出丧礼中“象生”的内容,还承认其中的“反生”的部分。即便如学者们经常举到的饭含,一方面确实是“缘生以事死,不忍虚其口”,但另一方面所用的生米、骨贝、玉石等显然并非生前所食。《礼记·檀弓下》解释说:“饭用米、贝,弗忍虚也。不以食道,用美尔焉。”后一句说得就颇含混。《荀子·礼论》中便说:“饭以生稻,含以槁骨,反生术也。”紧接着叙述了一大段“反生术”的例子,与叙述“象生术”的例子一样。所以王先谦注释到:“前说象其生也,此已下,说反于生之法也。”看来,清代学者尚有全面的认识,不知从何时开始,学界往往只强调其中“大象其生”的一面了。
确实,死者毕竟不同于生者,墓葬毕竟不同于居室。这不仅仅是由于其属性、形制、功能的差异,最重要的差别还在于,死亡作为一种终极性(或者是中止性)的消解,不仅消解了生前的所有,还消解了生前的所无。换句话说,消解了生前的各种局限,开辟出人们追求“幸福”的一片“新天地”。例如,上引《殷芸小说》中的“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对于生人来说恐怕只能是一句玩笑了。既然要去做扬州刺史,又如何能同时骑鹤飞升呢?扬州刺史并不能在天上做呀(后来倒是有个包拯,日判阳,夜判阴,人鬼通吃)。若说是骑鹤到扬州去做刺史,那只是旅途的神奇,不是终极超越的实现。但是,死后的官,就可以在天上做了,既是逍遥无待的神仙,又是紫袍玉带的大人。本书中会讨论到天仓的问题,汉墓题刻中就有“上食天仓”和“上食大(太)仓”两种说法,但说的其实是一回事儿。墓葬的愿望,至少从汉代以来,本质上应该是对死者、生者各种美好愿望(排场、安全、富贵、健康、繁衍、神仙等等)的综合。最流行的丧葬文化及其表现形式,必定是对这些愿望的聚合乃至整合。
《殷芸小说》中的这一段,记在题目《吴蜀人》之下,其中记的确实皆为吴、蜀人物之事,恐怕这一谈资说的也是吴、蜀之人吧。这让人想到了蜀地汉墓中的摇钱树。树座、枝叶图像的主体是昆仑、西王母、天门等,枝叶下挂满钱币,有的钱币上写着“利后”,巧妙地将神仙、富贵和繁衍、生人福祉的愿望整合在一起,当然整体来看,主体还是神仙。吴地的魂瓶恐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粮仓、田池、楼宇、神仙等)。其实,墓葬图像流行的各大地区无不如此。只是将这几种主要愿望完美整合在一种器物上的,还得是说出“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吴蜀人”。
读者想必已经了解到,我们对于墓葬文化,具体到本书主要是汉墓图像,是持一种多元性、综合性的态度,反对那种仅仅把它们归结到一个层面、某个核心的观点,不论是生前映射、死后继续,还是成神成仙,或是经义道德。不仅是多元,甚至不排除矛盾。例如,汉武帝一方面极力寻求神仙、不死药,同时又营造了规模宏大的陵墓。张衡在《西京赋》中铺排了武帝求仙的盛况后,转头就质问到:“若历世而长存,何遽营乎陵墓?”墓葬中追求的愿望,内容是理想主义的,但态度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所以我们在讨论至少汉代以来的墓葬文化时,例如哪里属“死”、哪里属“生”,哪里属“魄”、哪里属“魂”,什么是“藏”、什么是“现”,什么是“祭”、什么是“奠”,这样的概念问题,尽量少纠结,终究是剪不断、理还乱。读者试看本书中所引用的提到魂、魄的文献,除了那些本身就要一本正经地区别二者的(其实也有他们另一个实用的目的),其他的就语气、音韵、习惯上的选择,实在要比二者本身的区别来得重要。
墓葬文化本身是多元的、矛盾的,但现代学术研究显然必须以一个个合乎理性的问题为中心,方能成立,方可深入。而且做文章也须得有主旨,始终围绕,才不堕平庸。所谓“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本书即是针对其中神仙的问题(一个方面的问题),而且是内容较成系统的升仙思想和信仰的问题(合乎理性)。且神仙信仰是秦汉时期思想观念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更是当时墓葬文化中的核心之一,甚至侵染到国家陵墓典礼中。汉乐府中现存一篇《上陵》古辞(上陵何美美),属鼓吹曲辞,郭茂倩《题解》认为即与东汉上陵礼有关,并注意到其“古辞大略言神仙事”。如“芝为车,龙为马,览遨游,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仙人下来饮,延寿千万岁。”神仙信仰当然是理解汉代墓葬文化的一个关键抓手。
左思《蜀都赋》中说:“一经神怪,一纬人理。”蜀人以神怪为经,人理为纬。所谓“人理”,魏晋时的语境我不清楚,大概是人情物理的泛称。在宋代蜀学的语境中,则更强调“人情”。我,蜀人也。在以初入殿堂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第一部集腋成裘的著述上,以神仙问题为主旨,而所谓的系统问题,其实皆本自人理、人情(读者自见),也算遥契古人吧。
最后,开头的那则小说成了诗词中的典故。蜀人苏轼说:
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看来东坡先生的观点和我一致,在“世间”是不能兼得扬州刺史和骑鹤飞升的。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鱼与熊掌,字面上看还都是“肉”,东坡先生则要放弃他钟情的“东坡肉”,选择一个精神上的“竹”(当然孟子的熊掌也是精神上的“义”)。竹是空虚的、清高的、冷峻的,但他认为可以免俗。本书也放弃了那么多所谓事死如生的现实的内容,选择了这么一个虚无的、高渺的、奇幻的主题,既然世间没有“扬州鹤”,不妨去天上寻寻呢?两位天上的谪仙人,两位蜀人,李白和苏轼,应该会心莞尔吧(李白出生地仍有争议,但他实实在在生长蜀地二十年,度过了整个成长时期,青年出川入楚,称为蜀人应无不妥)。
话到此处,前言的内容本已说尽,但这个话题之题外,不知怎地又使我心有戚戚焉。东坡先生说“扬州鹤”之弦外,扬州刺史不言自明,鹤还不是升仙,而是如同神仙一般的自由和超脱。“肉”和“竹”的选择,虽然他自己说“旁人笑此言”,但至少在表明立场上,士大夫应该颇能一致。但是,在扬州刺史与骑鹤飞升之间,他选择哪一个呢?俯仰圣贤之书,周旋营苟之务,士大夫的所谓“出处”心理是特别矛盾的。笔者虽非贤士大夫,也无彭泽之任,尚心有悸悸然。至少在黄州时期,他这样写到: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本文系王煜《昆仑之上:汉代升仙信仰体系的图像考古》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