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在1945-1947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发表过一次演讲,主题是自由意志,这是维特根斯坦为数不多的几次深入探讨这个课题的时候。他认为哲学辩论往往是由于双方对概念和语言的误解而产生的。通过揭示这些误解,维特根斯坦试图使双方意识到他们的争论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了解维特根斯坦的见解是如何引导我们走上一条确定自由意志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意识是拥有自由意志的必要因素的道路。

维特根斯坦首先反驳了物理决定论对自由意志的否定,即因果关系是不可改变的观点。
他认为,自然法则是人类对现实的描述,而不是让宇宙遵循这些法则的原因。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法则是否会被打破。在1919年之前,所有的行星和恒星都被认为遵循牛顿引力定律,但在那之后,我们知道了爱因斯坦的理论可以描述牛顿定律失效的情况。然而,这两者都只是描述。我们不知道真正的自然法则是什么。
当我们说决定论的时候,我们是在把我们理解的物理定律(比如一块石头下落的轨迹)与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比如人类的意志或大脑)进行类比。尽管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关于大脑的知识,但我们仍然无法预测一个人会做什么,所以我们没有逻辑依据来相信人类是决定论的。
自由意志不是一个客观的、形而上的现实,而是一个我们赋予人类而非事物的形容词。
类比另一个形而上概念——数字,如果我有一桶水,我可以说我有3个水吗?水具有3的属性吗?这个说法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不说我们有3个水,我们说我们有3升水。然而,升这个单位是任意的,它是人为设定的,用来测量容量或体积。但这个单位本身并没有固有的、普遍的意义。它是为了方便度量和交流而设定的一个标准。
同样地,自由意志这个概念在描述下落的石头时可能不适用,因为石头不具备自主决策的能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将自由意志这个概念应用于人类,因为人类具有意识和决策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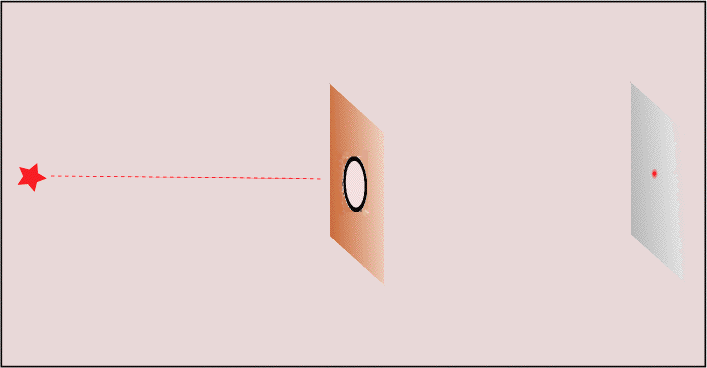
然而,尽管水分子可以具有3这个属性,如果我们对宇宙了解得足够多,以至于可以预测一个人所做的一切,我们也可以进行类比。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预测人类行为),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量子物理保证了宇宙的不可预测性。宇宙中的每一个物体都是由粒子组成的,我们知道这些粒子遵循量子定律。这意味着,无论我们认为用于预测下落石头的模型有多精确,它们永远会有偏差。现实是根本无法预测的。
接下来你会遇到混沌理论。
混沌理论告诉我们,混沌过程(如三体运动,或天气模型)与量子过程一样难以预测,尽管与量子测量不同的是,它们是确定的。即使知道它们是确定的也没用,因为我们永远无法以足够的精度知道它未来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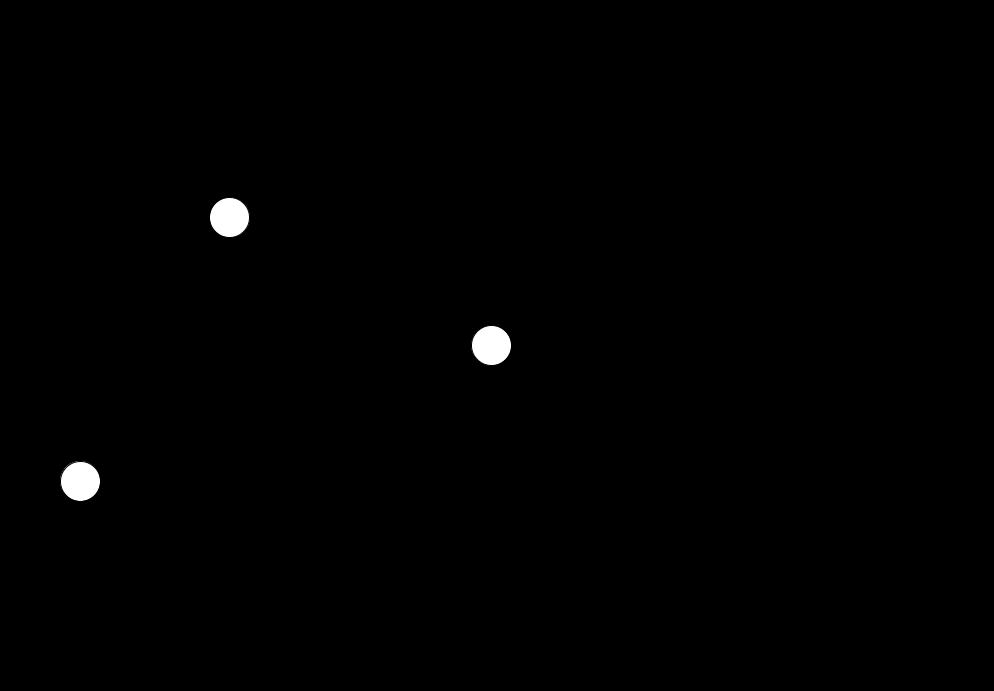
即使我们对人类了解得越来越多,并拥有越来越聪明的算法,我们也只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预测人们的行为,然后这些预测仍然是带有概率的猜测,就像天气预报一样。
不可预测性使我们推断人们通常具有自由意志,但有一些观察可以让我们相信人们没有自由意志。
一个案例
考虑一个人突然性格改变的案例。他从一个守法的人变成了一个犯罪分子。他不断地猥亵女性,最终因流氓罪而被捕。这给人的印象是他有自由意志。我们认为是他选择这样做。
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所有人重新评估他是否在自主行动。
当他即将被送回监狱时,发现他的新皮质上有一个巨大的生长物。他被送到医院接受手术。手术切除生长物后,他恢复了过去守法的自己。然后生长物又长回来了,他又变成了歹徒,不得不再次切除。瞬间,他又变成了好公民。
我们知道,新皮质负责抑制冲动行为。这是人类行为表现得像人而不是野兽的原因。所以,知道他的行为有医学原因,他的意志就不再被认为是自由的。他的行为不再是他的责任。
然而,如果我们相信大脑本身受到因果律的约束,那么这和大脑的正常运作有什么不同呢?在手术前后,他的自由程度有何不同?
需要领会的关键见解是,自由意志辩论本身并非形而上学的,而是心理学的。它是我们如何将道德推理归因于他人和我们自己。
当我们试图将自由意志辩论变成一个形而上学问题时,它变得混乱且无法解决,就像3这个数字是否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存在一样。这个问题本身毫无意义,因为数字3在我们的语言中是形容词,它在语言之外没有意义。
我们人类将语言视为一种工具,用以分享信息,但这种分享更像是一种游戏。那么,当人们使用“自由意志”这个词时,他们是如何使用它的呢?主要是在执行正义时使用,所以当我们问某人是否拥有自由意志时,我们想知道的是普通人是否认为他们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事实证明,确定一个人是否拥有自由意志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例如一个人的心智能力以及他们是否受到胁迫等。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一个人有或没有自由意志,因为这是一个多层面的问题。
即使有些人声称他们不相信自由意志,他们在谈论和思考意志时仍然会表现得好像意志是自由的。这是因为语言的使用方式使我们很难完全摆脱这种观念。实际上,我们使用语言来讨论意志和自由意志的方式是根深蒂固的,以至于即使我们试图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我们仍然会不自觉地以这种方式来谈论和思考它。
如果你明白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只是关于语义的无用争论,那么它可以帮助你在不诉诸更多形而上学的情况下解决最有争议的辩论,并解决真正的问题。

例如,神经科学家本杰明·利伯特进行了一些实验,他要求人们在大脑受到MRI机器观察时做出决策,以了解人们是在有意识地做出这些决策。当参与者根据自己的决定以特定方式移动手时,他们的大脑中负责移动手的部分在他们意识到自己做出决策之前就已经活跃起来。换句话说,大脑在我们意识到自己做出决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行动的准备。
这个发现引发了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因为它表明我们的意识似乎在决策过程中起到了较小的作用。一些生物决定论者据此得出结论,认为人类没有自由意志,因为我们的决策在我们意识到它们之前就已经被决定了。然而,这个观点在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意识不一定是做出自由决策的唯一条件。
假设你重复这个实验,但不是让人们根据某种游戏规则移动手,而是对即将犯下谋杀罪的人进行。想象一下,当一个人决定扣动扳机开枪射杀某人时,可以对他们的大脑进行MRI扫描。假设MRI显示在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前,开火的冲动就已经出现了。

那么我们会说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吗?他们应该被免罪吗?
普通人会说他们是负责任的,这是因为关于自由意志的语言是如何运作的。在我们理解正义的方式中,如果你扣动扳机射杀某人,而且被认为具有道德判断能力,并且没有被强迫去做,那么你就是负责任的。
这并不意味着意识与此无关。如果我们用机器取代扣动扳机的人,我们不会让机器承担责任。我们会让设计它的人负责,因为机器没有意识。
知道决策产生的自然过程以及它起始于大脑的无意识部分,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就像不应该承担责任的机器。
问题在于意识并没有扮演我们认为的角色。我们希望意识能做出决策,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意识为这些决策承担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做出决策时意识到的事物。
如果一个梦游者在睡梦中犯罪,我们不会认为这个人应该承担责任。这是因为他们是无意识的吗?梦游者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有意识的,因为他们正在经历一种心理体验,比如梦境或噩梦。我们不会让他们承担责任,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就像一个产生幻觉的人。那个人也是有意识的,但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处情境的现实。因此,他们意识的事实与他们行动的自由无关。

奇怪的是,似乎当有人被愚弄成相信不真实的事情时,意志并不自由。例如,也许我的生活就像吉姆·凯瑞主演的电影《楚门的世界》那样精心策划的骗局。尽管在现实语境中我的意志是自由的,但如果我的行为在那个幻觉之外产生了后果,我就不需要对我的行为承担责任。我只能对我意识到的事物承担责任。
回到神经影像研究,现在问题变得更有意义了。自由意志与在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无关,而是在事后对所做决策承担责任。实际的决策过程可能是在我们的无意识中进行的。当实验参与者根据指示移动他们的手时,他们可以为手的运动承担责任,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过程。因为他们明白正在执行的任务,所以他们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至于决策是如何形成的并不重要。

因此,意识心智并不是大脑中负责决策的全部部分。它只是起到领导作用,类似于约翰·海特在《幸福假说》一书中提到的骑象人。无意识心智就是大象。尽管大象有自己的想法,骑象人还是要对它的行为负责。如果大象发狂作乱,骑象人必须赔偿损失。因此,骑象人的自由意志才是重要的。大象的意志无关紧要。
在现代哲学中,人们很容易陷入一种将人与机器相提并论的思维方式,过分关注决定论(即一切都是预定的、必然发生的)。在这种观点下,意识被看作是机器中的一部分,好像它对于决策过程并无太大影响。然而,在启蒙运动之前,人们对自由意志的理解并不是关注决策能力,而是关注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为其行为承担责任。这意味着,古代的人们意识到,即使我们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仍然需要为这些行为承担责任。

王大勇
利害关系决定自由意志,即因果关系是不可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