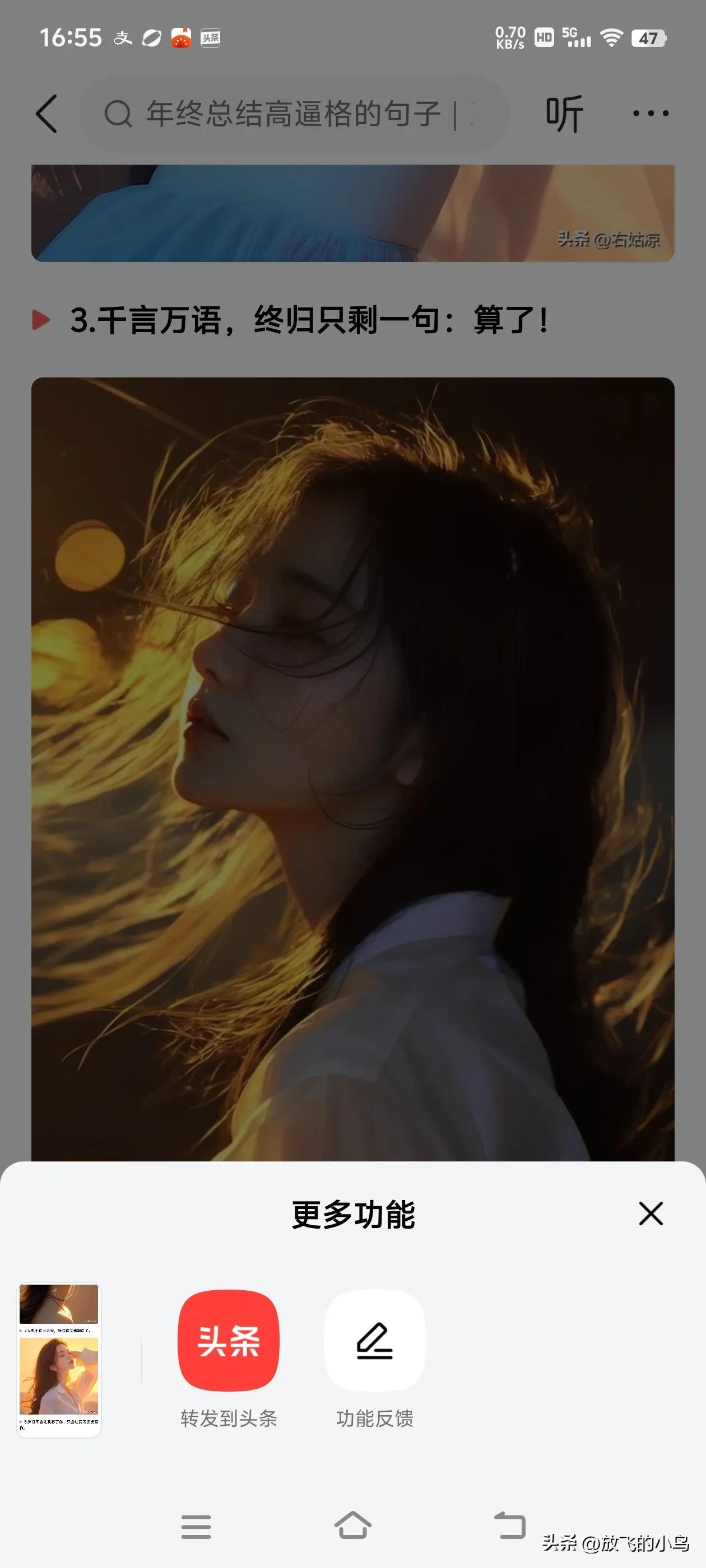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常扪心自问。 当老师时,太调皮,是最不像老师的老师。先不说能传授学生多少知识,就我那性格,当年的杨校长水是烟波横,山是眉峰聚。他瞅我,绝对是恨铁不成钢,后悔得咬断后槽牙。 我爬树,还教学生学习爬树掏鸟摘山果,从学校门口到办公室有很长一段路,路两旁种的是大杨树,树叶中间时不时露个黑腿腿,有猴子扮个鬼脸,不用问,是张小宇的猴子们。 杨校长仰着头骂:都滚下来。 猴子们扮鬼脸:不下不下就不下,山药地里逮蚂蚱,杨校长少瞎喳喳。 杨校长恼了:好,全是张小宇的错,我开除张小宇那个祸。 猴子们哧溜哧溜连滚带爬出溜到杨校长跟前:不许开除我们张老师,要杀要剐随便,头掉了,碗大的疤,十三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一伙二百五,让阴诡的杨校长一诈唬,就犯浑,杨校长照着猴子们的屁股一人一脚,都灰溜溜滚蛋了,边跑边扭头伸着舌头略略略。 杨校长提着我耳朵根教育:瞧瞧你,怎么教学生的,一群小土匪。 这话说的,有我这么好看的女土匪头子嘛。 杨校长气得损我: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你一个小女孩,脸皮这么厚,城墙上的土抹上去的,二寸长的刀子刮不塌。 我脸皮厚,玩得转。脸皮薄,靠边站。 我一个数学老师教学生数来宝,打快板,时不时来一段:学校领兵杨大帅,杨大帅真气派,教学改革出风彩…… 猴子们学啥啥不行,玩数来宝第一名,走着站着也来一段:太阳上工节节高,听我表一表懒大嫂,懒大嫂她懒的好,起得迟来睡得早…… 后来我怂恿校长开展才艺课吧,不能委屈了咱们这戏曲之乡。校长手托着下巴,想了又想,一拍桌子:搞它! 翠翠挂帅,小宇是先锋官,一马当先,干就得了,费劲不?太费劲了,一分钱补助没有,我爬树的腿,孔明的嘴,为开展活动流血流汗,从没喊过累。 我在杨校长手下干过四年辅导员,给镇里策划过无数次活动,没挣过一分补助,没听过一句表扬。屁颠屁颠的,差点跑断腿。杨校长是个面点师,天天画饼给我充饥。 后来我明白了他的套路,仍然往前冲,指哪儿打哪儿。我明白自己的定位:我就是一个零钱罐,千万不敢把自己当ATM机,希望渺小,失望没有。 我算不算合格的数学老师,起初不是,后来自创了一套新的教学思路,被大力推广过,优秀算不上,最起码及格线过了吧。 可头条上许多朋友怀疑我数学老师的身份,从4月份我有一篇爆款文章起,一直有人怀疑,你是数学老师吗?吹吧,语文老师吧。 我不停地辩解,不停地嘚嘚嘚,结果大部分人不相信。后来我就懒得解释了。 张小宇喜欢语文,却从未尝试过教语文,没信心。万丈高楼平地起,不行先得打根基。 就我这脑袋瓜,就我这根基打的,我哪敢诗词歌赋,连横平竖直都教不明白,平舌音翘舌音分不清,前鼻音后鼻音分不清,我敢祸害祖国的下一代,就等着家长问候我十八辈祖宗吧。 我上小学时,是差生。老师们眼中的鬼见愁。我一个小土豆,按个子高低排座位的话,我应该做第一二排,因为本黄毛丫头学习不好,我被老师扔在最后一排,靠着炭仓。一抹一手黑,上课不好好听讲,趴着桌子上睡觉,黑手手往脸上一蹭,再抹一脸黑。 老师们嫌弃我,上课从不提问我,我顽皮,手举得高高的,大声起哄:老师,我! 被老师火眼金睛发现一回,张小宇,你来回答。 我兴奋地站起来,脑子里一片空白,坏了,一激动,答案忘了。 老师认为我不老实,虎着脸拿起教鞭打我手心,手心瞬间肿起,青一道紫一道,疼的拿不了筷子。 老师讲语文,我头发昏。老师讲数学,我一头懵。 考试是最头疼的事儿,两门加起来没超出二十分,挨板子是家常便饭,老师打完,手肿脸肿,像发面馒头。 回家我妈打,我妈打我用鸡毛掸子,脱下鞋用鞋底子,满眼的厉光,在我脸上边打边诅咒。 后来我为了逃避挨打,考试前装肚子疼,蒙混过关,这一招耍得不错。后来不想上课,我假装肚子疼,窝着腰,手拄着肚,皱着眉长一声短一声哎哟,哎哟。 老师本就不想看我,借着病快滚吧,我背上书包逃出教室门的那一刻,我从眼角余光中打量到老师的如释负重,在老师眼里,我是一泡狗屎。 就我这么个学生,五年级遇上了张老师,我被打通了任督二脉,瞬间开窍,渣渣变面包。 我这点语文知识,是空中楼阁,华而不实,我要能当语文老师,恐龙都能再横行一个世纪。 我当老师,特别热爱那份事业,我喜欢并执着,可惜天不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