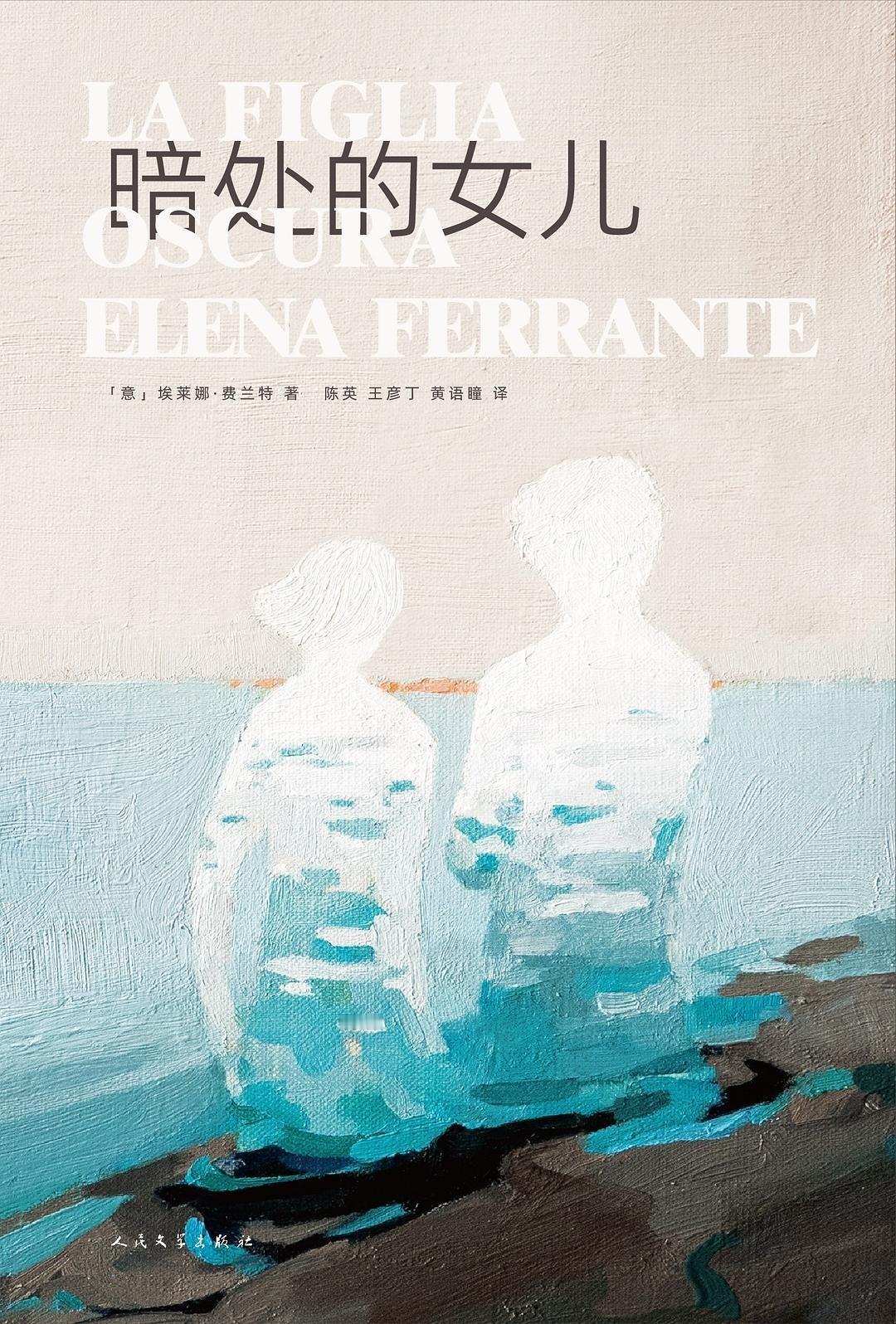时代在变,女性在变,进击的她们试图把传统与永恒甩在身后,但有些东西,她们终究逃不开躲不掉,那是爱——母爱,那是痛——女性之痛,埃莱娜·费兰特和她的《暗处的女儿》如是说。 春日荐片季 读书
·这或许是大多数女性之痛,成为母亲,人生就加了一块可见的天花板,我身边遍布这样的女人。
在与尼娜、埃莱娜母女相遇后,主人公勒达的海边假期悄然变为人生的回溯。第一次见到尼娜,勒达觉得,她是家族里的另类,是个神秘的存在,从那时起,勒达会不时望向她们,直至成为习惯。
“家族里的另类”,这是18岁之前的勒达一直想要成为的女人,她不要和母亲、外婆一样被困在世界的角落,所以当她18岁终于离开原生家庭,前往佛罗伦萨求学时,她说,我第一次开始喜欢自己。而这个女人,因为容貌与气质的超然,让勒达觉得,她或许也在准备逃离,与当年的自己一样,她以目光的在场,旁观并试图捕捉这场奔逃。
但,尼娜与女儿埃莱娜的亲昵与甜蜜,将前者牢牢拴在家庭内,勒达嫉妒不安着,在一次次望向她们的眼神中,勒达三年零三十六天的出走如同黑洞,将现实与过往统统卷入。
勒达曾因一个叫做布兰达的女人,而心生出走的念头。布兰达在汽车上对勒达下达“神谕”,“我们从小就不得不做很多蠢事,还以为那是都是必须的,但我现在做的,是自出生以来我觉得唯一有意的事”,布兰达口中有意义的事,是指离开年轻的丈夫与另一个离开妻儿的男人,寻获自由、释放欲望。布兰达,是一个出走的女人。
与其说,勒达遵从内心,不如说是布兰达在恰好的时间出现,带着恰好的自己,给勒达恰好的引导。勒达出走了,丢下两个年幼的女儿,去“新世界”玩了三年零三十六天。在勒达出走前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一个被困在母爱中的女人,至少当时的勒达是这么想的——母爱困住了她,一并困住的,还有她的事业、她的欲望、她的可能,这或许是大多数女性之痛,成为母亲,人生就加了一块可见的天花板,我身边遍布这样的女人。
·母亲是身份,但,母爱需要生命灌溉。
勒达又回来了,关于原因,她说,“因为我意识到,无法创造出任何东西,能与两个孩子相提并论”,然后她选择妥协,少为自己活,多为两个女儿着想,直到成为习惯。勒达说出的前半句,因为抽象而显得不真实,我觉得这更接近于“母爱”,是本能的选择,这也是现实中众多出走的女人的归因,因为孩子,因为那个剪断却依然连接的脐带。
这些是勒达以出走获取的人生经验和生命体悟,她该如何传递给尼娜,是促成她的出走和当年的自己一样,还是归于母爱与现在的自己一般?一把钥匙成了勒达为尼娜作出的引领。这时候,那个洋娃娃娜尼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勒达在关键时候将娜尼归还尼娜,直接斩断了她与尼娜的这种连接,并以娜尼归来的方式,让尼娜和女儿埃莱娜成为初见时的幸福母女,兜了一圈,看似回到原点,但尼娜却因为勒达,完成了出走、归来,不用付出三年零三十六天的代价,勒达,替尼娜作出抉择。
结尾,勒达对女儿们说,“我死了,但我很好”。前一个“我”,是指那个曾经追逐自我的勒达;后一个“我”,是指母亲身份的“勒达”,这种对于母亲身份的接受,多了一份坦然,她不是在呼吁女性回归家庭,而是对女性母亲身份的另类解读,她生来就有,但更需生命灌溉。至于男人们,作者埃莱娜认为他们不好不坏,一直就那样,希望不在他们身上,始终都在女人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