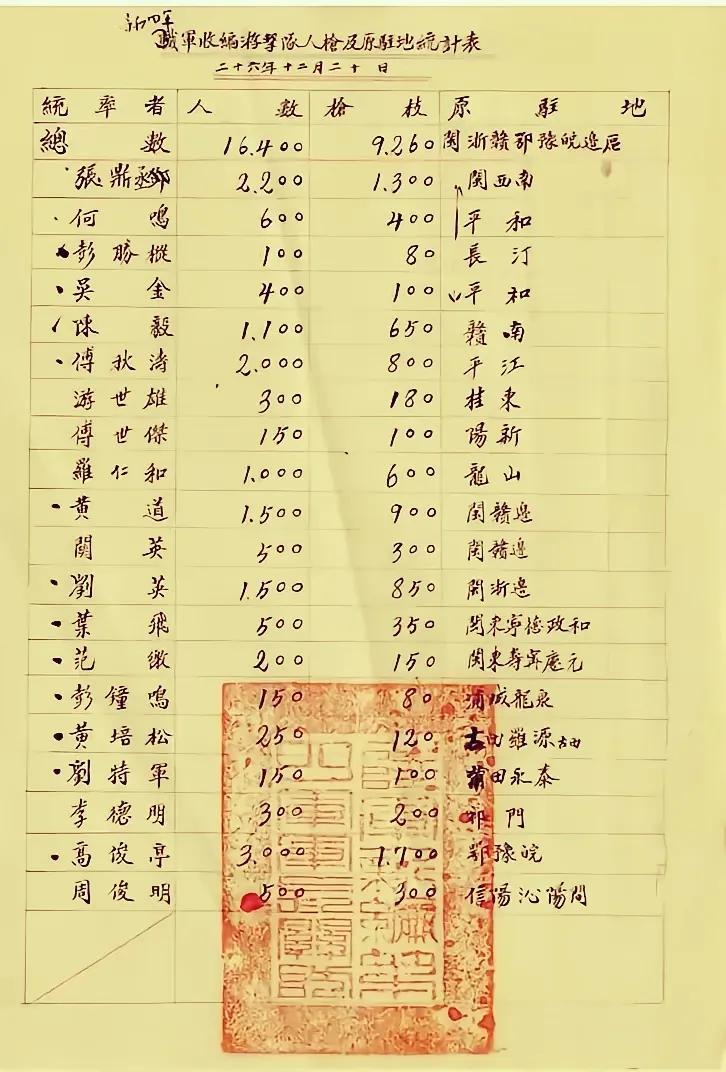阎明复:批斗大会
1966年8月4日前后,在中直礼堂举行了批斗原中办副主任龚子荣、原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原中央档案馆馆长兼中办副主任曾三、原中直管理局局长邓典桃的大会。会上有十几个“革命派”登台揭批,嗓门大,内容空,千篇一律,不记得他们叫喊了些什么了。但有一个“革命派”的发言却令我至今还能回忆起来。
这位“仁兄”揭发邓典桃用黄羊肉和大豆腐蚀和收买革命干部。原来,三年困难时期,人人忍饥挨饿,连我们中办机关的普通干部都不能幸免。大家真心实意地响应号召,自愿把自己每个月的口粮标准降到二十斤左右,很少吃到肉食,不少同志得了浮肿病。为了稍稍改善中办系统干部的生活,邓典桃派后勤机关的同志,冒着严寒,不辞辛苦到内蒙古大草原上去猎捕野黄羊,发给机关每个人二三斤黄羊肉。秋收的时候,还派人到江西的农村帮助老乡收割黄豆,然后购买一些运到北京,发给大家,以缓解当时的困难。我也曾分得这些食品,自己舍不得吃,而留给孩子放假回来稍微改善一下生活。我记得,当时机关的同志说起邓典桃和后勤部门同志的这些善举,都十分感激。然而现在,在批斗大会上这竟被说成是腐蚀革命干部,收买革命干部。我不知道,中办有哪位干部因为吃下这几斤野黄羊肉而被邓典桃腐蚀拉拢?只因为吃下了几斤江西老区的黄豆而被邓典桃收买? “文革” 对“真、善、美”的扭曲,竟然使一些人堕落到这样忘恩负义的可悲地步。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每个单位的“革命派”代表在发言中都点名批判一大批他们机关的“黑帮”,被点到的人都要站起来,低头认罪。中办秘书室的“革命派”在揭发中,点了他们单位的所谓田家英的爪牙,不知道为什么也点了我的名,可能因为秘书室的“革命派”“越位”了吧。我当即站了起来,坐在我后边的我们后楼的“革命派”却扯了扯我的衣服,又叫我坐下来了,后楼“革命派”的小小举动至今记忆犹新。
1966年8月27日,我们这些“黑帮”被带到天安门广场南侧的人民银行,在礼堂里召开了批斗原中办副主任兼国家机关党委书记龚子荣的大会。中办原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后来调到银行政治部任副主任,也被拉到大会上陪斗。批斗大会上,强加给龚老的“罪名”是为“黑五类”翻案。原来,当年龚老主持国家机关党委工作的时候,根据当时中央的精神,为金融系统历次运动中遭到迫害的同志进行了甄别。批斗大会上,银行系统的“革命派”对这位年逾半百的革命前辈进行了令人发指的肉体摧残。两个彪形大汉时不时地恶狠狠地摁着龚老的头,勒令龚老“低头认罪”,使劲地把龚老的双臂向身后扭,强迫龚老“坐喷气式”,还有人跳上台去对龚老拳打脚踢。这简直是反革命还乡团对老革命的“反攻倒算”!
还有一次,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学习班的“革命派”押着我们这些“黑帮”到京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参加批斗原中办副主任、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的大会。批斗大会上,一些“革命派”诬陷曾三“里通苏修”,他们声嘶力竭地批判和揭发,真令我感到又可笑又可悲。他们说,曾三把档案馆保存的中共早年的刊物交给了苏修分子郭绍棠。是什么刊物呢?是当年公开发行的 《新青年》。是擅自送的吗?不是。是根据中办主任杨尚昆的指示。
原来,郭绍棠是20年代的中共党员,后来到苏联学习,与杨尚昆同学,以后他留在苏联工作了。 50年代,郭绍棠回国探亲访友。杨尚昆接见他时,他提出希望能找到20年代中共出版的一些刊物。杨尚昆就请曾三帮助找几本。这就是全部事实。这些当年公开出版的刊物竟然成了“里通苏修”的“罪证”,岂不太可笑了吗!
“革命派”不择手段诬陷这位参加过长征、在党的机要档案战线上功勋卓著的老前辈岂不太可悲了吗!在批斗会场外,吃午饭的当儿,学习班四支部的“革命派”,逼迫我交代“里通苏修”的罪行,说要拒不交代,等待我的就是曾三的下场。
另外一次批斗大会,就是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批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大会。我坐在离主席台较远的地方,看不太清楚那里发生的事情。但我仍然记得,整个会场杀气腾腾,“打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批斗大会开始时,两个大汉押着彭真上场,接着是两人抬着一个大筐,筐里有一个人,到台中央抬筐的人使劲地连人带筐扔在地下。原来坐在筐里的就是遭受迫害双腿残废的罗瑞卿。接着被押上来的就是陆定一和杨尚昆。在声嘶力竭的“批判”、震耳欲聋的叫骂“低头认罪”的口号声中,大汉们长时间地向后扭着革命前辈们的双臂,迫使他们“坐喷气式”,时不时地拳打脚踢。我实在无法看下去了,就向“革命派”报告要上厕所。他们派原中办翻译组我组里的一位同事押我去厕所,途中我忍不住问了一句,是不是每次“批斗”都是这样。结果这句话惹祸了,那位同事“揭发”了我。回到学习班后,“革命派”对我进行了严厉的警告,说这是革命群众对“三反分子”的革命义愤,绝不能怜悯这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你要同他们划清界限,交代自己的“罪行”,等等。
注:阎明复,阎宝航之子,官至政协第七届副主席。涨姿势历史上的浪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