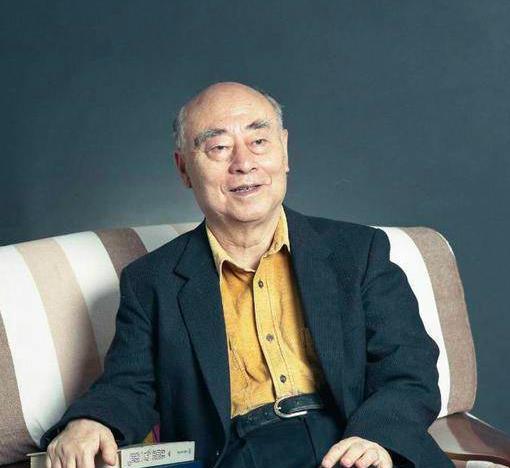1965年12月的一天傍晚,于敏在食堂排队打饭时,突然激动地抓住同事杜祥琬的胳膊:“快看!这个方程的解法对了!” 华东计算所门口的梧桐叶已经落了一地,屋里还亮着通宵灯。 那年头,上海人习惯叫这个地方“华算所”,但真正知道这帮人干嘛的,没几个。 于敏带队来了,带着一个目标——搞清氢弹。 不是理论猜测,不是纸上谈兵,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脑子,把那个连苏联人,都讳莫如深的东西算出来。 全所只有一台主机,J501,运算速度每秒5万次,这在60年代看是宝贝,但要拿来跑热核反应这种复杂模拟,差不多是用小马拉战车。 队伍没退,算盘上桌了,一张桌子堆满稿纸和算盘珠子,白天人挤人轮着上机,晚上两班倒。 有时为了等一个运算结果,全屋人只能靠墙坐,闭眼强憋十分钟的觉。 会战叫“百日会战”,但没人真以为一百天能破题。 问题卡在了热核燃烧的稳定性。 每多一步,就多一组非线性方程,变量多,边界条件死板,所有人像在沼泽地里推车,越推越沉。 于敏习惯不吭声,喜欢站在窗口抽烟,烟头烧到手都不动一下。 12月的某天午休,所里食堂油烟呛人,于敏没吃饭,抱着笔记坐在食堂靠墙的桌角,又开始反复推导一个临界条件的问题。 眼神像刀刃一样刻在纸上,忽然间,灵光一闪,他猛地站起来,把碗筷推开,把纸平摊在饭桌上。 “自持燃烧的条件不在压强跃变,在辐射流体本身的能量反馈!” 这句话当时没人听见,现场只有几个食堂工人抬头望了一眼。 于敏顾不上,抄起纸就往打饭口冲,排在他前面的是杜祥琬。于敏把纸往杜手里一塞,说:“你看看这组解!” 杜一低头看公式,抬头就见于敏冻得通红的手还在颤,嘴角微微咧着,像捡着宝。 饭没打,饭盆忘了,草稿纸揣进棉袄,整个人像进了另一个频道。 晚上那组方程重新上机跑,J501卡了半小时,打出第一批数据。 核燃烧温度与时间曲线终于稳定,没有爆震崩溃。 全屋静了一秒,接着有人喊了一句:“跑通了!”没人鼓掌,没人欢呼,所有人站着没动,几个人眼圈红了。 这一组解不是终点,却是打开氢弹原理大门的那把钥匙。 中国第一套完整构型的理论骨架,就这样在食堂的油迹纸上写出来了。 这个突破,后来被命名为“于敏方程”,支撑了之后被称为“于敏结构”的热核构型。 美国那边搞的是“泰勒-乌拉姆”方案,层层嵌套结构复杂;中国这套结构简洁、实战化强,体积和能量密度比美方更高,直到现在,世界上没人能破。 1966年12月28日,中国第一次氢弹原理试验成功。 没有外援、没有样板,纯靠一纸理论和几台落后设备算出来的。 半年后,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响起一声巨响,中国氢弹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爆,只用了2年8个月。 试验成功那天,邓稼先没睡,他一直在现场等消息。 其实于敏早在之前用“打松鼠”的暗号通知过他:解开了,两人说话不多,但彼此一听语气就知道情况。 邓稼先一得到消息,马上领队支援,后勤、结构、试验一气呵成。 这种默契,没有会议,没有文件,靠的是信与命。 于敏拒绝“氢弹之父”这个称号。 1966年他曾在一次会后被悄悄叫去拍照,拍完就消失了,他不准报道、不登刊物,连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哪。 直到1988年,这个名字才第一次以“国家有功人员”身份被公开,此前28年,无名无姓。 有一次庆功宴上,他突然用苏州话背起了《后出师表》。 整段背完,屋里静得能听见筷子碰盘子的声音。 科学不是冷的,人心是热的,于敏这辈子没上过战场,但打过最硬的一仗。 他没说过要“为国争光”,也不讲牺牲奉献,但从氢弹出图纸那天起,就没回头路。 身边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他还坐在那个老式计算器前,边翻公式边写草稿。 有人问他:“你图什么?”他没回答,桌上放着一张照片,是一个穿棉袄的女孩,抱着算盘打盹。 她是老同事走时留下的女儿,没人照顾,就送到办公室。 于敏一边工作一边照看,日复一日,这就是他信的东西——人得活下去,要安全,要底气。 从原子弹到氢弹,是科技,更是底牌。 中国能有今天,不是因为人多地大,是因为曾有这样一群人,饿着肚子、抱着算盘,把世界最复杂的武器结构,一层层抠出来。 他们不求名,也不愿多说,但每一颗爆炸的声音,都替他们在说:我们算出来了,我们能。 参考资料: 程开甲、于敏:《两弹一星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