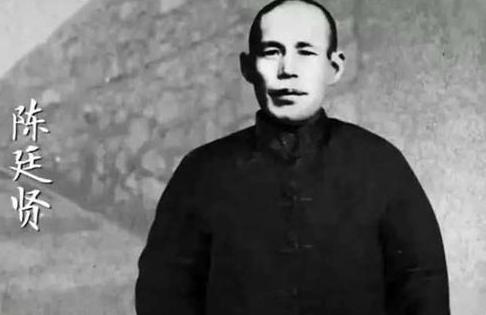1934年,程子华和郑位三亲自率领红25军从鄂豫皖苏区撤退,但没想到狡猾的敌军却布下了“铁桶阵”,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卖货郎站出来说:“放心,我准能带你们脱险。” 1934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上空乌云密布。红25军官兵们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这片曾经红旗漫卷的土地已被敌人压缩得只剩下几个零星的小块,部队被迫不断转移,飘忽游击。 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位装扮成走乡串村小货郎的人悄然出现在了红军队伍中。他是鄂东北道委派来的营政委陈锦秀。他向徐海东、吴焕先递上了一封珍贵的信件。 "宝珊、海东、焕先同志,中央派人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北来找我们。"这是郑位三的亲笔信,字里行间透露着紧迫和希望。 这封信犹如一线生机照进了困境中的红25军。多少次的书面提议、盼望已久的心愿,终于在这个飘忽不定的时刻得以实现——党中央终于派人来了! 其实,早在半年前,周恩来就曾与程子华进行过一次重要谈话。那是1934年6月,程子华在红军大学学习时,接到了去鄂豫皖的新任务。周恩来详细分析了鄂豫皖地区的严峻形势:"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人用碉堡、封锁线,以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把我根据地压缩分割成小块。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 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部队才能得到发展。把敌军主力引走了,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 这次谈话的背后,是鄂豫皖根据地屡次向中央发出的求援信号。1933年1月5日,省委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等八位领导人曾联名向中央请求:"务必设法多派干部来,我们的需要当然是很大的,不过我们估量中央无积有大批干部调到苏区来,至少请派10人左右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能领导全盘工作的干部来苏区。" 这些求援信是如何送达中央的?1934年,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冒险从鄂豫皖突围到上海,却找不到党的关系。他想起了鲁迅先生,便到四川路内山书店找到了内山完造。几天后,在一家咖啡馆里,成仿吾见到了鲁迅和茅盾,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通过鲁迅的帮助,成仿吾终于找到了党的关系,将鄂豫皖根据地的困境报告给了中央。 收到郑位三的信后,徐海东和吴焕先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奔赴鄂东北与中央派来的同志会合。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上官云相指挥的"追剿"部队像一张大网,正在步步紧逼。 而在大网编织的几个月前,一场生死相随的护送任务已经悄然展开。石健民,这位往返穿梭于上海和鄂豫皖苏区之间的"神秘人物",党的地下交通员,正带着程子华从上海返回根据地。 他们装扮成普通商客,搭乘客轮逆江而上抵达武汉。在汉口码头,敌人的岗哨林立,盘查极为严格。石健民常来常往,应对敌人的盘查从容自若;程子华在武汉读过书,熟悉城市环境,也顺利通过了盘问。 离开码头后,他们考虑到年龄相同而口音不同的两人走在一起容易引起怀疑,便一前一后相跟,装作互不相识。在汉口车站,石健民很快通过了检票口,而程子华却被宪兵拦下。 "你到哪里去?"宪兵盯着程子华问。 "到鸡公山去游览。"程子华沉着回答。 宪兵搜完箱子,还要检查他的手。程子华左手指曾受过伤,已伸不直,如果被发现这个枪伤,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程子华右手举起让宪兵查看,左手则握着一把扇子,巧妙地掩饰了受伤的手指。虽然最终获准登车,但已耽误了不少时间。石健民在火车上焦急等待,发现程子华迟迟未到,曾下车寻找,程子华用眼神示意他不要靠近,以免暴露两人的关系。 经过这样的惊险旅程,程子华最终安全抵达鄂豫皖,将中央的指示带给了当地同志。 而现在,1934年11月6日,红25军从葛藤山紧急出发,向西挺进。翌日,部队先后击溃敌人三道防线。11月8日拂晓,红军到达光山县东南50里的斛山寨。部队急行军200余里,几次激战后已十分疲劳,准备稍事休息。 就在这时,敌第107师、117师和第四、第五"追剿"支队,总共10个团的兵力从东南两面发起猛攻。更令人担忧的是,敌"追剿队"总指挥上官云相乘飞机在战场上空督战,敌机轮番轰炸、扫射,红25军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决战。 是"走"还是"打"?面对这个抉择,徐海东和吴焕先定下了"以打取胜"的决心。他们调整部署,以七十四师扼守高地牵制敌人,同时以二二四团和二二三团向敌实施侧翼突击。 战斗从早晨打到黄昏,红军将敌人压至朱家坳,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位置。敌人在三面夹击下纷纷溃散,仓皇逃窜。红军毙伤俘敌约4000人,自身也伤亡数百人。营政委姚志修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负重伤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