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返回家乡的前夕,李亚茹哆哆嗦嗦地脱下衣服,告诉老公:“今天晚上,让我们再做一回夫妇!”然后她就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回到了城里,时隔42年,她又见到了自己的女儿。 东北刮着冷风,火车站月台上堆满棉被和蛇皮袋。 上百万张返城登记表刚刚发下去,一夜之间,三线建设、知青上山下乡,全都成了过去式。 风声一紧,人心全乱了,城里工作铁饭碗,农村就是田头一把汗,谁都明白:这趟车不挤上,以后怕是再没机会。 李亚茹坐在炕边,手里攥着通知单,指尖冻得通红。 纸上写着她被安排,回天津机床厂车间做资料员,正儿八经的国营单位正式工,户口也能转。 旁边是个五岁的女孩,一边啃冻梨,一边哼着《浏阳河》,男人蹲在灶前烧柴,抬头看她时眼里全是土,一点不透气。 决定前没人劝,男人一句话也没说,只把家里那床厚被子留给了她。 孩子她不敢抱,怕一抱就走不了。 返城通知就是刀子,割的是家,切的是命。 李亚茹没哭,走到村口才吐了口气,身后雪地没留脚印,北风把门板吹得“咣咣”响。 在农村待了十年,埋过人,接过生,跟着大队种过地、打过狼,原以为扎根一辈子,结果一纸政策就全翻篇。 “回城”这词,当时跟“重生”一个劲儿,人人往前挤,没人敢回头看。 三年里,全国返城知青超一千万。 火车站、招工处、人武部门口挤得跟春运,每个窗口都围满人,每份表后头都跟着一家命运,李亚茹赶上了,但也掉了一半命。 没人给她准备行李,没人替她送行,没人告诉她离婚协议该怎么写。 村里人骂,说是“白眼狼”“抛弃女儿的女人”。 城里人也不认,说是“下乡回来不中用”,夹在中间,不上不下,不新不旧。 她从来没求过谁,但那年开春后,她托了三道关系,才把自己档案从乡里抠出来。 真正让她醒悟的,是车间食堂打饭那次。 排队时听人说:“女知青回来大都离了,谁舍得跟个农民过一辈子?”她端着铝饭盆,没说话,饭里掉了两粒眼泪。 那个年代,女人得生、得扛、得忍,回城的路,她们扛着行李箱,也扛着全村的目光和指责。 她不是第一个离婚的,也不是最后一个。 但因为是女的,被放大十倍骂,别的知青回城时丢的是地,她丢的是孩子。 她没得选,天津户口、城市学校、单位福利房,这些东西能换命。 她不回,孩子也永远出不来,清楚得很:如果留在那片地里,下一代也会一辈子刨土吃野菜。 赌了一把,把命搭进去了,指望哪天能再补回来。 但这一别就是42年,女儿成年后回过一次村,问大队书记:“李亚茹呢?” 书记愣了半天,说:“走了,不回来啦。”那时候通信靠写信,电话得去镇上邮电所,谁也没法主动联系谁,只能等。 等来了高铁,也等来了微信。 2000年后,李亚茹退休,搬进了天津南开的一间小屋,老邻居聚会,她喝了点酒,说了句:“我那孩子,还在么?” 命运很奇怪,兜了一大圈,有时候又把人往回拉。 2020年春,她接到个陌生电话。对方没说名字,只问:“您是李亚茹么?” 这一句,像炸雷一样炸在耳朵里。 两个月后,重逢在安庆老家,地点是县城边的饭馆,屋里没开空调,两人对坐,桌上摆一盘小咸鱼和一壶米酒。 没眼泪,也没抱头。只问了一句:“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对方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下了点雨,像42年前那天一样。不同的是,没人走。 饭后,女儿塞了张老照片,是当年她走时留的。 上头是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站在雪地里,后头是一排茅屋,李亚茹拿着照片,没出声,手指却一直在抖。 过去的事没法改,能改的是怎么活下去。 如今城乡差距没那么大,返乡不再丢脸。 李亚茹没问“你原谅我了吗”,她知道那是自私,只说了句:“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 那一刻,两代人终于不再隔着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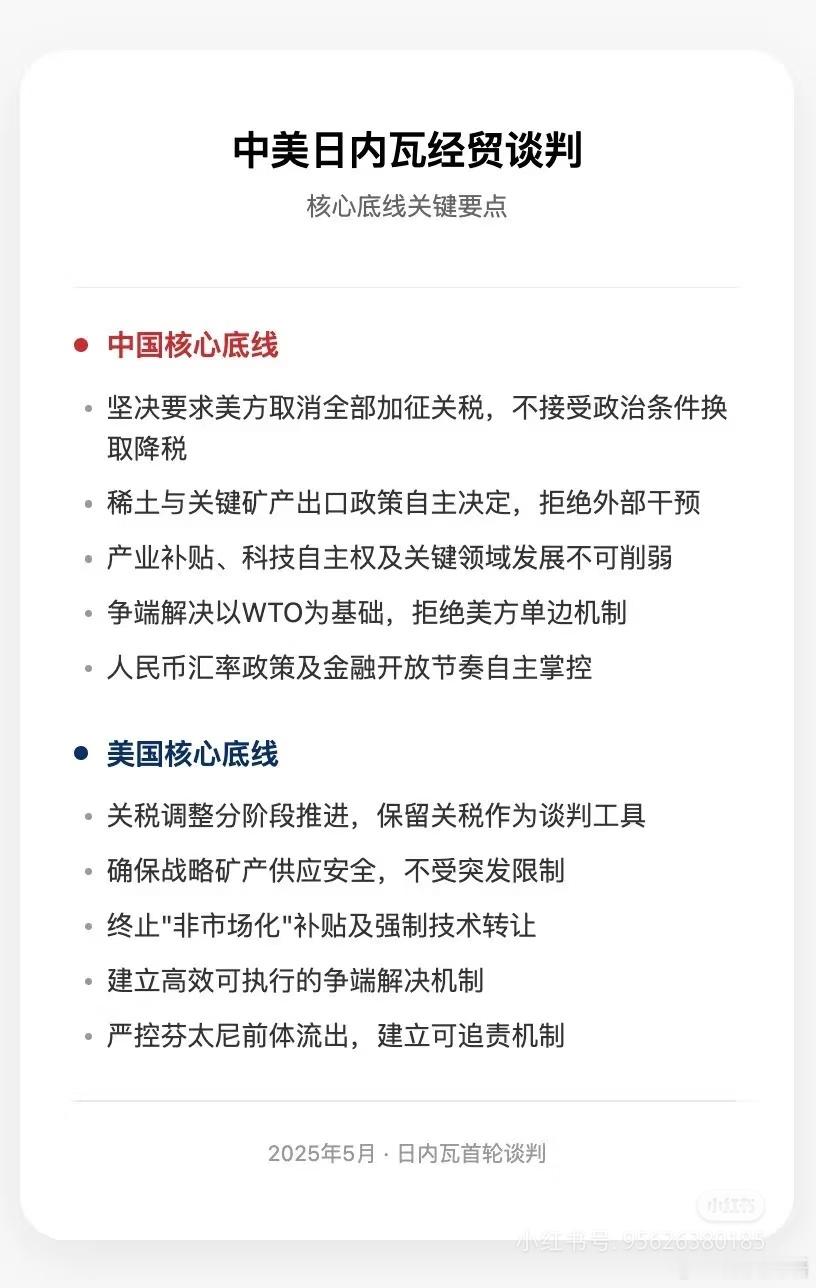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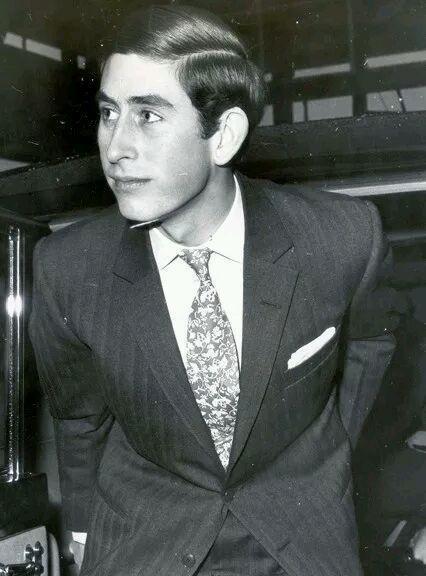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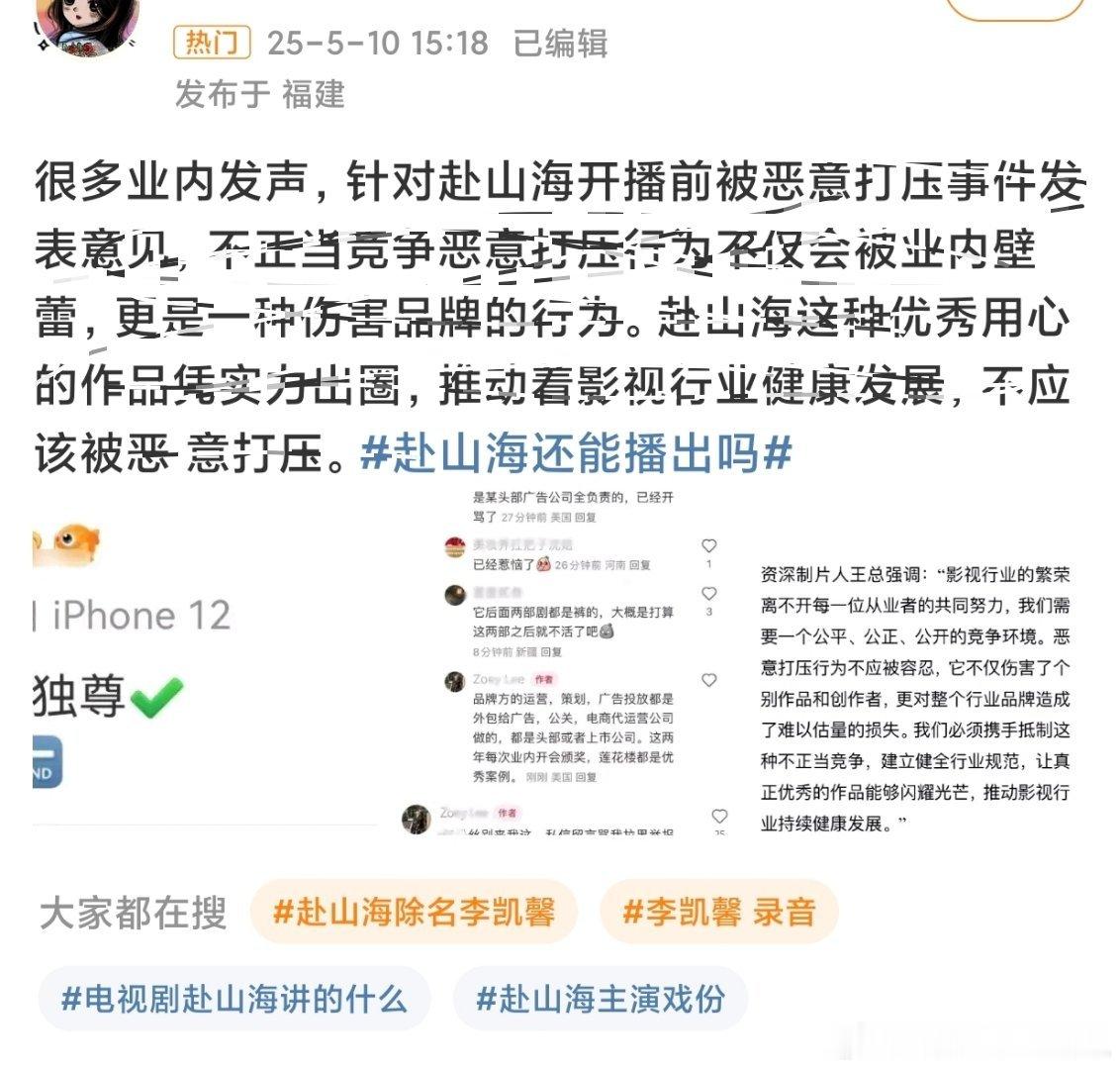




tb73790898
乱七八糟,瞎比咧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