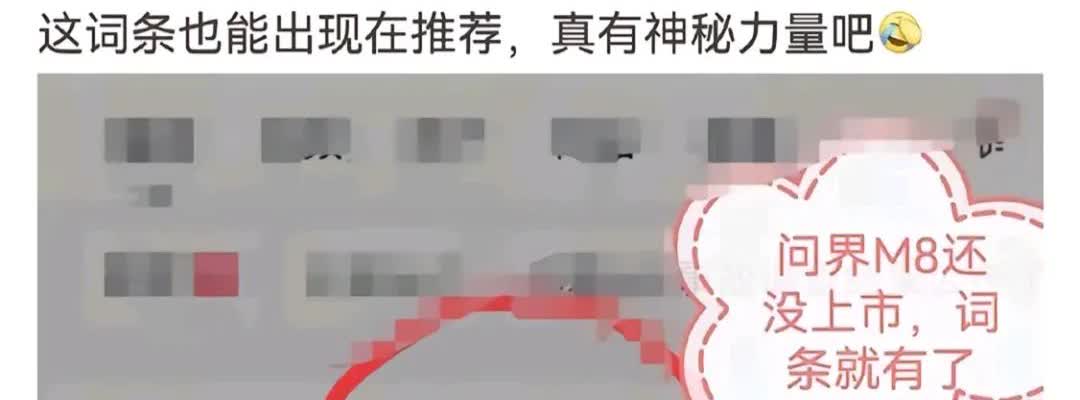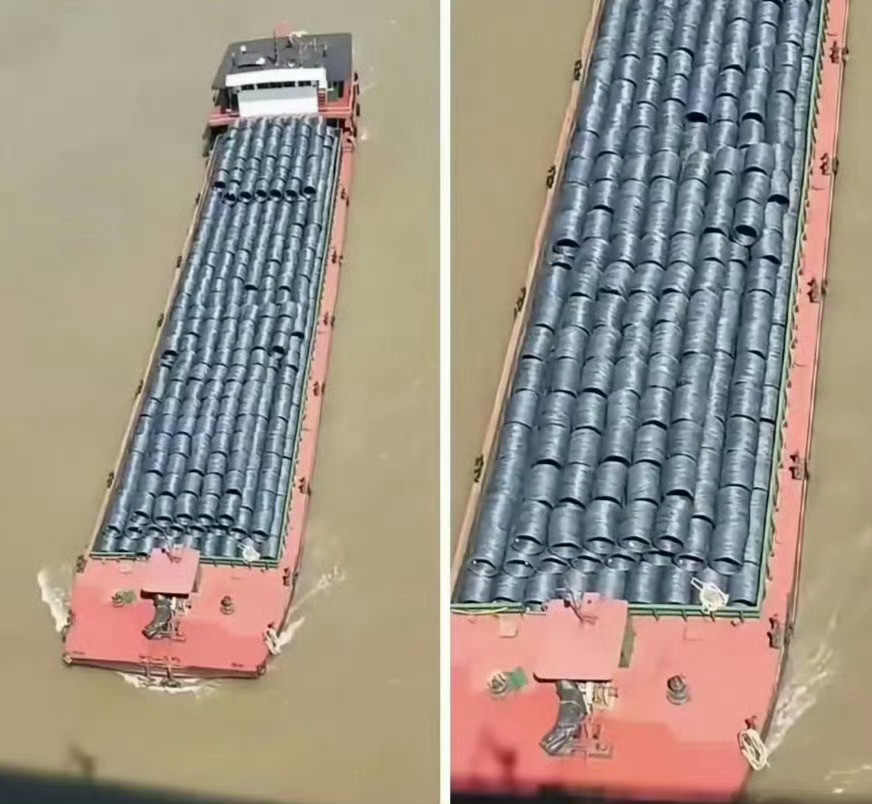消毒水气味刺鼻,我躺在病床上,看儿媳妇凌晨两点仍在按摩我浮肿的双腿。她头发油得打结,穿了三天的居家服皱巴巴,手背满是扎针的青紫。两个多月,她睡折叠床,护工价目表就在墙上,却坚持亲自擦身、喂水。隔壁床羡慕“闺女孝顺”,她只笑笑,继续用小勺润我干裂的唇。 亲女儿的电话总在饭点响起,麻将声混着“走不开”的借口。她不知营养餐要提前订,不懂气垫需定时翻面,通话像完成任务。 出院日,儿媳蹲地收拾便盆,汗珠砸在瓷砖上。女儿踩着细高跟冲进来,香水盖过消毒水,水钻指甲硌疼我:“把二十万给我吧。”这话比监护仪的警报更刺耳。 此刻终于懂:亲情不是银行卡的零,是深夜里带体温的便盆,是俯身照料的身影。儿媳没说甜言,却用熬红的眼、磨破的手,把“孝顺”写成日复一日的守护。而女儿的关心,终在索要金钱时,显了单薄。春风里,儿媳扶我出院,身后女儿的念叨,抵不过她掌心的温度——这,才是命运最暖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