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在看过明朝大臣的奏议,特别是熊廷弼的奏章后,颇为感慨,给了熊廷弼极高的评价:“明之晓军事者,当以熊廷弼为巨擘,读其《陛辞》一疏,几欲落泪!” 乾隆说,他看到熊廷弼奏章中写的“洒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躯于边塞”,为这个生前致力于抵抗清朝的明朝忠臣感到惋惜不已,想不到天启皇帝看完居然置若罔闻。 熊廷弼跪在乾清宫外等召见那晚,宫灯在寒风里晃得像冤魂的灯笼。他怀里揣着《三方布置疏》,靴子里垫着辽东地图——这玩意儿比棉鞋还厚实。天启帝正忙着雕木头人儿,太监魏忠贤捏着奏折冷笑:“老熊又拿血啊躯啊吓唬人,皇上最烦这套。”果然奏疏送进去,朱砂批红没见着,倒飘出一股木屑味儿。 当年辽东的冰碴子可比北京城硬气。熊廷弼带着士兵修七百多里边墙,零下三十度夯土垒砖,冻疮裂得渗血。屯田种出的高粱能堆成山,硬是喂饱了十万辽军。努尔哈赤派探子偷看,回来直嘬牙花子:“熊瞎子把荒地整得比八旗田还肥,这仗没法打!”可北京城里那帮穿蟒袍的,眼睛盯的不是辽东防线,而是熊廷弼有没有给东林党送年礼。 最绝的是广宁之战。巡抚王化贞领着六万精兵瞎冲锋,熊廷弼在山海关急得啃桌角:“守住!老子给你运粮!”结果王化贞撒丫子跑得比驿马还快,粮车刚到半道就变成溃兵的绊脚石。兵败消息传回京城,御史们连夜写弹章——熊廷弼“救援不力”的罪名,比王化贞丢城失地还大。这官司打得比辽东战场还热闹,最后定了个“同罪论斩”,熊瞎子跟草包巡抚捆一块儿上了断头台。 乾隆捧着《熊廷弼集》摇头:“明朝这帮人,比八旗军还会杀自己人。”他特理解熊廷弼奏折里那句“朝士多厌恶之”——这暴脾气在辽东整顿军纪,把吃空饷的将领吊城楼上抽;回京城述职,又把送礼的官员踹出衙门。得罪的人能从山海关排到秦淮河,最后连楚党老乡都背后捅刀。可八旗入关后查他账本,家里就三间土房,连努尔哈赤的悬赏金都没贪过一分。 更讽刺的是历史轮回。熊廷弼被传首九边那年,皇太极正在沈阳读他写的《防建夷疏》,拍腿叫好:“南朝若多用此等人,我等安能入关?”百年后乾隆给前朝忠臣平反,给自家臣子敲警钟:“看见没?谁糟蹋能臣,谁就是亡国之兆!”紫禁城的日晷转了一圈,杀熊廷弼的罪名从“通敌”变成“站错队”,只有辽河边那些他亲手栽的防沙柳,还年年春天冒新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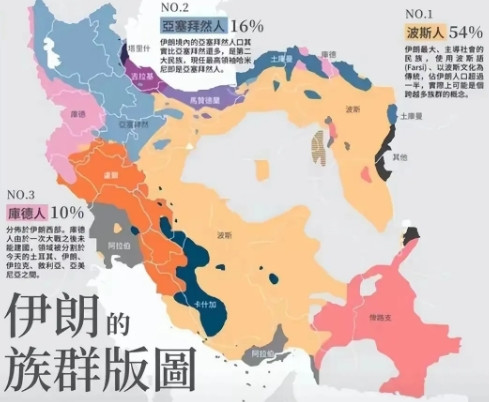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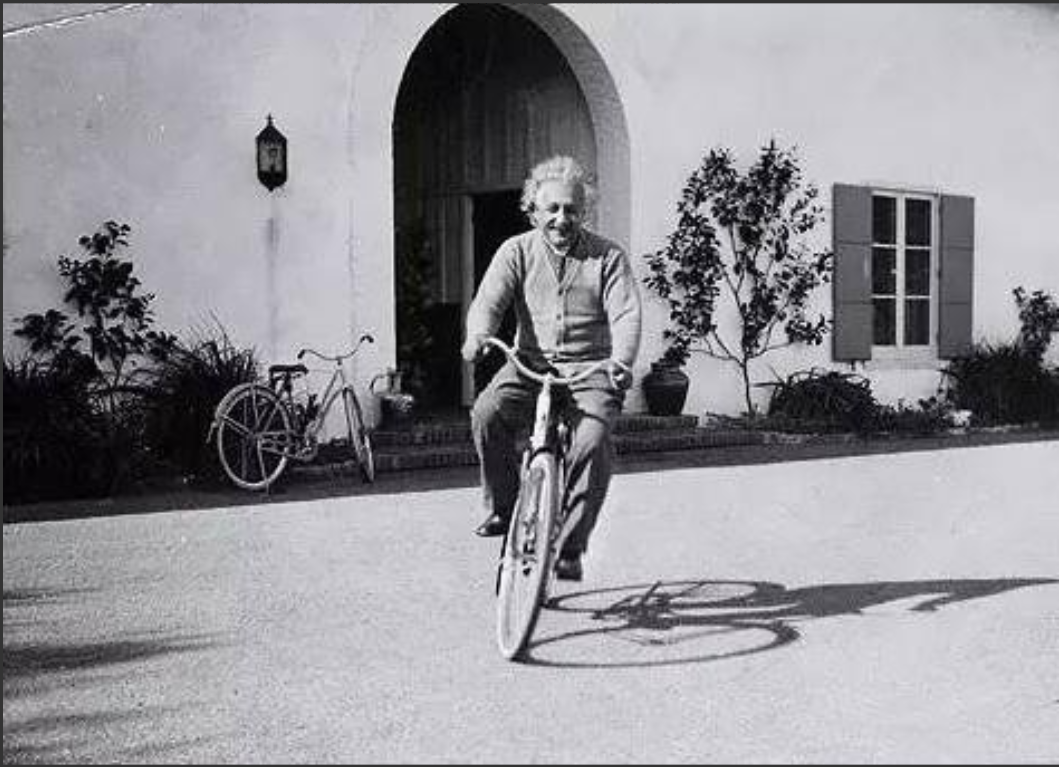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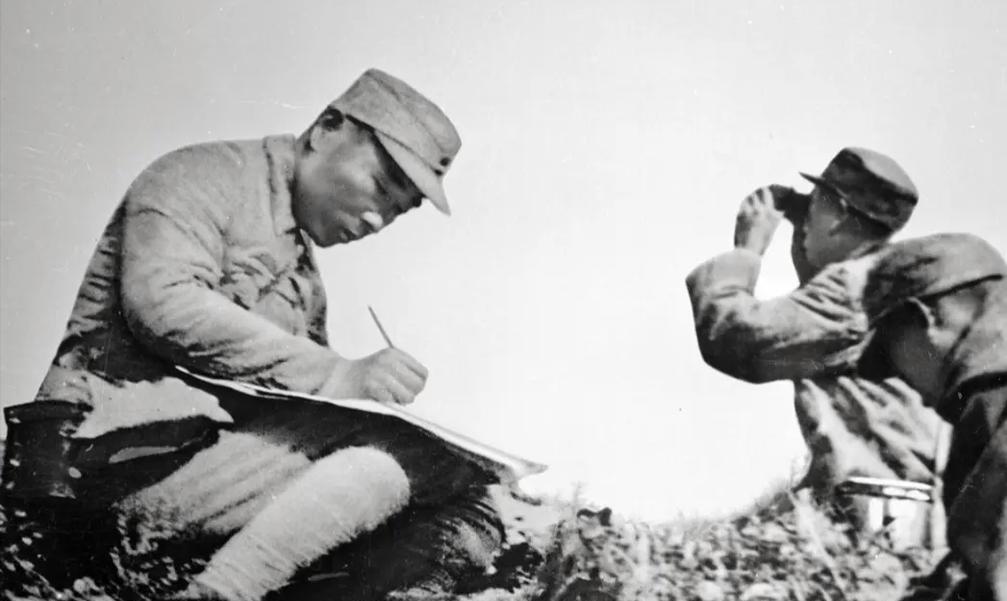




宇化贤
满清十大酷刑、闭关锁国、不思进取、文字狱、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剃发易服、驱使奴隶、鞑子一人管十家,银乱中国女子,欺男霸女、康熙乾隆六下江南挥霍奢靡、四库全书篡改禁毁15万册古籍、隐藏满清罪恶事实、抹黑明朝历史、禁锢思想、打断人民的脊梁骨、误人子弟,误导国人成为奴隶、阉割中华文明,使我国回到漆黑蒙昧的原始社会、凡有水旱,坐视不管、重徭役、纵贪官污吏,官以贿得邢以钱免,腐败,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国库空虚、圈地运动,百姓流离失所、民族压迫、宁与外邦不与家奴、割地赔款、不战而败、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百年屈辱、祸国殃民、扼杀维新、残暴专制、种族灭绝、赵州之屠、畿南之屠、潼关之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江阴八十一日、常熟之屠、四川大屠杀、金华之屠、南昌大屠杀、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汾州之屠、大同之屠、广州大屠杀、潮州之屠……几乎将明朝全境上下屠了个底朝天,整个华夏大地十室九空!中国文明领先世界几千年,直到满清统治时期才急剧衰落到世界贫穷国家。由于满清持续篡改两百多年的历史,很多罪恶都被掩盖!这些还只是已确认过的真实事件,不信的请自己先查一下有没有这些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