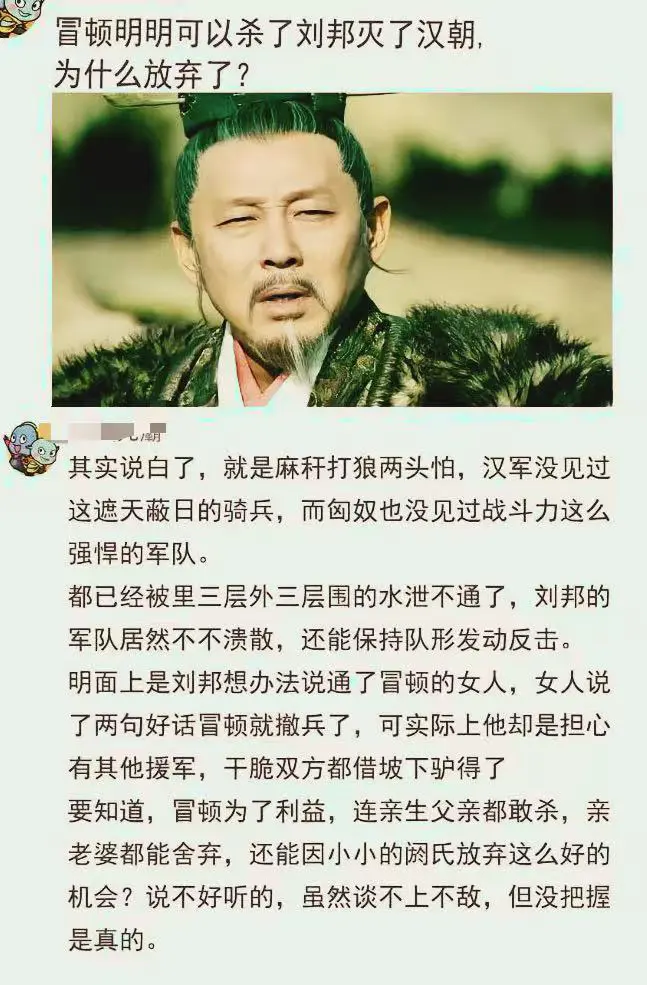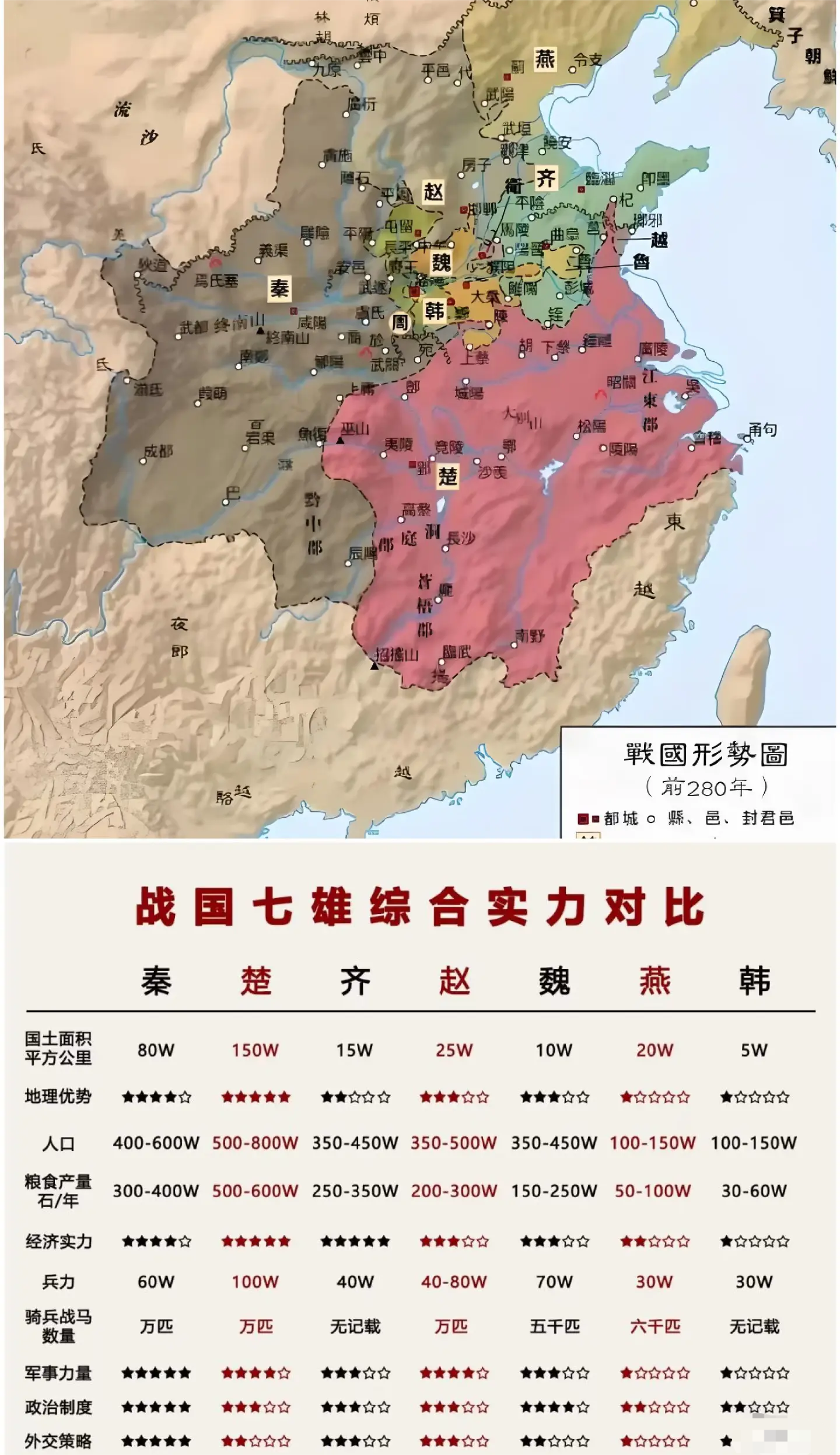从唐末以后,中原大地便陷入了几百年的分裂割据的局面,直到“崖山海战”的结束,中国才在元朝这个新生的政权中实现了统一。 而这一次的“大一统”,规模远远超过以往的汉唐时代,以至于“后来者”也是望尘莫及。元代空前辽阔的疆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而这也是忽必烈在中国疆域版图奠定中,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元代的疆域“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逾阴山。”,元世祖所建立的大元帝国的版图空前绝后,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这就正如王熙凤所说的“大有大的难处。”,如何有效地治理这样空前辽阔的疆域土地成为摆在元朝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此外,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性质意味着大元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实行简单粗暴的“部落联盟制”,新生的大帝国亟需一个新的制度来满足忽必烈的统治需求。 于是,元世祖开始频繁地和已经归顺的臣子接触交流。虽然他本人是蒙古部落的大汗,是从马背上打下江山的皇帝,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推崇汉化,向往“汉唐盛世”。 所以,在制定新的制度时,忽必烈考虑到了了唐代广建藩镇引起国家动乱和宋朝“重文抑武”导致王朝衰落的经验教训,又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金国的“行尚书省”,最终创立了“中书省”和“行中书省”(后世简称“行省”)分别管理中央和地方的制度。 其中,中书省高度集权,是国家政府的核心机关。而行中书省也保留了部分行政、军事和财税权,以确保地方军事上的稳定和赋税征收的效率。 “行省”初期虽然属于是中书省的外派机关,但随着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行省开始常驻地方,成为正式的行政机构。行省之下的“路”、“府”、“州”、“县”与宋制大体相同。 行省制度的创新同时也体现在具体的行政区域划分上。有鉴于唐末五代的割据局面和辽、金、宋和西夏并立的历史经验教训。 元代在行政区域的划分上不再仅仅依据“山川形便”来进行范围定界,而是更进一步地以“犬牙交错,相互牵制”来进行行省界线的划分。 就比如汉中地区是巴蜀两地的“门户”,刘邦、刘备都是拿下了汉中之后才可以坦然的将巴蜀地区作为大后方。 就这样的一个对于川蜀之地来说的“要害之郡”在元朝的行政地域划分中却划分给了陕西行省,自此四川就失去了割据一方的先决条件。 同样的,淮河流域自古就是南方的“膏腴之地”,光武帝刘秀的“龙兴之地”便是在南阳,汉末的袁术也是凭借淮南之地割据一方。 可是在具体的行省划分上,淮水流域却被划分给了北方的河南行省。于是,南方诸省都得“老老实实的趴着”,不敢妄动。 忽必烈在行政区域划分上如此刻意为之,为的是让各地方无法依靠山河之险要而拥兵自重。 但在中书省直辖的“腹里”的划分中,却是恰恰相反。中书省所管辖范围尽收“机要之地”。 中书省掌管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大部分和山东的部分地区,这些重点地域皆处于中原各地的核心地段,以便于中书省对其范围内的区域进行监控和管理。 此外,中书省中还常设一个“宣政院”的国家机构,负责管理全国的宗教事宜和统辖西藏地区的军政要务。 而宣政院的设立意味着西藏高原地区正式纳入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进一步加强了藏区的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交流联系。 元代的行省制度无疑是继秦朝郡县制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又一大发展。 这项制度极大的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省”作为最高一级的行政机构被明清沿用,一直被保留到今天。 元朝实行的行省制度,是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权衡利弊的行政举措。 它吸取了许多历史方面经验教训,综合了行政、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考虑,并经过几代统治者的发展和完善,才形成了最终的制度。元代的行省制无疑是中国行政制度发展的一大历史性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