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吴桂贤主动辞去职务,回到西北国棉厂继续当工人。可就在回到陕西的当晚,得知姐妹们上夜班后,她就直奔工厂也要上夜班:“我是个工人,我能干活!” 1977年初秋,长安街的梧桐叶还未完全落尽,一则不起眼的辞职申请却悄然递到了中组部的办公桌上。 那份申请上写得干净利落,只有短短几行字,但字里行间却掷地有声——“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返回西北国棉一厂工作。” 署名,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年仅39岁的吴桂贤。 消息传开,不少人错愕,一个年轻的女副总理,在万千工人眼中仿佛“从车间飞上北京”的传奇人物,竟然要放下权位、回炉工厂? 有人以为她受了委屈,有人猜她另有安排,更多的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对于吴桂贤而言,这是她早已深思熟虑的决定。 她清楚地记得自己是从哪儿来的。1951年,年仅13岁的她走进西北国棉一厂,成为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 日复一日,她在织布机前站着,双手被纱线磨出厚茧,嗓子因为纺织车间的噪音而沙哑。 可她从不抱怨,反而从中找到了劳动的尊严和人生的方向。 在那段特殊时期里,她因出身“工人阶级”,被破格提拔,成为“工人进中央”的象征。 她讲话带着一口浓重的陕西腔,言语直白,作风朴实,甚至连出访外国时,也仍穿着那身熟悉的蓝布工装。 可时间一长,她心中愈发不安。“我并不适合做政治工作,”她常说,“我就是个干活的人。” 1977年,她终于下定决心,向中央递交辞职报告。 没有挽留,没有阻拦,因为她的诚意和态度太坚定。 有人说她傻,这样的位置,有多少人一生求之不得?可吴桂贤笑笑:“一个人不能忘本。 工人出身,不代表升了职就永远脱离工人。我是工人,就得回去干工人的活。” 辞职获批的那天,她没有宴席、没有送行,悄然打包了几件行李,一张火车票,从北京西站启程,穿越千里,回到了她曾无数次进出的地方,西北国棉一厂。 那是个寒冷的晚上,天刚擦黑,工厂宿舍区灯光稀疏。她拖着行李刚落脚,便听闻老姐妹们正在车间加班赶活。 她立刻放下东西,什么也没说,转身就出了门。 “吴姐,你这是……”门卫老张一愣,看清是她,赶紧站起敬礼。 “我来上夜班。”吴桂贤的话简单明了,没有丝毫犹豫。 老张慌了:“不行不行,吴姐,你才回来,哪能马上上班?咱们得安排安排。” “我不安排。”她固执地笑了笑,“我是个工人,我能干活。” 说完,她熟练地披上旧工装,踏进嘈杂的车间。 空气中还是熟悉的棉絮味道,机器运转的轰鸣震耳欲聋。 老工友们一回头,竟看见她站在纺织机前,正把袖子撸起,准备开工。 “吴姐!”大家惊呼。 她回头,笑得爽朗:“我不是吴副总理了,叫我桂贤就行。我今天来上夜班,你们累了,就去歇会儿吧!” 没人说话,眼眶却泛红。有的工人下意识地停下活计,有的则悄悄转过身,抹了一把眼泪。 谁也没想到,这个曾站在人民大会堂里发言、在外宾面前代表国家形象的“女副总理”,会在回厂当晚毫无架子地回到一线。 那一夜,西北国棉一厂的灯,亮得格外久。 她回来的消息,很快在工厂传开,她没有办公室,也不要秘书。 每天按时上下班,干最累的活,轮最苦的班。 有一次,领导提议让她进厂部做技术指导,她笑着摇头:“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带好头、干好活。我不会躲在屋里当‘干部’,我就是一名纺织工人。” 她说到做到。夏天汗水湿透衣背,冬天手指冻裂流血,她从未请过一天假。 有人心疼她:“你都当过副总理了,何必呢?”她却淡淡回答:“劳动是我的根。我在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能干、还能带动大家干。” 这种精神,不仅感动了西北国棉一厂的工人,更成为当年许多普通人心中的一道光。 在那个改革开放初启、百废待兴的年代,吴桂贤的选择,像是一种清醒的回归,也是一种沉静的坚守。 多年后,有人问她:“你后悔吗?那可是副总理啊。”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后悔。我做工人的时候,心最踏实。” 是的,她的身份或许变了,可她的根从未变。她用一生证明:劳动并不卑微,选择做一个真正的工人,也是一种伟大的坚持。 信息来源:百度百科——吴桂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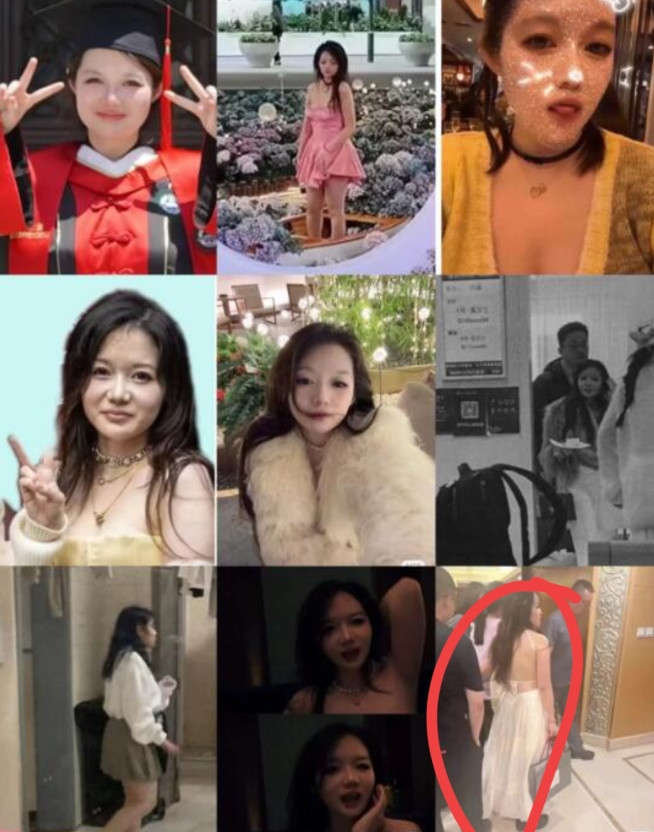

![五四奖章获得者大合照中的莎莎![呲牙笑]一眼就找出了大合照中的莎莎,因为她居中而](http://image.uczzd.cn/2326542908912631974.gif?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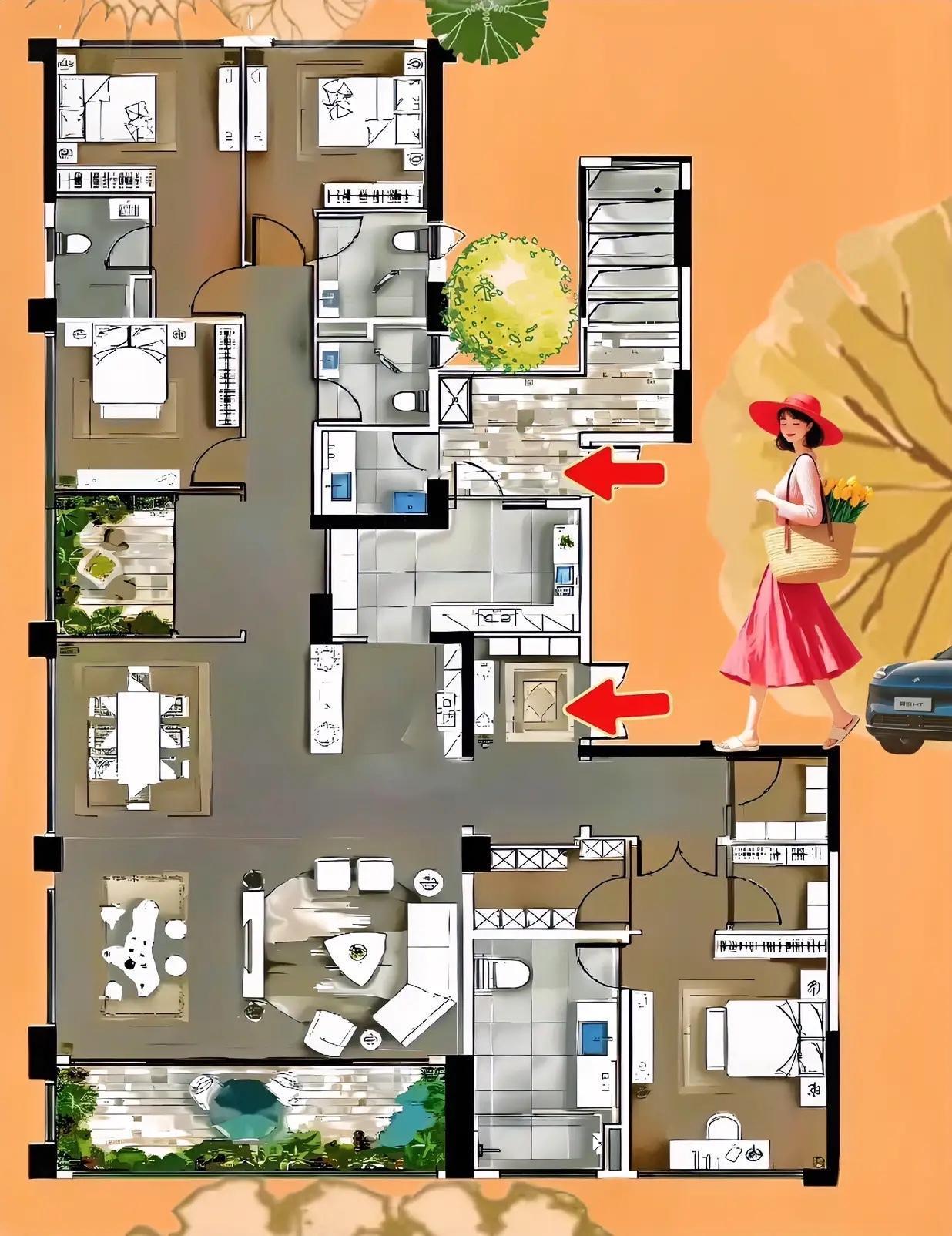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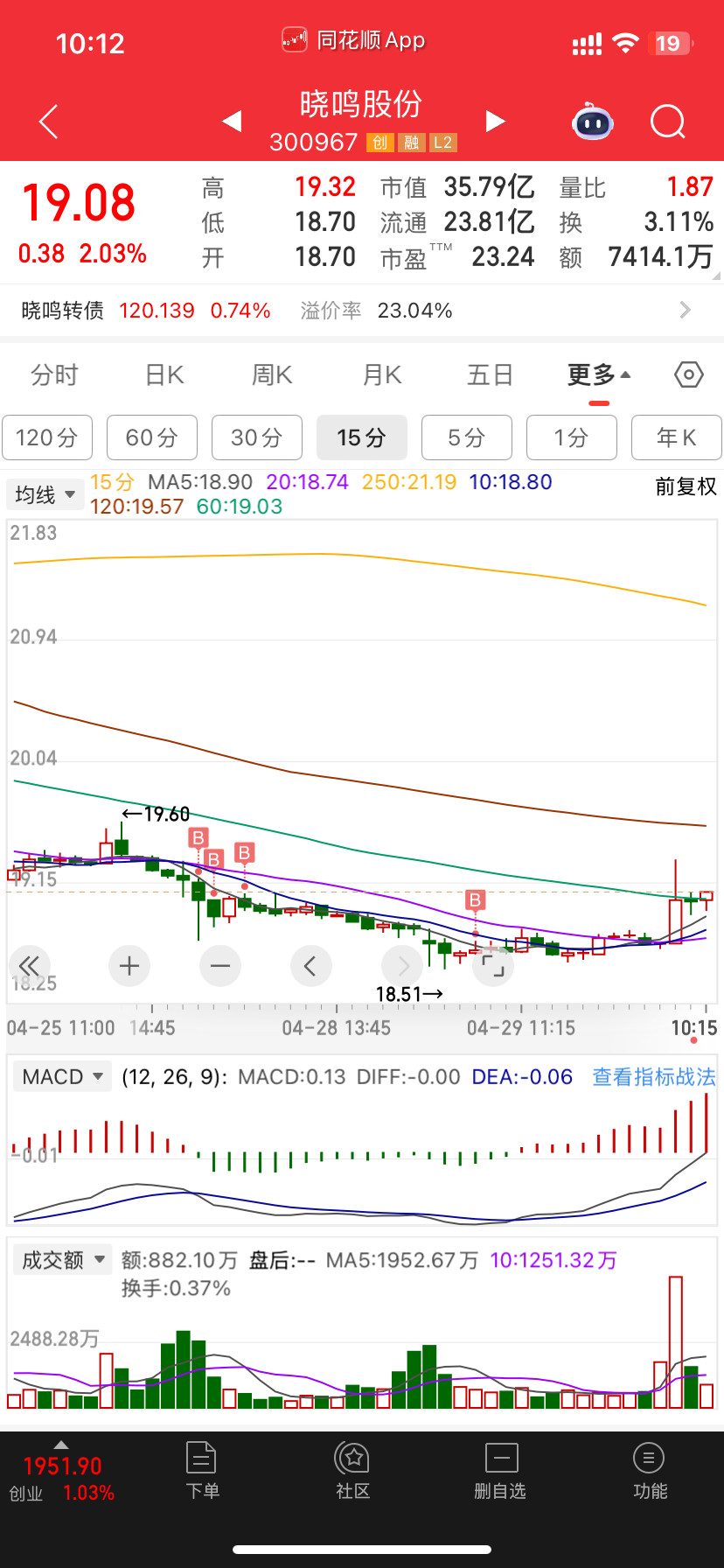



用户69xxx05
火红的年代,火热的心[点赞]
用户14xxx81
当时有北京西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