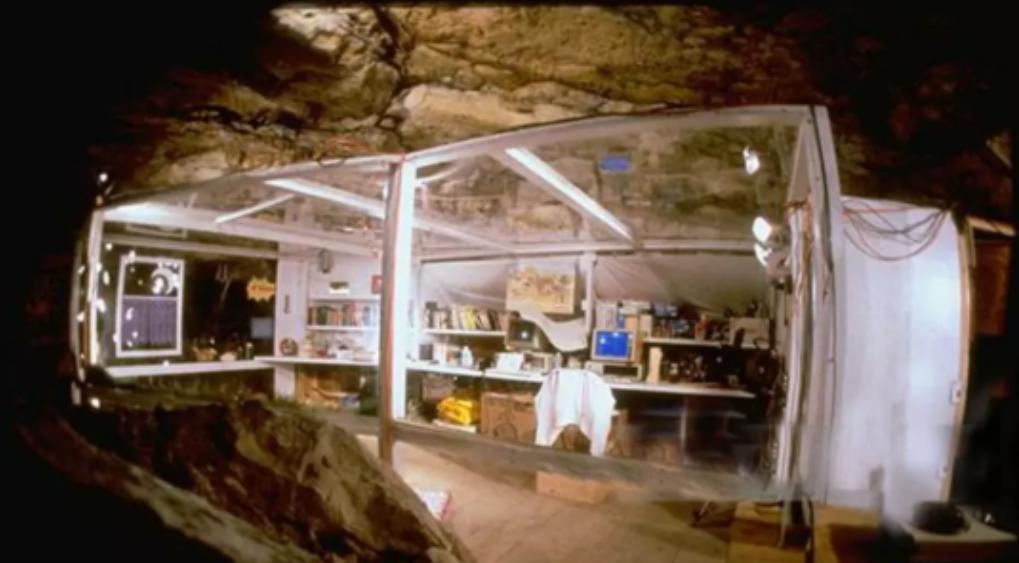刚从北影厂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梁晓声还住在单身宿舍里,一间11平米的斗室,木板床、蜂窝煤炉子、书桌堆满手稿,光线暗,油烟味浓。 单位食堂一顿饭八分钱都舍不得吃,每月42块5的工资,要寄回老家30块,剩下十来块,扛不住病、扛不住书,也扛不住恋爱。 单位里知道这个年轻人脑子灵、写得快,也穷得快。 大哥疯了,天天靠药稳着;五个兄弟姐妹全得指望他;爹妈年纪大了,老母亲舍不得吃肉;这摊子家务,哪个姑娘能接? 以前相亲几次,坐下不到十分钟就被看破底细——姑娘笑一笑,说“回头联系”,再就没音。 这次相亲,对象是北京姑娘,焦丹,工作安稳,家里是知识分子,规矩。 单位师傅给牵的线,说这姑娘有点意思,不嫌穷,不嫌事儿多。 见面当天,梁晓声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裤缝还烫着,头发压得服帖,手心都是汗,怕自己又吓跑人。干脆一开口就“摊牌”: “我工资不高,要寄钱回东北。大哥有病,吃药离不了人。我身体也不算好,胃炎、肝炎,都是熬夜写稿熬出来的。” 说完就等姑娘开溜,心想这回又得凉。 结果焦丹听得眼圈泛红,抬头回了一句:“没关系,多一个人分担就轻点。”这句话不大,但砸在梁晓声心口上,像有人替他扛起了一截天。 俩人第一次约会是去北海公园,梁晓声紧张得一路说话都打磕巴,焦丹安安静静听,时不时笑一笑。 他讲小时候打群架,讲知青时在黑龙江写广播稿,讲回城以后怎么熬夜,写剧本换五十块钱稿费,讲得嘴干舌燥,也讲不出一个“我喜欢你”。 几次下来,关系才慢慢热起来。 结婚当天,焦丹带着两床新棉被、几个搪瓷盆,搬进梁晓声那间11平米的小屋。 厨房没地儿,就把蜂窝煤炉子搬到走廊里做饭。 邻居说炒菜油烟呛鼻,焦丹就买把破蒲扇扇着,尽量不让油烟往屋里窜。 屋里桌上永远是稿纸,焦丹一边擦地一边踮着脚走,连洗衣服都选梁晓声休息的点做。 孩子出生那年,家里条件还捉襟见肘。 孩子哭,她往楼道里抱;梁晓声写稿,她端茶送水,稿子写完了,她一页页替他校对。 有次梁晓声创作卡壳,焦丹悄悄跑去查资料,把相关政策、数据全抄下来放在桌上。 最难那几年,不是钱少,是人多事多。 梁晓声的弟妹相继下岗,来信、来电、来人,一个月几个汇款单。 焦丹没一句怨言,把工资分成几份,谁家有急事先解决谁。 梁家那位患病的大哥,没人看了,焦丹直接接到北京来,吃住照料一手包。 孩子高烧那回,夜里连烧三天,焦丹守着不敢睡,白天一边照顾病孩,一边还得去邮局寄稿件。 梁晓声那几天正赶着结稿,焦丹扛住不吭声。 稿子一交完,人才倒下,烧得说不出话,眼圈青的,梁晓声急疯了,骂自己是木头:“怎么连你发烧都没发现?” 焦丹嘴角咧开一点,说:“你写完稿,我就好了。” 那年梁晓声写《今夜有暴风雪》,夜里三点还在改台词,焦丹窝在窗边缝孩子的旧衣服。 屋里静得连针线穿过布料的声音都清楚。 稿子写完,他问:“你困不困?”焦丹眨眼:“你写完了,我也就不困了。” 梁晓声拿茅盾奖那年,记者问他:“你这么多作品,哪部最满意?”他没犹豫:“《人世间》。但要真说成就,这一生最值的,是娶到焦丹。” 有人说他是“人世间里的周秉昆”,梁晓声回一句:“我比他幸福。” 人家说梁晓声“走狗屎运”,娶了个贤妻。可焦丹也不是“没得选”。 当年追她的人不少,家境、长相、学历都不差,焦丹眼里,梁晓声是真诚,骨子里有担当,穷可以扛,病可以治,难可以熬,就怕人不肯讲实话。 两人几十年感情,从没大起大落过。 平时吵嘴,焦丹一摔筷子,梁晓声就闭嘴,转身出去溜达一圈回来装没事。 吵归吵,日子照样一把米两个人煮。焦丹做饭、洗衣、看孩子,梁晓声写作、读书、寄稿。一本书、一盏灯、一屋子人,苦也过,甜也过。 晚年以后,两人常在后海边上散步,焦丹讲单位同事谁家孙子考上大学了,谁家老头骑车摔了,梁晓声听得津津有味,还时不时记下来,说这些“比文献资料还生动”。 有人说焦丹像郑娟,梁晓声摇头:“郑娟是写出来的,焦丹是过出来的。” 参考资料: 《梁晓声:在“人世间”写尽人间事》,《人物》,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