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后,得知毛主席也不喜欢等级制,所以,即使在大会堂开会,仍穿老农民的对襟衣服,包白头巾,不计较什么级别,连工资都不要。回了大寨就和社员一样下地干活,年轻人仍叫他“永贵大叔“,谁能做到这些?他进了北京,儿子、老婆仍留在队上挣工分。山西省有关部门将他全家户口办出来,要他带到北京去。他拍着桌子吼:“是谁办的?我不同意,他敢!“结果户口又退了回去。 陈永贵这人,1914年出生在山西昔阳县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家。小时候命苦,6岁那年,爹因为活不下去了上吊走了,他只能寄人篱下,跟着个寡妇过日子,长大后靠给人当长工混口饭吃。1948年,他入了共产党,开始在村里有点事儿干了。到了1952年,他当上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时候的大寨,穷得要命,土地全是瘦得不行的小坡地,粮食产量低得可怜,1952年才亩产237斤。陈永贵不服这命,带着村民硬是把山坡改成梯田,修水渠、搞灌溉,愣生生把产量整到了1962年的774斤,翻了三倍多。 1963年,大寨碰上大洪水,村子差点全毁了。换别人兴许就哭着找国家要救济了,他不干,喊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不要国家粮食、不要钱、不要物资,生产不少、交公粮不少、上级任务不少。靠着自力更生,不仅把村子弄回了原样,还卖了175万斤粮食给国家。这事儿一传开,大寨就成了全国农业的标杆,陈永贵这名字也火了。他不是啥高学历的人,就是个泥腿子出身的农民,但硬靠着一股子劲儿,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1975年,陈永贵被调到北京,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管农业。这在当时可是天大的事儿,一个农民能爬到这位置,谁不眼红?可他上任后,压根没变样。听说毛主席也不喜欢等级制那套,他更来劲了。开会就在人民大会堂,别人西装革履,他呢?一身对襟衣服,头上包个白头巾,跟个老农民似的杵那儿。工资?他不要国家发的,就拿山西省每个月给的100块补贴,在北京每天1.2块伙食费,再加上回大寨挣的那点工分,跟普通社员一个样。 他还给自己弄了个“三分之一”工作法,啥意思呢?一年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开会,三分之一跑全国调研,三分之一回大寨干活。这法子一提出来,国家批了,他也真这么干。回了村,他还是那个“永贵大叔”,跟社员一块儿下地,年轻人喊他照样亲切,没一点架子。有人问他为啥不换身行头,他说:“我就是个农民,穿啥西装?不舒服!”这接地气的话,谁听了不服? 陈永贵进了北京,可没想着把家人都带上享福。儿子老婆还留在大寨,跟着生产队干活,挣工分过日子。他自己在北京也抠得很,不用公车跑私事儿,坐公交,买菜就去国营市场,啥免费的都不拿,说是“不能搞特殊化”。可山西省有些人觉得他当了副总理,咋能还这么寒酸呢?硬是背着他把全家户口迁到了北京,想让他一家子都过上城里人的日子。 这事儿传到陈永贵耳朵里,他火了。听说他拍着桌子就吼:“是谁办的?我不同意,他敢!”那架势,谁听了不哆嗦?结果呢,户口又老老实实退回了大寨。这不是啥小脾气,是他骨子里的那股劲儿——当了副总理又咋样?我还是农民,根在大寨,谁也别想给我改了去向。他这态度,搁现在看都少见,更别提那时候了。 陈永贵这人,真不讲究啥级别。副总理这身份,听着多牛,可他压根没把自己当回事儿。吃饭就吃大锅饭,住的地方也没啥讲究,连家里人都不沾他的光。有次有人送点好菜给他,他直接推了,说:“我吃得下粗粮,干嘛非要搞特殊?”这不是装,是他真这么想。毛主席那会儿提倡干部跟群众打成一片,他算是把这话听进去了,执行得比谁都彻底。 他当副总理那几年,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热潮还没退,他也常跑各地去看田、问产,跟农民聊怎么种地增收。别看他在北京开大会,回到大寨还是那副老样子,扛锄头、挖地,社员看他这样,谁敢说他高攀了权力?年轻人喊他“永贵大叔”,不是客套,是真觉得他没变,跟过去一个味儿。 1980年,陈永贵不当副总理了,被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这活儿听着不咋起眼,可他干得带劲。每周都去农场转悠,看看庄稼长得咋样,跟农民聊聊技术,分享自己在大寨那会儿的经验。生活还是老样子,简简单单,没啥排场。1986年,他得了肺癌,在北京去世,72岁。遗体运回大寨,埋在虎头山下,墓地弄得有点像中山陵,台阶设计挺有讲究。他的遗物里,有双布鞋,鞋底缝着大寨特有的二十八道针脚,搁在县博物馆里给人看。这鞋,算是他一辈子的写照——从农民到副总理,再到顾问,脚底下踩的还是那块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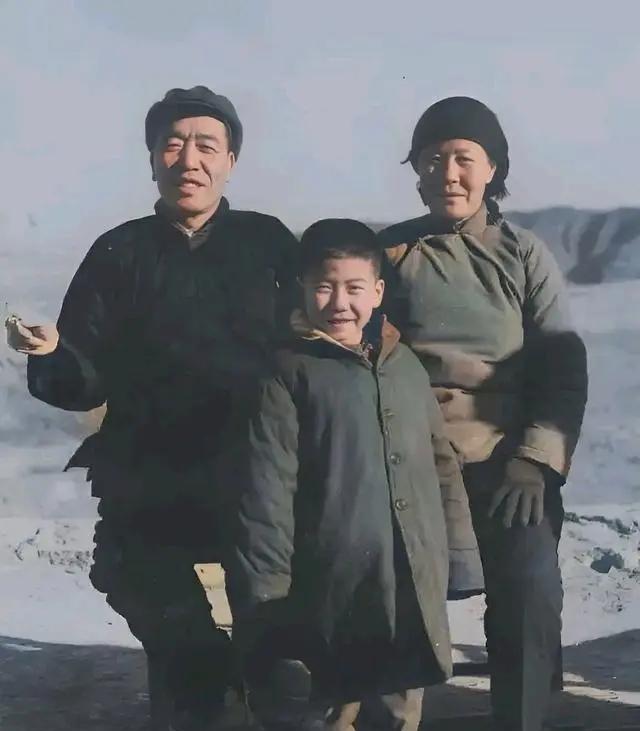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