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2年,薛仁贵全歼回纥大军,俘获十余万人,下令坑杀俘虏中的男子,并将女子赏赐给士兵。
公元662年,天山脚下寒风凛冽。薛仁贵身着白色战袍,银盔铠甲在阳光下闪耀,他率领唐军与铁勒九姓的十三位勇士对峙。这些回纥战士身披狼皮,手持弯刀,胯下战马嘶鸣,气势汹汹,似要将唐军彻底碾碎。薛仁贵从容不迫地抽出三支特制的穿甲箭,箭头上闪烁着幽蓝的光芒,这是长安工匠精心打造的利器,专门用来穿透游牧民族厚重的皮甲。第一箭射出,瞬间洞穿三名回纥勇士,天山北麓的云层也随之裂开。回纥萨满的战鼓声戛然而止,第二箭射断敌军帅旗,十三万联军顷刻间溃不成军。第三箭正中逃窜的首领后颈,唐军铁骑卷起漫天风雪,战场上只剩下跪地求饶的俘虏和散落一地的狼牙项链。
唐军将领郑仁泰看着绵延数里的俘虏队伍,忧心忡忡。十三万俘虏每天的粮食消耗高达三千石,而唐军的粮草仅够半个月之用。薛仁贵用带血的积雪擦拭面庞,俘虏营地里传来宰杀战马的悲鸣,这些草原人正用仅剩的粮食烹煮马肉,锅中翻滚的马肉呈现出令人不安的粉红色。
夜幕降临,薛仁贵在军帐中将虎符重重地掷在沙盘上。九姓铁勒三十年来七次叛乱的旧账历历在目,贞观四年突厥降而复叛的教训也让他记忆犹新。他用沾满血水的笔在羊皮卷上写下“永绝后患”四个大字,帐外的士兵看到将军的身影在帐篷上拉得老长,如同地狱修罗。
铁勒公主被押入军营时,薛仁贵正在擦拭他的方天画戟。这位年过半百的将军凝视着这位年轻的女子,心中涌起二十年前太原城破时,他从乱军中救出的胡姬的回忆。公主颈间的绿松石项链在火光中闪耀,如同当年胡姬自刎时溅在他铠甲上的血珠。
长安的御史台很快收到了密报,弹劾薛仁贵的奏章如雪片般飞向皇宫,但唐高宗李治却悠闲地把玩着西域进贡的夜光杯,杯中美酒映照着他深沉的算计:这位曾救过自己性命的将军,正利用“好色”的罪名为自己构筑庇护。
契苾何力主动请缨前往安抚铁勒,皇帝在诏书上加盖了“如朕亲临”的印章。契苾何力率领五百精骑进入铁勒营地,此时萨满正在焚烧疫病的牛羊。这位出身铁勒契苾部的将军深谙草原部落的祭祀习俗,他命人抬出九姓先祖的狼头图腾,在二百多名贵族下跪之时,唐军弩箭射穿了他们后背的狼形纹身。“叛乱者已除,其余无罪。”契苾何力的宣告随风飘散,但幸存的铁勒人发现,所有能够背诵《突厥碑文》的老人都不见了。唐军在敖包下挖出了三丈深的深坑,掩埋的除了尸体,还有刻着古突厥文的青铜祭器,这比单纯的杀戮更彻底地抹去了一个文明的印记。
凯旋而归的薛仁贵在洛阳郊外建造了一座寺庙,大雄宝殿的壁画上,三支金箭射穿了三个青面獠牙的恶鬼,而偏殿的暗格里藏着铁勒公主的狼牙项链。当香客赞叹“三箭定天山”的功绩时,老将军总是注视着壁画角落:那里画着一个怀抱婴儿的胡妇,正从血泊中向断箭爬去。
契苾何力晚年常告诫子侄:“草原上的草,割得越狠长得越旺。”但他始终没有说出这句话的下半句,那些被他亲手掩埋的突厥文字,成了中原史官笔下“蛮夷归化”的最好注脚。两位将军的“暴行”,实则是帝国边疆统治的精密策略。
七十岁的薛仁贵在雁门关咳血而亡,而幸存的铁勒部落却用汉语演唱着《秦王破阵乐》。天山脚下的万人坑早已被牧草覆盖,只有游方僧侣的诵经声,超度着那些难以分辨是唐人还是胡人的亡魂。长安的史官轻描淡写地将“杀降”改写成“靖边”,“纳妾”变成了“和亲”,只有西域商队的驼铃声中,还流传着这位白袍将军与草原公主的禁忌之恋。“三箭定天山”的战役,《旧唐书》中仅以十四字概括:“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而那些消逝在历史尘埃中的十三万亡魂,如同敦煌壁画上褪色的朱砂,永远沉默在盛唐的辉煌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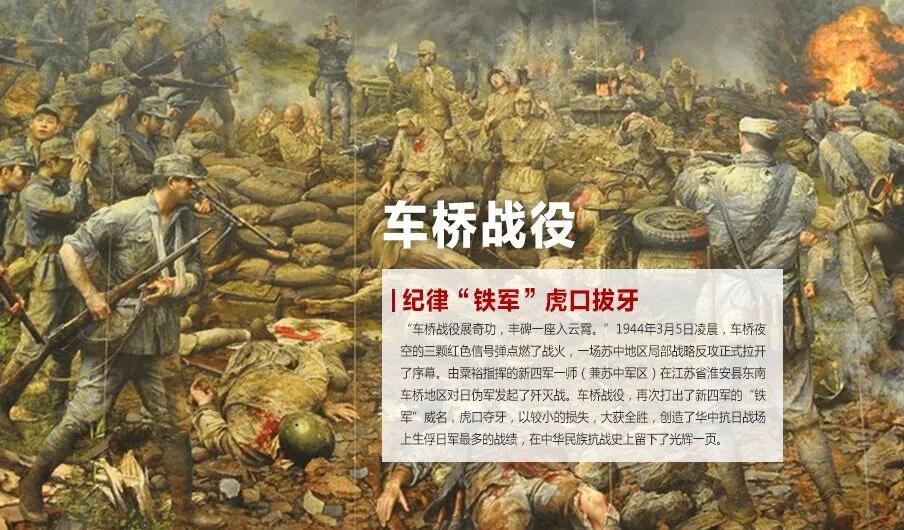





桥桥
慈不掌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