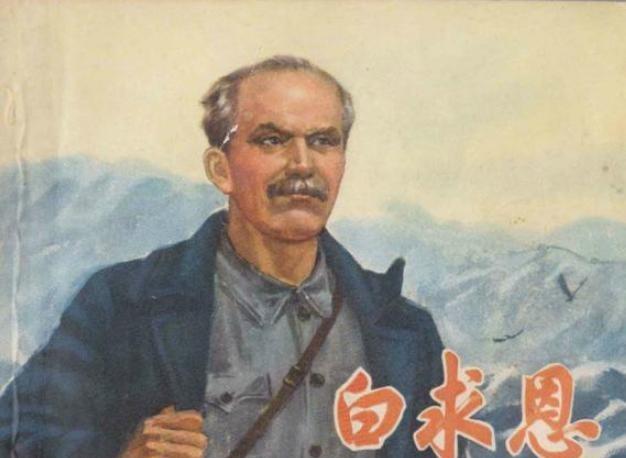1944年,战友给钟炳昌介绍对象:白求恩医科学校的校花,要不要? “1944年9月的最后一个夜班,你到底见不见那姑娘?”丁荣旋把杯子重重搁在木箱上,灯芯跳了一下,把钟炳昌的侧脸映得忽明忽暗。那个瞬间,炮火声在山后沉闷地闷了一响,像催促的鼓点。 钟炳昌没立刻回答。他刚接到调任第35团政委的命令,行军袋还摊在脚边。长征、反“围剿”、百团大战,一桩桩、一件件,全塞在29岁的脑袋里。他自认是个把生死看得比婚姻还简单的人,可战友一句“白求恩医科学校的校花”却像冷不丁的一拳,打在心窝:少年时悄悄幻想过的温暖,原来真的能与枪声共存? 第二天的送别饭桌多了一碟红烧肉和一瓶枣酒,已算奢侈。散席后,丁荣旋夫妇把他拐进土墙小屋,几句家常就切入正题:姑娘叫张曼,行唐县人,二十二岁,学医,前线随队。丁荣旋笑眯眯:“人聪明,腿脚快,唱《松花江上》能拉三调,你要是再磨蹭,就落别人家了。” 说实话,钟炳昌在女人面前有点“木”。当年在遵义一带,女卫生员递水,他都急得耳根发烫。可那夜,他独步在石子路上,忽听自己心里有节拍:年龄到了,组织也默许团职干部成家,再遇见合适的难。于是,第三天傍晚,他提着油灯去了医护驻地。 狭窄土屋里,张曼在抄病例。听到脚步,她抬头:“钟政委?”一句问好像细线,把尴尬扯成了笑。钟炳昌“自我介绍”没说两句就绊了词,倒逗得张曼笑出声。短短半小时,他们从“你伤过几次”聊到“你家几口人”,最后一句定音:“革命路远,要不要结伴?”张曼点头,油灯火苗稳了一下,这段战火中的姻缘便算结下。 1945年春,平山县小米峪村,新娘着灰布军装,新郎披缴获军大衣,证婚人是团长。鞭炮没有,用步枪鸣了三声礼;喜糖不足,煮了整锅高粱米。张曼悄悄对姐妹说:“这辈子若能把他送回家乡,就算圆满。” 新婚不过五年,局势骤变。1950年10月22日,天津稻谷扬花,钟炳昌被紧急召回军部——66军即刻东调安东。军部只有一句话:“任务到前线听高岗司令安排。”深夜回家,他只是摸了摸熟睡的孩子,又一次整背包。张曼没掉眼泪,可当列车汽笛拖着长音离站,她突然红了眼眶。这是她从医上阵以来第一次哭,她明白:跨过那座桥,也许就剩下一枚牵挂。 66军第四天抵鸭绿江南岸,补给单薄,衣被残旧。有人纳闷:“这像打仗前的准备?”钟炳昌把门帘掀开:“咱们在太原城墙上插过旗,难道渡江就发怵?”一句话,憋得战士们把疑虑咽进喉咙。26日夜,大桥上灯火全灭,脚步声杂乱却坚定——他们成为第五批志愿军,前后相差不过六天。 随后连打四役。第三次战役前,天寒地冻,补给更紧。12月31日晚,师部找不出半袋整米,钟炳昌却拿勺敲锅:“别沮丧,有粥就能过年。”那一锅稀粥,混着冰雪融水,却被战士们喝出了年味。有人嚷:“要是天津的小麦在就好了!”这话让钟炳昌愣神——天津的地里,张曼正和生产队抢收,他知道。 1951年3月,66军归国休整。火车驶进山海关时,钟炳昌隔窗望到月台,张曼正站在人群里,医用口罩遮不住笑。两人没拥抱,只对视一秒,便各自忙工作。有人打趣:“老钟,你媳妇管得住你?”他笑:“不,她懂我。” 休整期,他升任师政委,后又兼天津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家搬到海河边,日子算安稳。可老俩口仍穿旧中山装。孩子回忆:“父亲七十年代还穿草鞋,母亲补补再补。”钟炳昌说:“军装有补丁,心里就记得苦日子。” 1988年,他确诊癌症。医生犹豫着告诉张曼,张曼却先笑:“把病情瞒他,他反而胡思乱想。”钟炳昌得知后拍拍病历:“打过那么多仗,只当又一仗。”化疗期间,他仍让张曼把旧笔记本递来,记录长征口述资料。病奇迹般缓解,医生感叹“心态也是药”。 1999年,癌症复发,治疗同样艰难。钟炳昌躺在病床上,轻声对老伴说:“当年那晚你要是没笑,我可真不知道怎么办。”张曼握着他的手:“你那傻样子,我到现在都记得。”窗外树叶沙沙,像极了1944年那个夜路微风。 两年后,他安然离世。整理遗物时,子女在一个旧铝盒里翻出两封发黄的信:一封写于1944年调任途中的马背上;一封写于第一次战役前的防空洞。信不长,字迹歪斜——却把一个军人的大半人生浓缩成一句话:“惟愿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