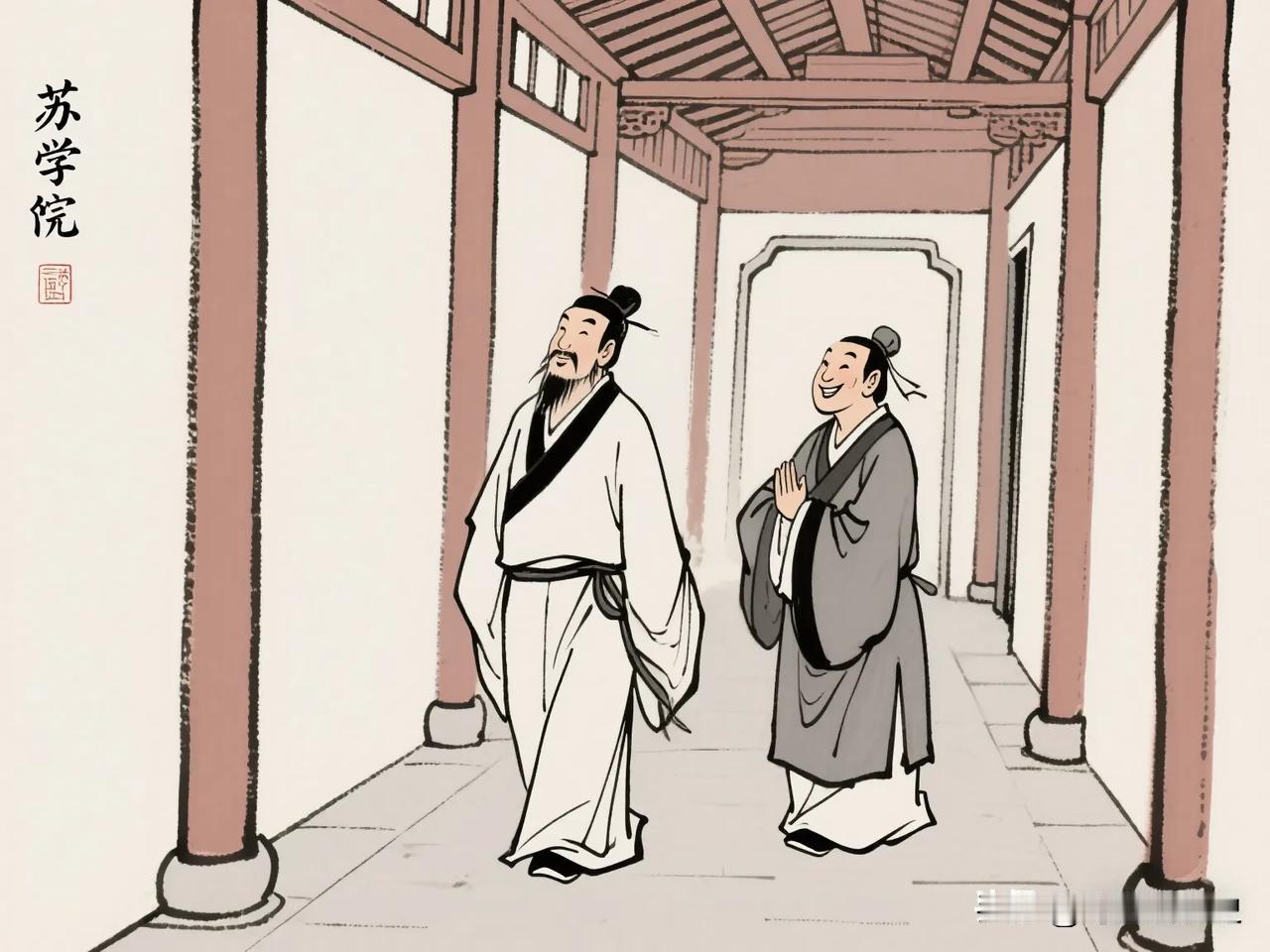正史上最令人费解的人,高俅,《宋史·佞幸传》中钉死的奸臣,徽宗朝权势熏天的“六贼”之一,其名与“祸国殃民”几成同义。他弄权营私、排挤忠良的劣迹斑斑在册,声名早已在士林与民间狼藉不堪。然而,翻阅散落于故纸堆的宋人笔记,一个与这固化形象格格不入的细节却悄然浮现:当昔日的恩主、名满天下的文豪苏轼及其家族在党争倾轧中零落成泥、艰难度日时,正是这位权倾朝野、世人唾骂的“奸佞”高俅,默默伸出了庇护之手。这庇护,持续经年,细致入微。一个公认的“反派”,为何独独对早已失势、甚至堪称其政治对立面的苏氏一门,倾注了如此长久而坚定的回护?这看似悖逆常理的举动,其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缘由与力量? 苏轼与高俅,一为光耀千秋的文坛巨擘,一为《水浒传》中奸佞弄权的代名词。两人命运的交集始于元祐年间汴梁城苏学士府中。彼时高俅不过一抄写小吏,因写得一手好字,被苏轼收在门下做些文墨差事。苏轼待人向无贵贱之别,对身边仆役亦多存照拂之心,高俅自然也在其列。史书未详载苏学士如何厚待于他,但这份情谊的种子,却在高俅心中悄然深种。 元祐八年,政局翻覆,苏轼被远谪岭南。临行前,他思及高俅前程,亲笔修书一封,荐其往驸马都尉王诜府中谋职。正是这一纸荐书,悄然扭转了高俅的命途。王诜府中往来者皆一时显贵,其中便有端王赵佶。高俅因蹴鞠精妙,竟得端王青眼,从此一步踏入天家门槛。待赵佶登基为徽宗,高俅亦随之平步青云,官至殿前都指挥使,权倾一时。 苏轼兄弟宦海浮沉,身不由己。绍圣年间,新党再起,苏轼贬至荒远的惠州、儋州,苏辙亦被远放雷州。苏门子弟散落四方,处境艰难。就在此时,显赫的高俅并未袖手旁观。史载,他对人言:“此苏学士子孙也,吾不敢慢待。”言语间,旧日恩情宛然可见。 苏辙一家困居颍昌时,高俅闻知,特遣人送银钱周济,解其燃眉之急。苏辙长子苏迟后来能重返仕途,亦多得高俅暗中斡旋之力。至于苏轼三子苏过,在父亲身后奉母北归,家计萧条。高俅念及故主恩情,对苏过多方照拂,助其度过窘境。 尤为世人感慨的是高俅对苏氏家族的整体护持。苏轼兄弟名满天下,却也树敌众多。每逢政争波谲云诡之际,高俅常以手中权位,为苏氏子弟筑起一道屏障。据宋人笔记所传,某次朝廷清查“元祐党人”亲族,风声鹤唳,苏家岌岌可危。正是高俅在御前婉转进言,苏门后人方得保全,免遭株连之祸。史书虽未明载,然此等传闻在士林间流传甚广。 高俅一生所为,史家自有公论。《宋史》将其列于《佞幸传》,指其“恃宠营私,军政弛废”。然其善待苏氏后裔一事,却如暗夜微光,烛照着人性中未泯的良知。野史《鹤林玉露》曾记其言:“人言我奸佞,然苏公恩义,未尝一日忘怀。”纵使史笔如铁,亦难全然抹杀这段情义。 高俅之报恩,固然与其权位相连——若无显赫身份,何来庇护之力?然而,富贵而忘故交者,古今滔滔皆是。当苏轼兄弟零落天涯,昔日门庭若市早已化为门前冷落,高俅却能在权势熏天之际,对沦落故主之后施以援手,这份“未敢忘本”的持守,在利欲倾轧的官场中,便显得格外珍贵。 历史的评价向来复杂难言。高俅的名字永远与“六贼”之列相连,这无可更改。然其对苏氏一门数十年的回护,恰似浑浊河流中兀自清澈的一脉支流。人性之复杂,本非“忠奸”二字所能囊括。正因如此,这段情谊穿越千年烟尘,仍能让人窥见:纵然是史册中的“恶人”,胸中亦存着一块未冷之处,懂得在长夜中为故人之烛,续上一点微光——这光虽照不透大时代的暗影,却足以映亮人心深处那点不易被磨灭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