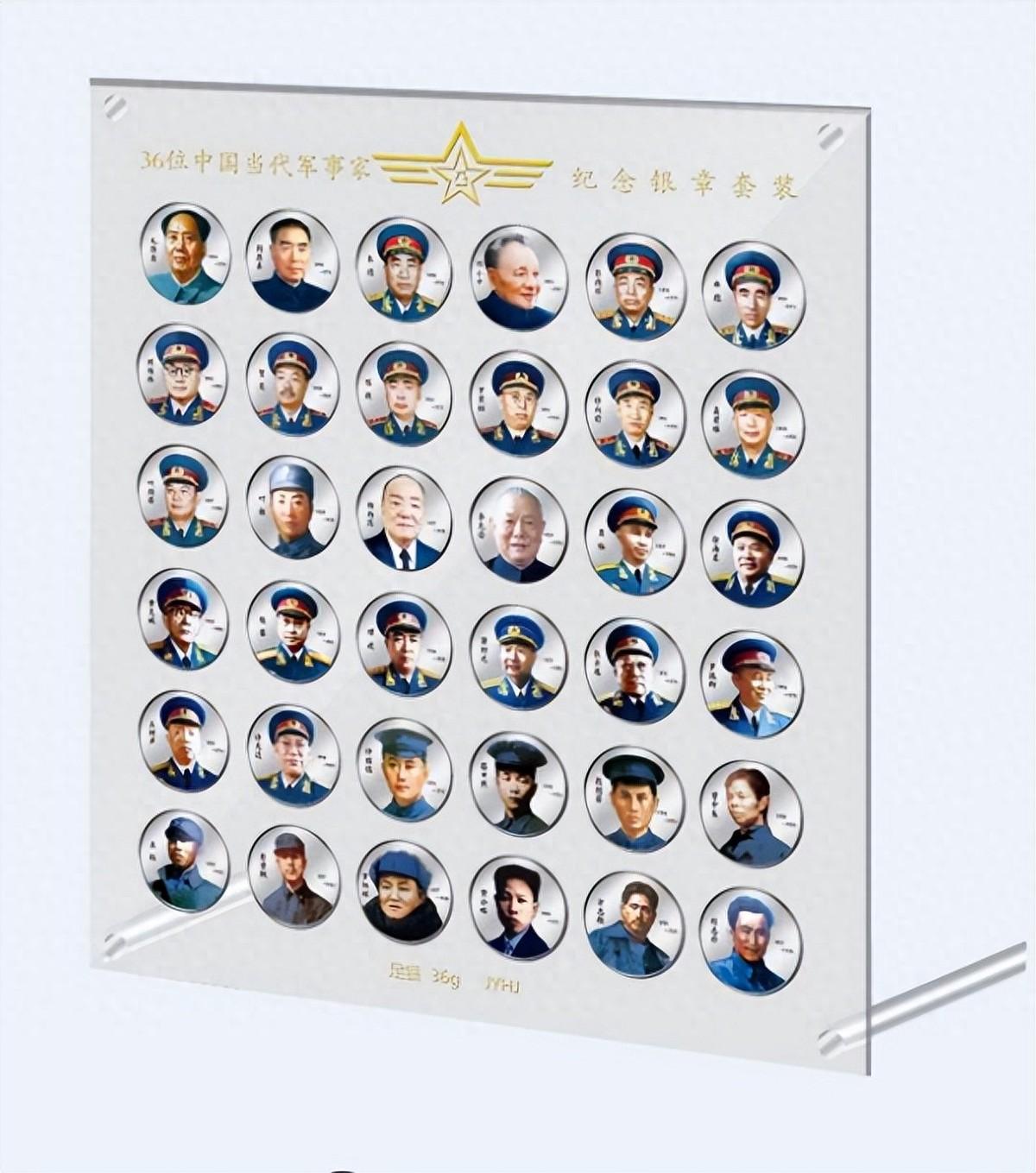1956年,傅作义请求毛主席释放陈长捷,也几次去功德林探望他,但陈长捷每次见了傅作义都是非常生气。
1957年,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头一次向战犯家属敞开大门,这个消息传到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耳朵里,但他心里只惦记着一个人——陈长捷,他过命的兄弟,如今却是一名战犯。
可是,当傅作义满怀复杂情绪提出探视时,却碰了一鼻子灰,陈长捷断然拒绝,还捎来一句锥心的话:“你在北平谈判,让我死守天津,结果你成了起义将领,我成了阶下囚,这辈子,我不会原谅你!”
这对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究竟有什么样的恩怨,才会在历史的岔路口走向截然相反的命运?
在旁人反复劝说下,陈长捷最终还是勉强同意见面,陈长捷看着眼前西装革履、面色红润的傅作义,再看看自己一身囚服、两鬓斑白,积压多年的委屈和怨恨瞬间决堤,他打断傅作义的寒暄,颤抖着声音质问着自己的遭遇。
面对昔日兄弟的痛苦,傅作义满心愧疚,他坦言,北平和平起义事关重大,在没和共产党达成最终协议前,这是绝对机密,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风险。
然而,傅作义本以为协议一签,就能立刻通知陈长捷一同起义,谁知战局变化太快,解放军提前攻陷天津,导致陈长捷兵败被俘,对此,他承认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傅作义接着说,他从未忘记自己的部下,起义前,他专门召开军事会议,宣布和平改编,并给不愿留下的人发足路费,任其去留。
起义后,傅作义更是多次向中央和毛主席恳请,希望能赦免包括陈长捷在内的被俘将领,甚至在1956年的政协会议上,两次郑重提议释放他们。
听完这番肺腑之言,陈长捷心中郁结多年的怨气才渐渐散去,他紧紧握住傅作义的手,轻声说了句:“我知道了,谢谢。”兄弟二人,时隔近十年,终于在监狱里冰释前嫌。
要看懂这场命运的交错,还得回到他们相识的岁月,傅作义和陈长捷都毕业于保定军校,又一同在晋军阎锡山麾下共事,从军阀混战到抗日战争,是实打实的生死之交。
不过,两人的仕途却大不相同,傅作义官运亨通,一路高升,最终成了手握重兵的华北“剿总”司令,而陈长捷虽以治军严明、擅打硬仗闻名,却长期担任虚职。
直到傅作义力排众议,向蒋介石力荐,陈长捷才当上天津警备司令,对此,陈长捷感激涕零,拍着胸脯保证:“总司令放心,有我在,天津万无一失!”他上任后也确实拼尽全力,修筑工事,征调壮丁,把天津打造成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
然而,平津战役的棋局,从一开始就不对等,面对解放军百万大军压境,傅作义内心盘算复杂,他一边将部队龟缩在平津铁路线,一边又错误判断,认为解放军需要休整,想借机在战场上捞点“胜利”,好为自己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
但傅作义甚至暗藏私心,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放在后方,却将蒋介石的中央军推到前线,为自己留好了和谈或西撤的后路,而他的这些盘算,都被他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毛主席。
与此同时,被蒙在鼓里的陈长捷,则完全是另一番心态,出于对老大哥的绝对信任和军人的天职,他按照傅作义的命令,准备死守天津。
在加上蒋介石为防止傅作义起义,不断给他写信打气,并提供大量援助,更让陈长捷信心倍增,自认十几万大军守城绰绰有余。
历史的车轮,显然不会按他们的剧本走,林彪率领的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张家口和新保安,一举全歼傅作义的王牌第35军,彻底斩断了他西撤的念头,紧接着,塘沽、天津、北平被团团围住。
为了敲醒傅作义,1949年1月,东北野战军开始猛攻天津外围,林彪和罗荣桓多次致信劝降,但陈长捷错估形势,回信拖延,声称“放下武器乃军人之最大耻辱”。
在最后通牒期限已过时,陈长捷致电北平请示,得到的答复还是那句模棱两可的话:“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
毛主席早已看穿了傅作义的侥幸心理,果断下令攻打天津,1月14日,总攻开始,解放军仅用十几个小时就攻入城内。
即便如此,陈长捷仍在地下指挥室里指挥巷战,当晚,他再次致电北平,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传来的指示依旧令人费解:“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了!”
而短短几小时后,解放军战士冲进指挥所,陈长捷才在绝望中举手投降,天津的解放,也彻底打碎了傅作义的谈判筹码,迫使他最终宣布北平和平解放。
这对兄弟的命运,从此天差地别,傅作义作为起义功臣,官至水利部部长,位列国家领导人,而陈长捷则作为战犯,在功德林监狱开始了漫长的改造生涯。
不过,尽管两人和好,陈长捷并未立刻获释,直到1959年,他才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走出功德林,后被安排在上海市政协工作,安享晚年。
【信源】《李宗仁回忆录》自我毁灭的西南保护战 1370页-1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