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那天,体育馆里坐满了人,我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看着我追了4年的校花林倩穿着学士服走上讲台。
她对着话筒,开始说那些关于青春和未来的漂亮话,突然她话锋一转,矛头直指向我:“有些人,最重要的是认清自己,要知道,什么是你能碰的,什么是你永远够不着的。
“总有那么些癞蛤蟆,妄想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你不累吗。”
我没有回应她的话,而是默默上台领取了属于我的特别奖学金。
01
6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香味和离别的气息,从滨海大学体育馆巨大的天窗吹进来,却吹不散场子里那种紧绷的气氛。
今天就是毕业典礼了。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四年大学生活的结束,也是走向社会的开始。
可对我来说,陆远,这就像一场公开的审判大会。
校长在主席台上讲完了关于梦想和未来的那些套话,现在轮到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了。
苏雨桐穿着合身的学士服,慢慢走上台去。
她不愧是滨海大学公认的校花,皮肤白得发光,五官精致得像画出来的一样,连学士帽都压不住她那头又黑又顺的长发。
她站到演讲台后面的时候,整个体育馆的空气好像都变甜了。
我坐在观众席最偏僻的角落里,旁边的同学都在小声议论,讨论着苏雨桐今天有多漂亮,或者她那份早就到手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录用通知。
“大家好,我是经管学院的苏雨桐。”她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出来,清脆好听,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自信和亲切,“四年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曾经为了写论文在图书馆通宵,也曾经为了社团活动在操场上流汗。”
这是标准的优秀毕业生发言,内容空洞却很励志,充满了对大学生活的回忆。
我低着头,手指头无意识地在手机屏幕上划拉着,屏幕上是我正在写的一个物理模拟引擎的程序代码,无数行绿色的字符像瀑布一样往下流,正在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
这比听苏雨桐讲话有意思多了。
我追了她整整四年,从大一开学在新生接待处第一眼看到她开始,我就成了滨海大学人人都知道的“跟屁虫”。
送早餐、占座位、修电脑、帮她整理课程论文的思路……只要她一句话,我几乎随叫随到。
我的室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王浩,不止一次捶着我的胸口说:“老陆,你这是图什么啊?就凭你这脑子,用在学习上能拿国家大奖,用在苏雨桐身上,就只能换来一句‘哦,谢谢’?”
我图什么呢?
也许是图她偶尔一次不经意的微笑,也许是图她在我帮她解决了一个复杂的数据模型之后,眼睛里闪过的那一点点依赖。
那种感觉,就像是给一个黑白色的程序世界,点亮了一个彩色的小光点。
“……但是大学教会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认清自己。”台上的讲话忽然转了方向,苏雨桐的语调微微提高了一点,带上了一丝尖锐的味道。
全场的吵闹声好像都变小了一些,大家都感觉到,重点要来了。
“它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我们能得到的,什么是我们永远也够不着的。”她的目光像有实质一样,穿过几千个人的头顶,准确地找到了我坐的角落。
我抬起头,对上了她的视线。
那双曾经让我心动不已的眼睛里,现在装满了冰冷的、高高在上的打量。
周围的同学开始骚动起来,不少人顺着她的目光朝我看过来,脸上带着看热闹的表情。
“总有一些癞蛤蟆,”她停了一下,红红的嘴唇轻轻张开,说出来的每个字都像带着毒的冰刺,“妄想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四年了……”
她几乎要念出我的名字,又好像没有。
但所有人都知道她说的是谁。
“陆远,你不觉得累吗?”
轰的一声!
整个体育馆好像被扔了一颗炸弹。
压抑的、控制不住的笑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那些目光,不再是小针,而是变成了一把把大锤子,要把我砸进地底下,砸成一滩烂泥。
我旁边的王浩猛地站起来,一张胖脸涨得通红,拳头攥得咯咯响,好像下一秒就要冲上台去。
我伸手,轻轻拉住了他的衣服角,摇了摇头。
我没有看苏雨桐,也没有看周围的任何人。
我只是平静地低下头,继续看着手机屏幕上的代码。
累吗?
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无数遍。
在冬天的清晨,提着热豆浆在她宿舍楼下等一个小时,她却发消息说和室友出去吃了。
在她参加辩论赛的前一天晚上,我帮她查资料、整理论点到凌晨四点,她却在获奖感言里感谢了所有人,就是没提到我。
在她生日的时候,我用省下来的钱买了一条她提过一次的项链,她收下之后,我再也没见她戴过。
这些时候,我都会问自己,累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但比累更强烈的,是一种几乎算是偏执的、属于程序员的固执。
我总觉得,只要我不断优化“输入”——就是我的付出,总有一天能得到我想要的“输出”——也就是她的心。
现在看来,我错了。
我的算法,从一开始就有根本性的逻辑错误。
苏雨桐不是一个等着被攻克的程序,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看不起我的人。
“……所以,同学们,认清现实,脚踏实地,才是我们走向成功的唯一方法,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苏雨桐用一句漂亮话结束了她的“审判”,弯腰鞠了个躬走下台,全场响起了礼貌但稀疏的掌声,掌声里夹杂着更多意味深长的偷笑。
她下台的时候,经过我坐的这片区域,没有看我,但那高高抬起的下巴,像一只骄傲的白天鹅,宣告着她的胜利。
王浩气得全身发抖:“老陆!这你都能忍?她……她这是把你的脸扔在地上踩啊!她那些破论文,哪篇没有你的心血?她那个五百强的录用通知,面试用的PPT里的数据模型,不是你熬了三个通宵帮她弄出来的?”
“算了,胖子。”我关掉手机屏幕,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算了?”王浩提高了嗓门,“这怎么能算……”
他的话被主席台上传来的新声音打断了。
“下面,我们要颁发今年一个特别的奖项。”说话的是头发花白的副校长,物理系的权威人物,周院士。
“这个奖,不属于任何一个学院的常规评选,而是由学校董事会和几位特聘院士一起提名,奖励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毕业生。”
体育馆里再次安静下来。
大家都好奇,滨海大学还有这种级别的奖项?
周院士清了清嗓子,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欣赏和激动。
他打开手里的红色荣誉证书,用一种严肃的、不容置疑的语调,念出了那个让全场瞬间死寂的名字。
“获奖者——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陆远!”
那一刻,时间好像停止了。
所有的笑声、悄悄话、同情、鄙视,都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掐住了喉咙。
我没有动。
直到周院士又喊了一声:“陆远同学,请上台。”
聚光灯,那道刚才还照着苏雨桐的、代表着荣誉和胜利的光束,慢慢移动,越过几千张错愕的脸,最后,稳稳地照在了我身上。
我默默地站起来,在无数道混合着震惊、疑惑、不敢相信的目光中,整理了一下身上便宜的学士服,迈开步子,朝着那个所有人都在看的主席台,一步一步,稳稳地走了过去。
02
从我座位到主席台的距离,差不多有一百米。
但在这个时候,这条铺着红毯的路,却长得像我那被公开羞辱的四年。
我能清楚地听见自己脚下每一步发出的轻微声音,也能感觉到身后,王浩那激动到几乎停住的呼吸。
更多的,是那几千道目光的重量。
它们不再是尖针或锤子,而是变成了无数个大问号,飘在空中,压得人喘不过气。
陆远?
是那个陆远吗?
那个给苏雨桐当了四年“备胎”的陆远?
那个刚刚被苏雨桐说是“癞蛤蟆”的陆远?
我走得很稳。
四年里,为了给她占图书馆的座位,我几乎每天都第一个走过这条路。
就算闭着眼睛,我也不会走错。
主席台上的领导和院士们,表情各不相同。
几位校领导脸上带着公式化的微笑,但眼睛里透着明显的陌生和一点尴尬。
很明显,在今天之前,他们对我这个名字没什么印象。
而周院士,还有他身边几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则用一种欣赏的、甚至可以说是欣慰的眼神看着我。
我没有看观众席,但我能准确地找到苏雨桐坐的位置。
我能想象出她现在的表情,那张永远保持着完美弧度的脸上,大概第一次出现了无法控制的裂痕。
她所有的骄傲、优越感,在周院士念出我名字的那一刻,应该就已经碎成粉末了。
“陆远同学,祝贺你。”周院士亲自把那本烫金的红色证书递到我手里。
证书很重,上面的每个字都好像有千斤重。
“滨海大学‘启明星’特别奖学金。”
我接过证书,低声说了句:“谢谢周院士。”
我的声音通过他面前的麦克风传了出去,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体育馆里,清楚得像在耳边说话。
周院士拍了拍我的肩膀,转向全场,声音响亮而有力:“很多同学,甚至很多老师,可能都对陆远这个名字感到陌生,这不奇怪,因为大学四年里,他既没有当过任何学生干部,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热闹的社团活动。”
台下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
这些话,无疑证明了我“边缘人”的身份。
“但是,”周院士话锋一转,语气中充满了自豪,“陆远同学把他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最需要智慧和汗水的地方——科学研究。”
他拿起另一份文件,开始宣读。
“大二那年,陆远同学独立完成的‘关于高维数据降维的非线性映射算法优化’,其核心代码被国家某重点实验室采用,用于‘深空’项目的部分数据预处理。”
“大三那年,他作为核心成员,参加了我的‘量子纠缠态下的信息保真度’课题研究,提出的‘多路径补偿模型’,从理论上解决了困扰我们团队将近两年的一个关键难题,相关论文,已经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
“大四上学期,他用匿名方式参加了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以单人组队的形式,拿到了亚洲区预选赛的金牌。”
周院士每念一条,台下的寂静就加深一分。
从最初的震惊,到疑惑,再到觉得不可思议。
几千名学生,包括那些自以为是的学霸们,现在脸上的表情,就像在听一部玄幻小说。
SCI?
PRL?
ACM金牌?
这些名词,对大部分本科生来说,就像是遥远星空里的传说。
很多人努力四年,能发一篇核心期刊就够吹嘘半辈子了,而这些,竟然是一个在他们眼里默默无闻,甚至有点“窝囊”的同龄人完成的。
我注意到,苏雨桐坐的那片区域,已经完全乱了。
她的几个闺蜜,正用一种见鬼了的表情看着她,又看看台上的我,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
而苏雨桐本人,她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能看到她放在膝盖上的手,在不受控制地微微发抖。
她当然知道这些事。
那篇关于数据降维的论文,初稿是我写完后,她拿去说“帮我改一下”,结果被她经管系的导师看到,惊为天人,差点要推荐给自己的博士生。
量子纠缠的课题,有一次我为了赶进度在实验室熬了个通宵,她早上给我送来一杯咖啡,温柔地说“别太累了”,就那一杯咖啡,支撑了我后面整整一个星期的高强度工作。
至于ACM,她更知道了。
因为那段时间我几乎“消失”了,她发了两次脾气,说我对她不够上心。
我没法解释,因为参赛协议里有保密条款。
原来,我那些“不累”的时刻,那些支撑我走下去的“彩色小光点”,在她眼里,不过是我众多“怪毛病”中的一个。
她知道我在做这些,但她从来没想过,这些东西的价值。
或者说,她潜意识里,拒绝承认这些东西的价值,因为那会打破她对我“癞蛤蟆”的设定。
“……基于以上突出的学术成就,”周院士的声音再次把我的思绪拉回来,“经学校董事会和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一起商量,我们决定,授予陆远同学‘启明星’特别奖学金,奖金十五万元。”
“同时……”他在这里故意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我身上,带着一点长辈的调皮,“……陆远同学已经获得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保送资格,将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祝贺他!”
十五万!
保送北大!
直博!
如果说前面的学术成就还只是让大家不明觉厉,那么这三个词,就像三颗重磅炸弹,在每个人的脑子里炸开了花。
这是最简单、最直接、也最有效的现实冲击。
体育馆里,死寂被彻底打破了。
雷鸣般的掌声,从稀稀拉拉,到整齐划一,最后变成了山呼海啸。
这掌声,不再是出于礼貌,而是发自内心的震撼和佩服。
那些曾经的嘲笑和鄙视,在“北大直博”和“十五万奖金”的绝对实力面前,显得那么可笑,那么苍白无力。
我站在舞台中间,沐浴在灯光和掌声里,手里拿着证书和一张巨大的、代表着十五万奖金的红色牌子。
我终于抬起眼睛,穿过晃动的人群,再一次,看向苏雨桐。
这一次,她没有躲开。
她抬着头,脸色白得像纸,那双漂亮的眼睛里,不再有冰冷和打量,取而代之的,是汹涌的、无法掩饰的后悔、震惊,和一丝……我从来没见过的,叫做“恐慌”的情绪。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碰到一起。
四年了。
这是我第一次,在她眼睛里,看到了我自己。
一个清晰的、不再模糊的、让她无法忽视的,陆远。
03
掌声持续了很久。
我对着台下深深鞠了一躬,没有说任何获奖感言,转身准备下台。
周院士却拦住了我,把他面前的话筒朝我推了推,示意我说几句。
我知道,这是他给我的机会。
一个让我反击的机会,一个让我把刚才受到的所有屈辱,加倍还回去的机会。
全场几千人,现在也都屏住呼吸,等着我的“复仇宣言”。
他们期待着我痛骂苏雨桐的虚荣和无知,期待着一场痛快的打脸好戏。
连我自己都以为,我会这么做。
我握住冰凉的话筒,目光再次扫过台下。
我看到了王浩激动到涨红的脸,他正用口型无声地对我说:“说啊!老陆!怼她!”我也看到了苏雨桐,她身边的闺蜜已经像躲瘟疫一样,和她拉开了一点距离。
她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像一座快要融化的雪雕。
那张曾经让我日思夜想的脸,现在写满了脆弱和崩溃。
那一瞬间,一种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
愤怒吗?
当然有。
但更多的,是一种巨大的、空荡荡的疲惫感。
就像你花了四年时间,精心写了一百万行代码,只为了实现一个特定的功能。
你调试、优化、为它投入了全部心血。
最后你成功了,但就在成功的那一刻,你忽然发现,这个功能本身,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一百万行代码,瞬间变成了一堆没用的字符垃圾。
“谢谢学校,谢谢周院士。”我的声音通过音响系统,在体育馆里回荡,“我没什么想说的。”
说完,我放下话筒,在周院士略带惊讶的目光中,走下了主席台。
全场一片哗然。
所有人都没想到,等来的不是高潮,而是这样一个平淡的结尾。
这就像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让所有准备看热闹的人都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憋闷。
我没有回到原来的座位,而是直接走向了体育馆的出口。
王浩立刻跟了上来,一把搂住我的肩膀,激动得话都说不清楚了:“老陆!太牛了!你看到了吗?苏雨桐那张脸,跟调色盘似的!太他妈解气了!不过……你就这么算了?刚才在台上,你应该……”
“应该说什么?”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喧闹的舞台,“说她不识货?说她虚伪爱钱?然后呢?让全校人看她的笑话,让她身败名裂,大学四年都抬不起头?”
“她活该!”王浩气呼呼地说。
“也许吧。”我淡淡地说,“但那又怎么样呢?证明我比她更高尚?还是证明我这四年的付出,是值得的?”
王浩愣住了。
我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胖子,你不懂,当一件事,你需要通过羞辱另一个人来证明它的价值时,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不值钱了。”
我的四年,我的付出,我曾经以为的爱情,在苏雨桐说出“癞蛤蟆”那三个字的时候,就已经彻底归零了。
现在再去做任何事,都像是在折腾一具尸体,一点意义都没有。
走出体育馆,外面阳光刺眼,照得人眼睛发疼。
手机在口袋里疯狂震动,不用看也知道,学校的论坛、贴吧、各种班级群,现在一定已经炸开锅了。
我掏出手机,没有理会那些99+的未读消息,而是打开了通讯录,找到了那个置顶了四年的名字——“雨桐”。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几秒钟。
曾经,这两个字对我来说,是傍晚天边绚烂的云彩,是雨后初晴的新鲜空气。
而现在,它只是两个普通的汉字。
我按下了删除键。
确认。
就在我删掉她的那一刻,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
我下意识地挂断,对方却不死心地又打了过来。
我皱着眉接起来:“喂?”
“陆远……是我。”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颤抖的、带着哭腔的女声。
是苏雨桐。
她的声音,不再是台上那种清脆自信,而是充满了慌乱和卑微,像一个迷路的小孩。
“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哽咽着问。
我有点莫名其妙:“我做什么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她的声音猛地提高,带着一丝歇斯底里的质问,“你拿了那么多奖,发了那么多论文,你就要去北大了……你为什么一个字都不跟我说?!”
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又荒唐又可笑。
“告诉你?告诉你什么?”我冷冷地反问,“告诉你我发了SCI,让你觉得我配得上给你修电脑了?还是告诉你我拿了ACM金牌,让你觉得我给你占的座位会更舒服一点?”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着急地辩解,“我……我只是……我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你……”
“你以为什么?”我打断她,“以为我只是个除了死缠烂打,一无是处的书呆子?以为我所有的价值,就是能帮你处理那些你搞不定的功课,然后让你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一切,再在毕业的时候,当着全校人的面,把我当成你显示自己‘清醒独立’的垫脚石?”
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剩下她压抑不住的抽泣声。
“陆远,”过了很久,她才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说,“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别生我气了,好不好?我们……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吗?”
像以前一样?
我脑子里闪过她站在台上,说出“癞蛤蟆”时那冰冷的眼神。
“苏雨桐,”我的声音平静无波,“你知道一个程序里,最致命的错误是什么吗?”
她愣住了,显然没跟上我的思路。
“不是语法错误,也不是逻辑错误,那些都可以调试,可以修改。”我停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最致命的,是需求错误,当你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你写的代码再精妙,运行得再完美,最后得到的,也只是一个没人要的垃圾。”
“我们之间,就是这个错误。”
“嘟……嘟……嘟……”
我挂断了电话,把她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
世界,一下子安静了。
王浩在我旁边,听完了整个过程,现在正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好半天,才竖起一个大拇指:“老陆,以前我觉得你在第五层,现在我发现,你他妈的是在平流层啊!”
我没理他的玩笑话,抬头看了一眼蔚蓝的天空。
一只不知道名字的鸟,正展开翅膀飞向天空,冲向更高、更远的地方。
那里,才是属于我的天空。
04
毕业典礼结束后的那个下午,校园里像往常一样热闹,但我走在路上却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和我没什么关系了。
我拖着行李箱往宿舍走,路上遇到好几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同学,他们都用一种特别热情的眼神看着我,还有人主动过来打招呼。
“陆远,恭喜你啊,真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以后去了北大可别忘了我们这些老同学!”
“那个……能不能加个微信,以后说不定有机会请教问题。”
我礼貌地应付着他们,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心里却没什么波动。
这些人里,有曾经在小组作业时把最难的部分扔给我的,也有在背后议论我“就知道追女生没出息”的。
现在他们脸上的笑容真诚得有点刺眼。
王浩帮我把行李搬下楼,一边走一边嘟囔:“这些人变脸比翻书还快,以前怎么没见他们这么热情。”
我没接话,只是抬头看了看住了四年的宿舍楼。
楼门口的宣传栏上还贴着优秀毕业生的海报,苏雨桐的照片排在第一个,笑得特别灿烂。
“等等啊老陆,我去把那张海报撕了!”王浩说着就要往那边走。
我拉住他:“别去了,没意思。”
“怎么就……”王浩话说到一半,看着我的表情,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我知道他是为我打抱不平,但现在做这些事真的没意义了。
回到宿舍收拾东西的时候,手机又响了好几次,有学院老师打来的,有学校宣传部的,还有几个记者想采访。
我都以“要赶火车”为由礼貌地拒绝了。
最后打来的是周院士,他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特别和蔼:“陆远啊,手续都办好了吗?北大的张教授昨天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非常期待你过去。”
“都办好了,谢谢周院士。”我一边把最后几本书塞进箱子一边说。
“别客气,你这样的学生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周院士顿了一下,又说,“对了,有件事我想问问你的意见,苏雨桐的父亲今天下午联系我了。”
我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
“他想通过我联系你,好像是他公司那边遇到了什么技术难题。”周院士的语气有点无奈,“我没答应也没拒绝,只说会转告你,你看……”
“不用了周院士。”我平静地说,“我和她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周院士的笑声:“好,我知道了,年轻人就该这样,该断则断,对了,到北京安顿好了记得给我打个电话。”
挂了电话,我坐在已经收拾干净的床板上,看着空荡荡的宿舍。
四年的时光,最后就浓缩成了这两个行李箱。
王浩坐在我对面,难得地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说:“老陆,说真的,你现在什么感觉?是不是特别爽?特别解气?”
我想了想,摇摇头:“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觉得……该往前走了。”
是的,该往前走了。
那些过去的付出、期待、失望,都像写在沙地上的字,被毕业典礼那场大风一吹,就什么都没了。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去北京的高铁。
王浩非要来送我,在车站里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到了那边好好混,混出个人样来,让那些瞧不起你的人看看!”
我拍拍他的背:“你也是,好好工作,少打游戏。”
列车开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城市,心里忽然轻松了很多。
这个我追了苏雨桐四年的地方,这个我默默做了四年研究的地方,现在终于要离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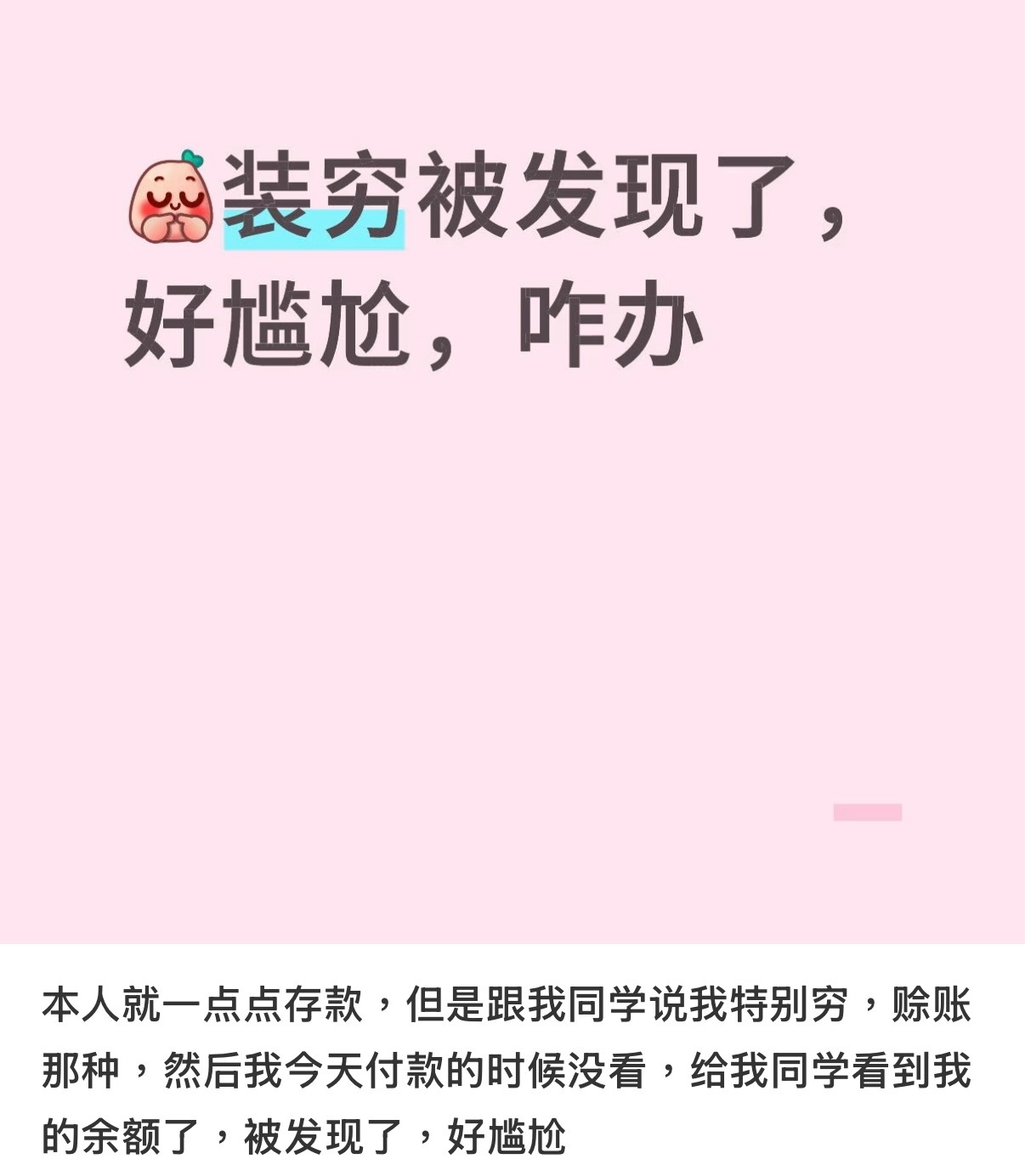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