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绕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已经连续写了三篇文章,主要讲了明朝从嘉靖晚期到万历初期文官斗狠的故事。——高拱徐阶互斗,陈以勤、殷士儋、赵贞吉等人与高拱互斗,就差“张居正与高拱”没写了。

殷士儋和高拱“皇极殿互殴”事件爆发后,殷士儋于第二年(隆庆五年)辞官致仕。挤走了殷士儋,朝中再无人可跟高拱拍桌子叫板。内阁法人代表就是高拱一人的,另外递补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高仪,加上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张居正,新一届内阁班子就这么搭建起来。
隆庆五年,是高拱人生最高光的时刻。这一年,他接任了内阁首辅,还同时身兼“吏部尚书”“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
可就是这一年,隆庆帝“嘎嘣”脆断,属于高拱的繁华转瞬即逝。
平时看似“人畜无害”的小张,早有了取代大哥的意思,岂能放过“新皇登基”这个绝妙的历史拐点。
隆庆帝是五月崩的,张居正对高拱的反击是七月开始的,反目成仇的速度比翻书还快。
曾经死皮赖脸、紧抱高拱大腿、各种表忠心的小张,立马变成了“倒高派”的扛把子。
权力是容易让人上瘾的嗑药。在权力的磁场漩涡中,根本没有仁义可言,就像一个落水之人,必须把别人往死里踩,才能不断往上爬。
“张高之争”有点像宋朝的“庆历之争”。高拱像一个守旧派,坚持守道,虽然他本人干的事与“道德”毫无关联,但不影响他的高调主张。张居正则是一个新锐派,坚持“打破揉碎”,重头再来。
很明显,张居正的理念在任何朝代都不会受到“官僚老爷们”支持。一时间,朝堂上立刻分化成为两队人马。
一伙是团结在高拱周围的守旧老臣以及勋贵世家。另一伙是以张居正为代表的中产新锐。两伙人马为了所谓的帝国出路,在庙堂上吵得不可开交,就跟大妈的“广场舞团”争夺场地一样。

作为两伙人的代言人,张居正和高拱也相互取关拉黑了对方,开始给彼此各种“下绊子”。
弹劾对方的奏折跟雪片一样,太监们每天要用小推车往李太后的慈宁宫运送。
最后的结局是,张居正完胜。
准确地说,并不是张居正取得了“张高之争”的胜利,而是高拱自讨落败。
高拱属于传统型知识分子,内心对太监有着天然的鄙视。他当年两次入阁,全是靠司礼监太监李芳和邵芳的运作。可每次入阁后,他又开始不拿太监当人看。
张居正则不同,主打一个“口碑”。三教九流,无所不交。最重要的是,他早已提前布局,巴结上了万历的发小冯保。
这都不是张居正扳倒高拱的决定因素。真正扳倒高拱的,还得高拱自己临脚一门,送了张居正一个乌龙球。
隆庆驾崩后,最悲伤的人除了他的“精神少妇”李太后,就属他的老师高拱最悲伤。既是自己的学生,还是自己的权力来源,不悲伤是假的。
但高拱在这场悲伤中,犯了两个致命错误。
一是要对冯保下手,而且要找“心腹小弟”张居正一起干这件事儿。高拱要办冯保,绝不是办冯保本人,而是想一举铲除明朝的“阉患”毒瘤。他就联络张居正说,咱俩把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给干了,一起留名青史。(应与公,共立此不世功)
他万没想到,张居正早就跟冯保尿在了一壶里,转头就把高拱的计划全盘托出。
高拱在这个时机要办冯保,铲除“阉患”,事是好事,但时机不对。李太后和万历母子刚死了当家的,他们除了依靠身边的太监,心理上还能依靠谁。这个时候办冯保,无异于是办人家“孤儿寡母”。
二是有了这个计划后,冯保和张居正团结得更加紧密。很快,高拱送来了第二波人头。他居然当着张居正的面,感慨说“十岁天子,如何治天下”。高拱这句话,原意是对大明朱家的忧心忡忡。
可是,到了张居正耳朵后,就变成了另一个风向。经张居正和冯保一番润色,传到李太后耳朵后,就变成了“十岁孩童,如何做人主”。
原本是一句忧国忧君忧民的感慨,在句式不变的前提下,稍微改动两个字,就变成了“一代权臣,威胁皇权”。
一个进士出身的官僚人精,和一个混迹皇宫的太监人精,两人合起伙来骗李太后这个“精神少妇”,那不就跟玩一样。
不论在哪个朝代,公开说了不当之话,不死也得扒一层皮。高拱的仕途就算到头了。
接下来,就差一个看似合理的程序。

正好,张居正手头有一个绝佳的“素材”——“王大臣案”。
万历元年正月,一个叫王大臣的社会青年,乔装成太监混入了宫中,被抓捕后留着没办。张居正就把这个“素材”交给了冯保,在冯保会替他照顾好家人的承诺下,王大臣就招了,称“是受了高拱指使,进宫行刺万历”。
这事,一眼假。朝中“高拱派”看不下去了,吏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带头请求移交锦衣卫会审。
在会审时,王大臣见有了一线生机,当场翻供说不认识高阁老。冯保看事情要败露,赶紧叫停了会审,择日开庭。
等二次会审时,王大臣早已被人狱中下了哑药,成了一个哑巴。这场“首辅谋反案”,因此不了了之。
到了六月十六,早朝退后。高拱走到太极门,遇见太监王榛正在恭候。王榛捧着圣旨,伴随一声尖声细语的“高拱接旨”。
高拱知道,属于自己的辉煌落幕了。
果不其然。李太后在圣旨中说,高拱专横跋扈,令我孤儿寡母吃不香,睡不踏实。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张居正从此路过,搀扶着高拱谢恩接旨。
次日,天还没亮。高拱就收拾好了简单的行囊,带着家人乘坐柴车,回到了河南新郑。
晚景,相当凄凉。

隆庆的“天团内阁”都讲完了,我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朝遭人诟病呢?
归根结底是,明朝是唯一一个善恶好坏,最难区分的王朝。徐阶可能贪财一点,扳倒就扳倒了吧。可陈以勤、赵贞吉、殷士儋、李春芳这些阁老有什么大奸大恶行径,照样被高拱给外走了。
高拱为官清廉,但为人霸道。可张居正更不是善男信女。他和冯保拿“王大臣案”给他定了“行刺皇上,蓄意谋反”,这分明是没给高拱一族留活路。
张居正这一点做得非常恶劣,开启了文官“斗狠”的地狱模式。
过去,瞅你不顺眼,把你弄走就算了。到张居正办高拱时,已经不是“卷铺盖走人”那么简单,而是“趁你病,要你全家的命”。
明朝灭亡的剧本,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位“救时宰相”给写好了草稿。
后来他一死,新任首辅张四维那样对他,似乎也在合理之中了。
高拱和张居正两个所谓的“救时宰相”被争论了数百年。可小象始终没有读明白一点。
——他们到底是为了“天下大计”,不得已玩权力的游戏,还是为了玩权力的游戏,顺道心系了一下天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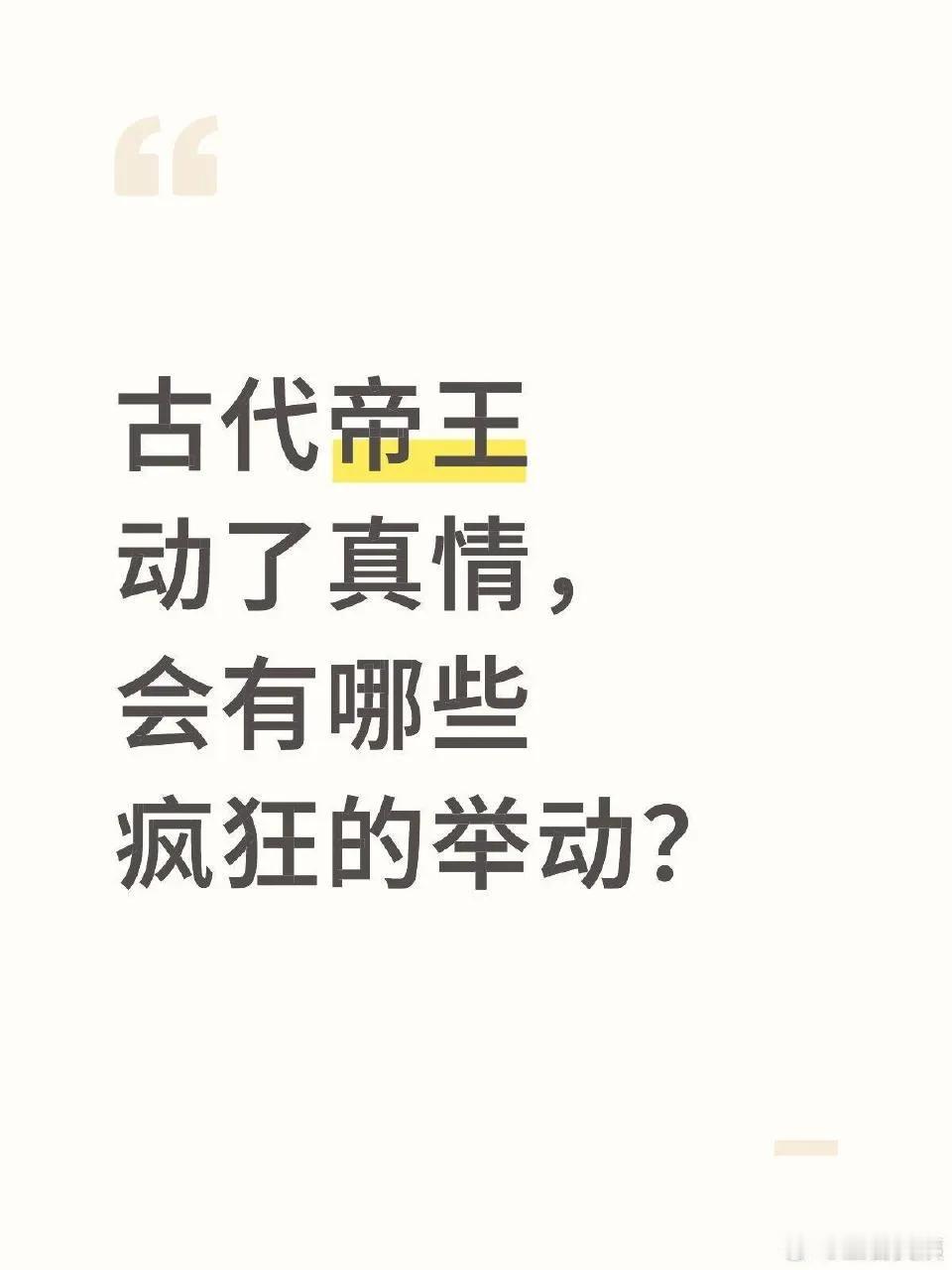
![满清野史想不到明朝最后还给他们种了木马[大笑][大笑][大笑]](http://image.uczzd.cn/4833966861126845595.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