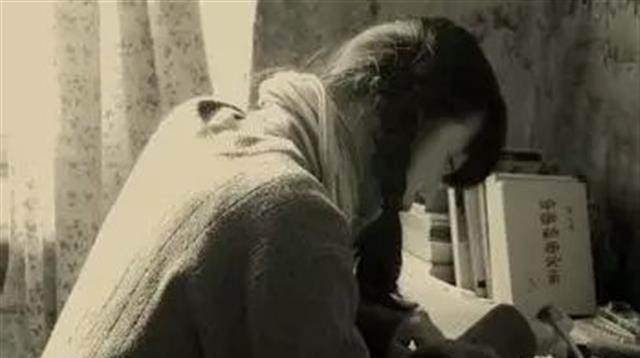1942年,31岁的萧红因病去世。她死前感情泛滥,当着丈夫的面,竟和其他男人暧昧,更留下遗言:“自己想葬在鲁迅旁边。” 1942年的香港,那座孤岛,战火纷飞。萧红,这个从东北冰天雪地里走出来的才女,生命也走到了冰点。“当着丈夫的面,竟和其他男人暧昧”,这事儿到底有没有? 有,但此“暧昧”非彼“暧昧”。 当时的情况是,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确实在她身边,但战争的混乱和求医的奔波让他心力交瘁。香港沦陷,物资奇缺,萧红被庸医误诊,喉管开了刀,话都说不出,痛苦不堪。在那个连正常医疗都保障不了的地狱模式里,端木也曾亲自用嘴为她吸出喉中的浓痰。这画面,你能说他不尽力吗?但在一个垂死之人的眼里,这点努力或许远远不够。 这时候,一个叫骆宾基的年轻人出现了。他是个文学青年,视萧红为偶像。在端木外出想办法的时候,是骆宾基,这个“其他男人”,寸步不离地守在萧红床前,喂水、擦身,记录下她最后的呓语。在一个濒死的人看来,谁在身边,谁就是全世界。那种依赖,是求生的本能,是对最后一丝温暖的抓取。 这是一个被命运反复抛弃的女人,在生命尽头,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更劲爆的是那句遗言:“我想葬在鲁迅旁边。” 这话一出,又点燃了无数人的八卦之魂。一个女人,临死不想和丈夫合葬,却惦记着另一个男人,这背后得有多少故事? 故事确实有,但真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对萧红来说,鲁迅意味着什么?是情人吗?太庸俗了!在那个年代,鲁迅是她的光,是她的“精神父亲”,是唯一看透她文字底下那股“不甘”的知己。 想当年,萧红和萧军揣着小说《生死场》手稿,在上海穷困潦倒,是鲁迅拍板,自费为她出书,并写下那句著名的序言,称赞她“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 一句话,让萧红在文坛“炸”了。 鲁迅的家,是萧红在颠沛流离中唯一能找到温暖和安宁的港湾。她可以在那里笑,可以放肆地聊天,可以像个孩子。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是她在萧军那里,在端木这里,都未曾完全得到过的。 所以,她想葬在鲁迅旁边,根本不是小儿女的情爱纠葛,而是一个天才作家,对自己文学归属的最终选择。 她是想告诉这个世界:我,萧红,是一个独立的、有价值的作家,我应该和我精神上的引路人在一起。这是一种灵魂的“认祖归宗”,是她对“半生尽遭白眼冷遇”的最后反抗。 现在学术界和文化圈,正有一股新的潮流,大家开始努力把萧红从这些八卦绯闻里“捞”出来。比如前几年出版的一本叫《跋涉:萧红的哈沪港行记》的书,就把焦点重新对准了她的文学本身,探讨她如何通过写作,在那个乱世里寻找自我。这说明,我们终于开始懂得欣赏一个女作家的才华,而不是只盯着她的私生活不放。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美国那位顶级的汉学家葛浩文,他翻译了几乎所有萧红的作品。他发现萧红最后一部长篇《马伯乐》没写完,留下一句“第九章完全文未完”。这位美国老先生,在70多年后,居然提笔给续写完了! 这事儿在文化圈争议不小,但它恰恰证明了萧红的魅力。她的文字,她的故事,有足够的力量,让一个异国的顶尖学者,在几十年后,依然念念不忘,甚至想替她完成遗愿。 一个作家的生命力,绝不是31岁就能终结的。萧红的一生,就是一个大写的 “逃离”。 她从呼兰的封建家庭逃出来,反抗包办婚姻,这是第一次逃。为了活下去,她投奔了未婚夫,结果被抛弃在旅馆。在绝望中,她遇到了萧军。萧军像个英雄一样“拯救”了她,给了她爱情,也给了她文学的启蒙。但很快,这份爱就变成了拳头和背叛。萧军的爱,炽热也伤人,像一团火,能取暖,也能把人烧成灰。 于是,她又逃了。 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了性格温和的端木蕻良。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她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安稳度日的“正常”家庭,但命运却把他们抛入了战争的洪流。端木的性格,在安稳岁月里是优点,但在乱世里,却显得有些软弱,护不住她。最终,在香港的病榻上,她发现自己无处可逃了。 她一辈子都在寻找爱,寻找一个坚实的依靠,却一次次被推开。这种极致的孤独和痛苦,也淬炼出了她独一无二的文字。没有这种“人生尽寒凉”的体验,就写不出《呼兰河传》里那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悲悯,也写不出《生死场》里那种原始、粗粝的生命力。她的天才,是用苦难喂养出来的。 1942年,萧红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这句“不甘”,才是解读萧红一生的钥匙。她不甘心自己仅仅是个被男人抛弃的弱女子,不甘心自己的才华被埋没,不甘心生命如此短暂。 八十多年过去了,依旧有人在聊她,研究她,为她续写作品。也许,这就是对她那句“不甘”的最好回答。她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她的文字,真的与蓝天碧水永处了。